發(fā)布時間:2023-05-12 來源:安徽作家網(wǎng) 作者:安徽作家網(wǎ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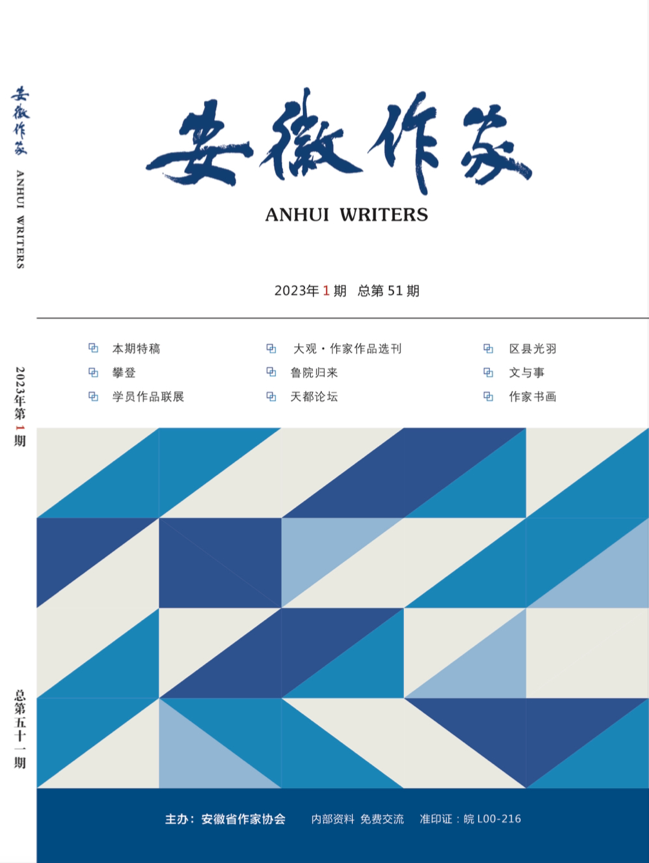
找個能說一噸話的人
雅不知
一噸話是多少?
八十年代初期那兩年,詩人張棗每每大老遠跑去尋柏樺。二十年后柏樺回憶說,每次我倆都要說上好幾噸的話,我們將這樣的見面稱之為談話節(jié),但不能超過三天,不然就會因說得過多而窒息。說話的長度是有重量的,這是一個好的比喻。我想,也要考慮到人的體力,如果是林黛玉,一噸話也就是極限了,大約是十個小時吧。
黛玉在榮國府的日常生活,雖然她素性淡然,也不免時常要到各處走走、坐坐,說一會子話的。每次在賈母處,因奉承的人多,有她的話時,不過說個十二三斤吧;在王夫人處,也就是三五兩。和姊妹們之間,說個五斤七斤算好的了。這樣計算的不光是長度,還有密度。總歸離心越遠,話就越輕,離心近時,話自然沉一些。
四十二回以前,黛玉和寶釵說話,也是輕的,但畢竟才學(xué)相敵,多了一層較量的心思,比起姊妹們便重一些,一次也大不過二三十斤。后來“蘅蕪君蘭言解疑癖”,不想二人竟成了貼心人,有幾次談話,說到二三百斤的重量。這是作者的菩薩心腸。有時和紫鵑說話,話是重的,但黛玉性冷,話不會多。偶爾一日,會說到四五十斤,這樣的日子,一年不會有一日,平時不過三五斤罷了。其余的,老嬤嬤有二斤,雪雁一斤,春纖三兩。但紫鵑每天或有三五百斤的話想要說給她,只是說不出來。黛玉和香菱,在教授寫詩的那一段時光,她的講話是用心的,用的是菩薩心和夫子心,故話沉,最多一次,百斤而已。其余說的話,每日加起來不過一斤。
能一次說上兩千斤話的人,寶玉一人而已。兩小無猜時,起居都在賈母外間碧紗櫥內(nèi),每天有幾個小時的話可說,雖然話尚不沉,但長度不短,日常已能達到數(shù)百斤。后來年紀大了,住的漸漸遠了,說話的機會有些減少,但心反而越來越近起來。有時即便相對靜默,已是互知心音,無聲處卻勝有聲,悄然間話已百斤百斤地產(chǎn)生了。黛玉遇見寶玉,說是前世的緣紛,不如說是今生的福報。知音難求。如果沒有林黛玉,就沒有賈寶玉,只是世上多了一位富貴閑人罷了;如果沒有賈寶玉,就沒有林黛玉,只是世上多了一位懨懨才人罷了。金風(fēng)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shù)。真的有幸遇見時,各自的人生才得以放大,也許生死離別,竟都是小事了。說《紅樓夢》是悲劇的,有著人心的不滿足。 《紅樓夢》講的是人的孤獨,也是講知音的難覓。
才學(xué)相近的,未必能成知音。黛玉與寶釵,一時瑜亮,也只是做到能貼心而已。 性情相近的,未必能成知音。黛玉與妙玉,都是清冷孤高的性子,也只是做到相惜而已。 情感親近的,未必能成知音。黛玉和紫鵑,紫鵑可以和她托以生死,卻也不是知音。 身世相近的,未必能成知音。黛玉和香菱,黛玉憐她孤零一人存于世間,也只是盡心對她,畢竟不是知音。 疼惜你的,你疼惜的;了解你的,你了解的;敬你的,你敬的,都未必能成知音。如賈母,如晴雯,如湘云,如探春,都稱不得是知音。 人之相處,最難的,是知字。難上加難的,是知而欲近,近而生情,一往而深,這才是知音。
知音最難得。古來的傳說故事,最好的幾個里,就有“高山流水”這一篇。“高山流水”最先出自《列子?湯問》,傳說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鐘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鐘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鐘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謂世再無知音,乃破琴絕弦,終身不復(fù)鼓。
我曾上終南山,山上一處處多有住山隱居的人。看見一間門上有殘了半邊的春聯(lián),寫的是“知音說與知音聽”。我想那些住山的人,心思原該是極淡的了,還這么牽掛著。我才知道,對知音的企盼,未必是俞伯牙、林黛玉這種絕世之人獨有。后來看到劉震云先生的《一句頂一萬句》,通篇都在講人的孤獨,原來我們這些普通人,終生也都在尋覓一個能說得上話的人呀。我們不能確證這種尋覓。這個心底的秘密,中國人只是從來不講給其他人聽就是了。
最憶牽牛花
楊 秋
初冬將至,花木草禾漸次失了水分,日見枯黃,顯出蒼涼的光景。
那些耐寒的花除外,比如牽牛。這花形容嬌嫩,吹彈即破,卻又極抗風(fēng)雨。它的顏色也豐富,有白、紫、藍、淺紅、深紅等。深紅的俗氣,淺紅的慘淡,看到紫色總讓人想起深紫的絨布來,毛茸茸的,倒也可觀。藍的最普遍,在長的秋草里隱藏著。仔細看過去,越發(fā)多起來,很有些意思。
郁達夫先生是偏愛這種顏色的,他稱藍色并白色,在牽牛花中屬上乘,我也認同。去年一次湖邊漫走,看見一棵纏繞在枯枝上的牽牛,開著白的朵子,玉一般細膩柔嫩。忽而感覺,這白色是牽牛花中的貴族了。可惜得很,第二日再去,已被連根拔去,細藤上還綴著兩三朵,與昨日相比,細瘦了許多,也沒有了白玉的光澤。
這似乎成了一條規(guī)律。每個秋季,在小區(qū)的石楠棵旁、木柵欄邊,總有一些牽牛花的細莖,不知什么時候攀了上去。在清晨的冷風(fēng)里,開出藍的、紫的朵子。風(fēng)一過,這些藍的紫的,就像嫵媚的眼,閃著快活的笑意。
目光觸及到它們,總莫名得緊張起來,擔心它們此后的命運。接下來幾日,自是不敢再去。或者懷了僥幸之心,悄悄去望:半死的藤上必綴著極為慘淡的小朵,那努力的樣子,叫人不忍。是我目光有毒,還是誰窺到我的歡喜,而剝奪了它的性命?似乎都不是,卻又出奇得準確,不知是何原因。若開口詢問,必引來詫異的目光,仿佛在說,為一棵野花?往往自己倒先失了底氣。
幾日前去鄉(xiāng)下,經(jīng)過我的村莊。我執(zhí)意停留一會,一個人。這個村子幾年前被拆遷了。所有的樹木,成材的、不成材的,一律伐掉了。剩下新發(fā)的野樹蓬、過膝的荒草以及隨著地勢起伏的暗淡陳舊的綠植。
我艱難地在荒草中行走,尋找當年生活過的痕跡。目之所觸,一片荒涼。我感到如此陌生,有種被撂在荒島的惶恐。所幸,在一片結(jié)滿籽的秋草里,看到有藍的紫的亮光在閃,“牽牛花——”我眼中一熱,幾乎要跪下去擁抱這片土地。這里應(yīng)該是我生活了二十年,又離開了三十余年的家。
牽牛花盛開的所在,是我家廚屋之南,緊挨著水坑。那一年不知是從飛鳥嘴里跌落的,還是風(fēng)送過來的種子,在坑沿兒柳樹旁生發(fā)了長長細細的莖,隨著樹身向上攀援。心形的綠葉帶著三個尖兒,在南來北往的風(fēng)中不停顫動著。入秋之前,柳樹的細條子上點綴了藍的紫的粉的花子,為綠枝增添了美好。
放早學(xué)回家,掀開饃筐子,壞紅芋的氣息夾著餾熟梅豆子特別的味,讓我沒有半點食欲。母親總是這樣子,發(fā)覺東西壞了,不扔。用刀削了又削,剜除壞掉的部分,仍舊做給我們吃。不變的,還有同時出鍋的梅豆子,它和壞紅芋的氣味混到一起,我畢生不忘。
那滿是綠肥和塵土的水坑,似乎無聲地滋潤著那棵柳樹,連同纏繞的牽牛。入冬很久,桐樹、楝樹、棗樹,它們的葉子落凈了,大柳樹依然繁茂著,頂著一頭彩色的花。對著這樣的景致,我忘記了壞紅芋的氣息。那棵綠柳以及攀附的牽牛,成了我心中的牽掛。
又一次回家,書包一丟,就去看。眼前的狀況讓我驚駭:心形的綠葉全折皺著,向下垂,有少數(shù)花在開,形容憔悴。三棵小拇指般粗細的根被齊齊割斷。我摟著大樹把臉貼在纏繞的莖上,感到心里很疼。
母親說,那棵樹是公家的,我們不能阻止誰干什么。我知道,除去我之外,誰在乎幾棵野花子呢。手里的鐮刀,隨時可以讓它斃命的。不曾想牽牛花居然落下了后代,一年一年,生生不息了。
憑借著匍匐在地的牽牛花,我找到了我家的堂屋、西屋、父母住的小屋還有廚屋,以及院子里那棵大泡桐樹、堂屋后的棠梨子樹、西屋前的兩棵棗樹、壓水井、雞窩……雞窩邊上,天麻正開著銀紅的花。
那道矮墻地基處,綠植要高出一些。墻外楊霞家青磚的堂屋、向西連著廁所的過道、門向東的廚屋、院子里那一棵椿樹上綁著布帶的小臭,癱坐在木墩上咿咿呀呀的,不知道是哭還是笑。
程老太紅著臉膛子,拎著拐棍仍舊在她的園子邊逡巡;大老陳倚著老槐樹端著小饃盤兒吃著紅芋。他們各做各的事,沒有人看到我。我用半天時間,在村子里走了幾趟,感覺自己像是一個外人。
站在渦河壩上,再看,一片荒蕪罷了。
為了解決心的思念,我從故鄉(xiāng)的荒草里,尋了牽牛花的種子,埋在花盆里。來年,出了兩株可憐的芽,很委屈地生存著。我時時關(guān)注著它們,其中一株無端黃了。另一株長長了秧子。我用細的線把它縛在防盜窗的網(wǎng)上,竟然沿著網(wǎng)格跌跌撞撞向前爬了。隨著曉風(fēng)晚風(fēng),心形小葉子微微顫動。很細的一枝,也沒走多遠。
夏里,酷熱的太陽炙烤著它,夜間吸納的清涼,全被烤走,整個藤葉若水燙一般。如此,一天一個生死輪回,卻也活了下來。一屆仲秋,細藤上有了花的蓓蕾,我們等著它盛放的樣子,始終不得。往往開了一半,大太陽一照,匆匆擰在了一起。
內(nèi)心只覺著它可憐,牽牛花沒有留下一粒成熟的種子。以后,我也沒有再種過。
故鄉(xiāng)(外二首)
馬金萍
槐花提著一串香
在夢中
鄰家小妹又開始唱了
相思高過思想
不知道那個曾經(jīng)的木馬是否變了模樣
想你的澎湃
比這里的早會還要熱烈
打卡,草稿,報表
像極了你的笑
無時不刻
鄉(xiāng)間的小路
成長在遠方
從未停止過坑坑洼洼
我枯萎,我茂盛
似一個從未休息的陀螺
童年的田間有一棵樹
路邊的雜草又似多個我
路啊,
走過祖輩,父輩,如今又走過我
羊腸一樣的彎
朝夕相照,風(fēng)雨婆娑
偏愛這樣的
想做一個長長的夢
有浩雪,有繁花
有彎月
還有那片無憂的羊群
綠色傳染了綠色
我沒有告白
就這樣,跟隨了一片綠色
我把自己分成兩半
一半是我,一半是影子
高處,低處
我們身嵌其中
一片片的
不再消失
山路肥沃,等浩瀚的秋景深過春宵
慢慢活著吧
綠,畢竟代表生命
就當一次復(fù)活
初冬晨練(外一首)
丑 石
我看到了蘆葦,高高矮矮,參差無味
單調(diào)輕盈如母親近七十年的身體
三個孩子追逐嬉戲,兩個年輕的母親
他們鬧著,母親跟著,慢慢迎來一場雪
一撥撥廣場舞是最廉價的藥
頸椎病、腰疼、食欲不振,還有一些疑難雜癥扭扭就好
一道朝陽艷麗地照到廣電大樓中央
她的美高于玫瑰
高于餃子的味道
白 紙
白紙黑字
那寫錯的符號
留給誰看
曾經(jīng)錯過的人
用涂改液能否找回
白紙上多難的詩行
沒有儀式感
沒有進入房間
那生銹的鑰匙留給誰
一生中愛過的人
靜靜地躺在白紙上
選自《安徽作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