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11-28 來源:安徽作家網 作者:安徽作家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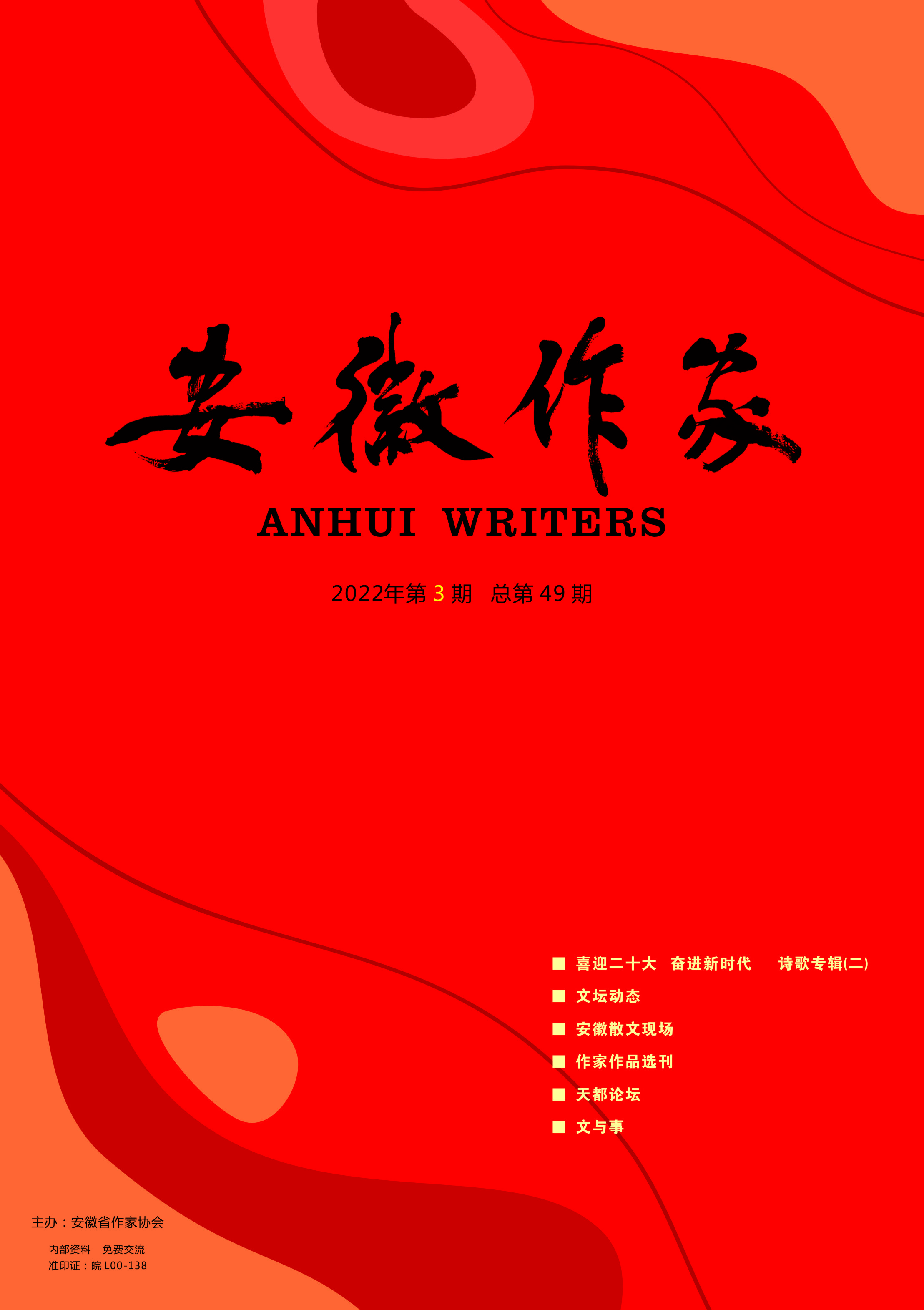
作品欣賞
散文觀:作為一種見情見性的文體,散文對寫作者的消耗太大了,大體量的寫作勢必會導致質量上的平庸。修辭立其誠。散文寫作尤其需要“誠”。比較而言,我更喜歡有生命體驗的散文,讀這樣的散文,能觸摸到作者的呼吸、心跳和體溫。
草木本心
江少賓
我是到合肥之后,才認識廣玉蘭的。阜陽路上,長長的兩排,橢圓形的葉子肥而厚,正面光滑,反面粗糙,無鋸齒,像一把把臨風輕搖的小蒲扇。我在鄉村長大,蒲扇太熟悉了,盛夏的傍晚,梧桐樹下,一張咿咿呀呀的小竹床。破舊的蒲扇握在母親的手里,朦朧間,蒲扇在我身上“噗嗒”一聲,又在妹妹身上“噗嗒”一聲。“輕羅小扇撲流螢”,母親撲的不是流螢,是蚊蟲。在牌樓,竹床不叫竹床,叫“涼床”。這個詞是誰發明的?不知道,太準確了!睡到半夜,渾身涼洇洇的,疏朗的星光從梧葉間漏下來,像一灘流瀉的乳汁在四周搖晃。星空是一方幽藍的池塘,在瓦屋頂上傾覆,星漢燦爛,若出其里,看上去就在巢山之巔。離開牌樓許多年之后,我在江西的懷玉山、石臺的牯牛降撞見過童年的星空——低矮的穹廬浮著一層毛玻璃,滿天繁星就在毛玻璃后面,伸手可摘的樣子。“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銀河是一條幽藍色的游動的光帶,水晶一樣,就快漲破了。好像已經漲破了。我久久地仰望童年的星空,竟無語凝噎,像面對一個闊別多年的親人……我時常遙想童年的星空,也時常遙想母親的蒲扇。
廣玉蘭開花有早有遲,在同一棵樹上,能看到花開的各種形態。有碧綠如洗的花苞,如嬰兒的臉,柔嫩可愛;有完全綻開的,花朵潔白而甜美,紡錘形的花蕊長約一寸。廣玉蘭香味淡雅,花期也不長,花瓣凋落之后,花蕊依舊挺立在枝頭,已經長成了一根兩寸長的圓莖。圓莖四周,綴滿了紫紅色的小顆粒,那是廣玉蘭賴以孕育新生命的種子。這時候的廣玉蘭不再是一棵樹,而是黃昏里瞌睡的老祖母——風風雨雨都過去了,如今四世同堂,她在余暉里享受著歲月安詳。
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飄萍于江湖,寄情于草木,中國自古就有歌詠草木的傳統,但玉蘭入詩卻極少,一直到明朝,才偶現幾首脫俗的玉蘭詩,其中名氣最大也寫出了一點新意的,是文徵明的這首《詠玉蘭》:
綽約新妝玉有輝,素娥千隊雪成圍。
我知姑射真仙子,天遺霓裳試羽衣。
影落空階初月冷,香生別院晚風微。
玉環飛燕原相敵,笑比江梅不恨肥。
新開的玉蘭花潔白優雅,仿佛綽約多姿的女子,她剛剛妝過的面容散發出美玉一般的輝光。遠看時,滿樹的花朵像無數穿著素衣的美人,又像雪花一樣輕盈起舞,真是美不勝收啊……文徵明寫的其實是白玉蘭。白玉蘭和廣玉蘭同屬木蘭科,白玉蘭是落葉喬木,廣玉蘭是常綠喬木。白玉蘭先開花,后長葉,廣玉蘭花葉同放。另一個明顯的區別是花期:白玉蘭的花期在每年的二三月份,這個重要的時間節點,詩句“影落空階初月冷”可為佐證;廣玉蘭的花期則在初夏時節,大江南北,物候上略有差異。五月,天鵝湖南岸綠軸公園里的廣玉蘭就開花了,而六月份在北京,一株雨后的廣玉蘭剛剛綻開五六朵花苞,孤零零地站在一條幽深的巷道里,前后左右,全是槐樹。槐樹開花也是暮春初夏,但北京六月的槐花,枝葉間的花苞才剛剛綻開。我見過槐花怒放的繁盛景象:一棵槐樹,就是一片花的海洋。一串串乳白色的風鈴垂在枝頭,在微風中輕輕搖曳。完全綻開的,像一只只展翅欲飛的白蝴蝶;有的還是花苞,像一盞盞小燈籠;有的只開了一半,宛若情竇初開的少女的臉……槐花樣子淡雅,氣味卻迷人。
槐花可食(許多花都可食),且吃法很多,僅我吃過的,就有槐花雞蛋湯,干蝦蒸槐花,槐花蒸蛋,槐花炒蛋,槐花煎餅,槐花餃子,槐花面疙瘩,還有母親最拿手的槐花飯。割晚稻的時候,母親喜歡煮槐花飯,那是一個農家主婦能給予孩子的最高犒賞。母親把槐花摘下來,在井邊淘洗,然后一片片地鋪在篩籮上,曬。槐花不吸水,曬兩個日頭就干了。母親把曬干的槐花捧進一只褐色的鐵皮筒里,掛在廚房里的一根橫梁上。每一次煮槐花飯,母親都要將右手窩起來,慢慢地探進鐵皮筒,啄兩小把槐花,放在米里,攪勻了,蓋好鍋蓋,再彎腰點燃鍋洞里的柴火。從田畈里歸來,我們老遠就聞到了槐花的香氣,山芋的香氣。鍋洞里的草灰將熄時,母親總要在草灰里埋一根山芋,等草灰冷成一堆死寂的灰燼,山芋也煨熟了。揭開一層焦燙的皮,山芋黃燦燦的,甜絲絲的,沁人心脾。母親做的槐花飯有些澀嘴,卻包著一縷淡淡的槐花香,沒有一種滋味可以形容它。或許,那就是農家的味道,母親的味道吧。
離開牌樓之后,我再沒有吃過母親的槐花飯。每一次想吃槐花飯,我首先想到的,總是母親窩著右手,從鐵皮筒里啄槐花的樣子。母親過世后,我已經沒有了再吃槐花飯的想法。
合肥環城公園里有一大片槐林。五月,槐花開了,環城路上浮動著清甜而軟糯的槐花香。那時候單位還沒有搬遷,閑暇的午后,我時常在環城公園的甬道上散步。甬道上槐花紛披,濃蔭深處,合抱著一對對你儂我儂的小情侶。我從不去驚擾他們。我也在五月的環城公園里談過戀愛,那一樹樹槐花,也只有愛情可堪比擬,也只有兩心相悅才不算辜負。密密匝匝的槐花下面,蜜蜂飛來飛去,嗡嗡,嗡嗡嗡。我嫌鬧,卻不嫌吵,和人類相比,蜜蜂更有資格享受這場盛宴。更何況,蜜蜂鬧來鬧去,最終都為人類做了嫁衣。父親酷嗜槐花蜜,早一杯,晚一杯,溫水沖服,常年如此。我喝過幾次,相當失望,槐花蜜里,并沒有那種清甜而軟糯的槐花的香氣。
若以花喻人,清甜而軟糯的槐花,當是情竇初開的少女,白居易詩云:“夜雨槐花落,微涼臥北軒。”無論是開在枝頭,還是零落在地,槐花的氣質都是少女的;而晶瑩皎潔的玉蘭,無疑是熱情洋溢的少婦,明人張羽的詩:“芳草碧萋萋,思君漓水西。盈盈葉上露,似欲向人啼。”櫻花也有一種慵懶的少婦美。中國科技大學黃山路的校園里有一條“櫻花大道”,在微信朋友圈里著名著,近在咫尺,我卻一次也沒有去過。武漢大學也有一條著名的“櫻花大道”,友人多次邀約,我也從未允諾。詠櫻花的詩詞不多,好的更少,我只記得一句,蘇曼殊的,“芒鞋鐵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玉蘭和櫻花都太奔放了,我不喜。詩人好像也不喜。少婦一旦奔放起來,往往了無詩意。
桂花是花中的美少女。桂花,又名木樨,花簇生,果實紫黑色,俗稱桂子。現知的桂花品種至少有一百多個,常分為四大類:黃色的金桂,味淡香;白色的銀桂,香味濃;紅色的丹桂,香味較淡;最常見的是四季桂,俗稱月桂,花期較長,但味道很淡。桂花是合肥市的市花,幾乎遍及大街小巷,壽春路、黃山路,大蜀山,植物園,包河、逍遙津、琥珀潭、環城公園……八月桂花遍地開,滿城暗香浮動,連發梢上都染上了桂花的香氣,如絲如縷,心曠神怡。白居易詩云:“遙知天上桂花孤,試問嫦娥更要無?月宮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詠桂的詩詞不勝枚舉,佳句也不少,或許是桂花迷人的香氣,激發了詩人不羈的想象力。據《晉書》載:晉武帝年間,郄詵出任雍州刺史,晉武帝請他自我評價,郄詵毫不謙虛地說:“我就像月宮里的一段桂枝,昆侖山上的一塊寶玉……”面對狂傲的郄詵,晉武帝不僅不以為忤,反而大笑著予以嘉許。后人便用月宮中的一段桂枝、昆侖山上的一塊寶玉來形容特別出眾的人才,這便是“蟾宮摘桂”的由來。蟾宮就是月宮,吳剛月宮伐桂的故事,在中國民間流傳甚廣,婦孺皆知。桂花和月,也成為秋賦的核心意象之一。唐朝以后,科舉制度盛行,蟾宮摘桂便成了科舉及第的代名詞。蟾宮,摘桂,一靜,一動,想想就很美啊!激動人心。
每次看到桂花,我總會無端地想到豐腴的大唐。少女般明媚的桂花,也配得上那個豐腴的大唐。大唐的桂花開在巍峨的廟堂里,開在李白王維白居易的詩歌里,開在唐玄宗美輪美奐的《霓裳羽衣曲》里。中國栽培桂花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春秋戰國時期的《山海經》、屈原的《酒歌》、東漢袁康等輯錄的《越絕書》、西漢司馬相如的《上林賦》,以及晉人嵇含所著的《南方草木狀》中,都寫到了桂花。在民間,桂花的廣泛栽培始于宋,盛于明。桂花枝繁葉茂,無論是開花還是散葉,都是一團和氣,多子多福的樣子,有一種東方女性的美。胡蘭成說,桃花,難畫,因為要畫得它靜。桃花太艷了,近乎妖,靜不靜我不知道,霜降之后的遲桂花倒是靜的。花壇邊,夜露垂降,天地寂然,桂花兀自撲簌簌,一朵,兩朵,三四朵。落葉總是悲秋,但桂花落,看上去既嫻靜,又美好,心底仿佛有清風徐徐拂過。“人閑桂花落”,少時讀王維,這一句總是念念不忘,每次讀,都像一個人潛回故鄉。
“月宮賜桂子,獎賞善人家。福高滿樹碧,壽高滿樹花。采花釀桂酒,先送爹和媽。吳剛助善者,降災奸詐滑。”桂花酒是人間佳釀。中秋飲桂花酒的習俗在我國各地流布甚廣,屈原的《酒歌》中已有“援驥斗兮酌桂漿”、“奠桂兮椒漿”的詩句,可見飲桂花酒的年代已經相當久遠了。
除了釀酒,桂花還是一種天然藥材。桂花性溫味辛,具有健胃、化痰、生津、散痰、平肝的作用,能治痰多咳嗽、腸風血痢、牙痛口臭、食欲不振、經閉腹痛。由桂花蒸餾而得的“桂花露”,具有舒肝理氣、醒脾開胃的功效,能治口臭、咽干等病,是上等的飲料。桂枝、桂子、桂根皆可入藥,由桂枝、芍藥、生姜、大棗、甘草配制的桂枝湯,專治外感風邪、腎虛等癥。桂根可治療筋骨疼痛、風濕麻木等病癥。桂花晾干后可以沖茶。某年,在皖南祁門某個古村落的水口,我遇到一位自產自銷桂花茶的老農,他家的后院長著兩棵桂花樹,兩棵都有一百多年了,接近三層樓高,樹冠如蓋,樹干需要兩個人合抱。老農自己說,他做桂花茶已經二十多年了,每年能做五六斤,自己喝的少,大部分用于銷售。沖泡之后的桂花像飽綻的粥粒,貼近杯口,淡黃色的茶湯里,漾起一股撲鼻的桂花香。老農的桂花茶半斤起售,六百元,太貴了,我只好泡了一杯,坐下來,續了三次水。臨走,我在杯子底下壓了五十塊錢,老農沒有拒絕,笑瞇瞇的,裝著沒有看見。那是我喝過的最貴的茶葉。
桂花糕。桂花蜜。桂花糖。桂花粥。桂花鴨。桂花糯米藕。桂花……桂花有各種各樣的吃法,每一種,光看名字,就透著一股馥郁的香。還是白居易的詩:“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邵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游?”2011年國慶,我陪父親游杭州,西湖、岳王廟、靈隱寺、宋城都去了,最讓我難忘的,還是朱利平凌來芳夫婦請我們吃的桂花山藥。太好吃了,人間至美。飯店的名字我忘了,規模不大,門前有兩株蒼翠的香樟,高約兩丈,一地濃蔭。
老家的院子里也有一棵桂花樹。小村牌樓,也只有這一棵桂花樹。父親喜歡栽樹,梧桐,香樟,楓香,女貞,欒樹,構樹,海棠,棗樹,桃樹,杏樹,香椿,刺槐,松樹……破罡街上能買到的樹苗,父親都買回來栽過。現在的小村,已經沒有人栽樹了。春節,回來的人多,留守在家的老人會提前上山,砍幾棵松樹或楓香,曬干了,當柴火。巢山上的松樹和楓香,已經長野了。它們在巢山上兀自生長,和老人們一樣寂寞。
百般紅紫斗芳菲。這是草木對大自然的回報,也是對人類的豐厚饋贈。遺憾的是,除了自幼熟悉的草木,在植物學方面,我長期停留在小學生的水平。面對合肥街頭那些琳瑯滿目的花花草草,我曾經一片茫然,甚至不知道路邊那種隨處可見的矮灌木,就是大名鼎鼎的石楠,更不認識櫸樹、樸樹、紫薇、黃連木、鵝掌楸、金邊黃楊、杜英、無患子、五彩蘇、吉祥草,甚至一度區別不了芙蓉和木槿……一個不關心草木榮枯的人,勢必索然無味,他不會發自內心地熱愛親人、自然和社會,近乎面目可憎,幾乎不足以談人生(這當然是我的個人偏見,過于粗暴和武斷,面目也很可憎)。人進中年,我越來越喜歡深居簡出,生活隨性而簡單,逐漸疏離形形色色的圈子,基本不參與無謂的應酬。每月為數不多的幾個休息日,我喜歡帶孩子去野外踏青,教他背唐詩,讀《詩經》,識鳥獸草木之名。在我看來,辨識草木的過程,就是重新認識自我的過程,就是自己給自己洗心洗肺的過程。自然中的每一棵植株,其實都是我們的故人。每一根花草,都是我們的血親。草木有本心。自然中葳蕤的草木,附著有我們的情感、體溫和靈魂。
我喜歡梧桐和桑樹。梧桐是蕪湖路的標志之一,這是一種父性的適于懷舊的樹。秋天的黃昏,夕陽西下,梧葉斑駁,有一種滄桑和蕭索的美。桑樹是屬于故鄉的植物,有桑樹的地方,總有炊煙升起。炊煙飄拂的屋頂下,總有我們的親人,坐在鍋洞旁邊,溫暖的火苗,舔紅了大地一樣蒼老的臉。
我在合肥沒有找到成林的桑,找到過幾株伶仃的梓。古人栽桑是為了養蠶,種梓是為了點燈(梓樹的種子外面,白色的就是蠟)。小時候,每到春天,菜園里,屋腳邊,總會抽出一兩棵幼苗,每次看見,我們總要除草一樣將幼苗連根拔起。那時候我們都不認識梓,現在認識了,菜園早已荒廢,老屋的院子里雜草叢生。沒有了梓。屋頂上,炊煙不再升起。
都說“吾心安處是故鄉”,吾心安處,不在合肥。歲月如白駒過隙。屈指算來,我在合肥,已經二十二年了。
(選自《安徽作家》,2022年第三期)
作者簡介

江少賓,上世紀七十年代生于安徽樅陽,供職媒體,業余寫散文。曾獲人民文學獎、冰心散文獎、老舍散文獎、西部文學獎等。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回不去的故鄉》《大地上的燈盞》。
作品欣賞
散文觀:佛經講,不要“法縛”。我寫文章,不喜歡既成定例。隨心隨性,自然成文。
文章小道,但若能通于大道,就已非小道了。只要足夠懇切真實,就能夠以小見大。我是一,也是一切。是芥子,也是須彌。
被風吹綠的筆記本
文 河
年后立春。時值陰歷正月初7。風細了,圓了,長了。絲絲吹著——穿過針眼兒,若有若無,仿佛來自靈魂的罅隙。陰歷21號,上午,有陽光。陽光變暖時,便成了一種撫摸。在路邊,我發現那株野海棠的枝條上爆出了芽粒。星星點點的。腥紅。很紅很紅的顏色有尖銳感,像針尖。好些年了,它一直沒有開花。不知道今年它會不會開。我看了一會,感到很愉悅。感到春天正一針一線的把我織進她的圖案中去。
麥子還沒起身兒——是那種待要起身,猶未起身的狀態。但看上去明顯比年前綠了。這是在雙廟地界。雙廟,一個地名。我曾在此生活過幾年,因此,對我而言,它已經超越于地名。它是一枚靈魂的郵票。沿著黑茨河蜿蜒向南,在去神農藥材廠的堤壩上,是一條楊樹林帶。從白龍橋到藥材廠的這段距離,我看到了很多鳥巢。一個、兩個、三個……一共十七個。鳥巢很大,粗糙,簡陋。有烏鴉的,也有喜鵲的。這些鳥巢無一例外都搭建在最高的樹梢上。有的一棵樹上甚至有兩個。很快,這些楊樹就會長滿葉子了,就能把鳥巢掩藏起來了,并且又慢慢把它們舉向一個新的高度。這樣,過不多久,鳥巢中就會孕育出幼鳥,林子里就會充滿新的歌唱。從神農藥材廠出來,在去王大莊的路上,我才看到五六只烏鴉,它們在楊樹上飛落。我總感到烏鴉是種孤獨的鳥兒。這么多鳥兒在一起,只不過加深了它們的孤獨。又過一段路,在黑茨河灘上,我又看到十來只喜鵲,溜河風把它們黑白分明的羽毛吹得有點零亂。我在風中一動也不敢動。
在早晨,沉默整整一個冬天的花斑鳩突然叫了幾聲。是一只。在西沙河對岸那片雜樹林子里。從此,在以后的許多個早晨它都會不停的叫下去的。我懷疑那片樹林里還應該有一只斑鳩。只不過此時還沒鳴叫。陽光明凈。早晨的鮮明的陽光。古詩“初日照高林”,寫的只是事實,但在一個經驗主義的層面上,卻有著一種超越日常性的質樸的美感。我身邊的這棵野石榴樹的枝條變得柔韌了,樹皮吹彈得破,充滿了一種生命的力度。去年,這棵樹結了七個野石榴,小小的,圓潤的紅皮石榴,像北斗七星。毫無疑問,今年,它會結的更多。天空會在它披紛的枝杈間降下一個更為璀璨的星群。沉寂中又是一陣斑鳩叫。我沒有到河對岸去。我在河這邊停下來。我一直守著一條窄窄的理想主義的河岸。
從賈顧莊到西沙河之間的這條路,我不知道曾走過多少遍了。同一條路,走得越多,越證明我生活的單調。但是,反過來說,為什么我就不能通過對簡單有限事物的反復描述,來使自己抵達某種繁富呢。從賈顧莊到西沙河之間的這條路,中間還隔著李營。李營西頭的那片天空。去年夏末,下午,陽光白亮亮的,當我經過時,曾看到一大堆雪白的云。映著深邃淵靜的藍天,映著野地里那幾棵綠葉郁郁的大桐樹梢子,那白云顯出極其強烈的亮度和雕塑感。當然,那片白云早就消失了——過不多久就消失了。緣起緣滅,云聚云散。如今,只剩下一片空曠的天空。只有我知道,那片天空,曾有過多么壯麗的景象。只有我,一直對那片白云念念不忘。因此,每次走過那條路時,也只有我一個人感覺到那片天空有一種無法言喻的荒涼。李營西有一大片櫻桃林,小小的腥紅色花骨朵剛剛從枝條上脫穎而出。脆弱的美從虛無深處再次來到人間。我一直在某種極端的有限性中生活。是的,我要把同一條路,反復走,經常走,只到把它走成一種無限,只到用盡自己的一生。
那所鄉村診所在秦小莊東邊,靠著一條砂礓路。一個小小的院落。三間出檐瓦房,青色的磚,灰色的瓦,白色的院墻。它的瓦很好看,半圓弧的小筒瓦,積滿青苔,是小土窯燒的。八十年代末期這種小土窯就淘汰了,因此,這樣的瓦如今極少見了。現在的瓦都是紅色的片瓦。一個小筒瓦就像一個半括號,這些半括號順勢疊徹,呈魚鱗狀,便有一種沉靜典雅的韻律感。診所有著古樸清涼的色彩,有著皖北平原特有的深厚滯重的寧靜,也有著可以看得見甚至掬在手中的清幽幽的光陰。我喜歡這個診所的名稱:“一根針,一把草”。這個名稱有著傳統中醫的平和、沉穩和自信。甚至略微顯出了某種簡潔的意味。院子里種著何首烏、桔梗、大青根、麥冬、白芍、忍冬(這種植物的花朵在福克納的小說《喧嘩與騷動》中有著那么濃郁曖昧的氣味)。還有幾種藥草,我叫不上名字。根莖最大的那株何首烏被制成了盆景。白芍剛剛冒出紅艷艷的芽粒。一只鳥兒在極高的天空中叫了一聲,像一滴飽滿的雨水,在一大片青荷葉般寂靜的天空中滴溜溜的滾動好大一會兒,然后才突然筆直地落下來。生命在天地間流轉著,并且波瀾不驚。
在這片平原上,這些村莊其實大同小異。有些零亂和陳舊,像被一陣大風突然刮成這個樣子的。并且永遠陷入寂靜之間。甚至在刮大風時,這些村莊也是寂靜的。風把聲音都刮跑了。冬天,這些小村莊就更寂靜了。尤其是夜晚。寂靜到極處,世上所有的聲音倒仿佛又回到寂靜之中了。這樣,寂靜反倒成了一種更大的聲音。冬夜,一個小村莊就是住了再多的人,還是空,還是寂靜,還是感到時空和歲月的無邊無際。冬天的房間需要住上人,需要有燈光,熄燈后房檐上需要夜夜掛滿古銅色的大月亮。風刮過來,刮過去,然后就刮到了春天。這時,風會把一些帶走的東西送回來。風同時刮進所有空蕩蕩的房間,把色彩和溫暖還給人間。風吹皺河水,吹皺女人的衣衫,還把一些人的心吹成漣漪。當然,風還吹動更多東西。慢慢的,村莊在風中發生變化。墻角的花朵在你看到或看不到的時候一夜之間就紅了。然后,在你看到或看不到的時候,一夜之間,有的落了,有的變成了果實。星星特別大,特別亮,掛滿酸棗樹瘦瘦硬硬的枝條。春天到來的時候,我經常在村子與村子之間游走,直到盛夏來臨,綠蔭重新把我覆蓋。村莊,一個最綠的詞。記得二十年前的暮晚,父親曾讓我到鄰村楊橋去找他的一個老同學喝酒。我很快就到了。整個村子靜悄悄的,似乎空無一人。記得當時我曾想道:這整個村子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這兒有種古樸、廢棄和遺忘的氣息。我感覺自己好像一下子來到另外一個極其遙遠神秘的地方。村口有個大水塘,塘里堆著菱角葉子,開滿金黃色的小花。也許還有蓮藕。一株粗可摟抱的大黑皮柳樹斜臥在水面上。到處是撕裂不開的濃蔭,鋪天蓋地,似乎把我的雙肩都壓疼了。濃蔭中還有許多幽暗又閃爍的光線、光斑和光點。那種寂靜、溫煦、厚實的氛圍(就像一個夢境)包裹住我。我懷著好奇而又虔敬的心情放慢腳步……那時我才十來歲。我還沒讀到保羅·策蘭的詩句:“每當我與桑樹并肩緩緩穿過夏季,它最嫩的葉片尖叫”(王家新譯)。那強烈到近乎尖銳的內心感受啊!那種感受我至今不忘,——但至今仍無法完全清晰的表達出來。
我是去年夏天發現那道溝渠的,它在三河村西南角。那是一個早晨。我先是從老遠的地方看到那個四圍長滿楊樹的水塘,然后就信步走過去。還沒到那兒,就聽到嘩嘩的流水聲。那條溝渠從水塘向西沙河蜿蜒流去。剛下過一場暴雨,水積得很滿。渠道兩旁長滿茂盛的荒草。幾只鵪鶉突然竄上天空。我順著流水沒走多遠就返回來,因為草葉上露水珠子太多,把褲腳都打濕了。深秋的一個黃昏,我又去過一次。渠水變得又細又淺,幾乎看不到流動。夕陽一片火紅。枯黃的茅草在西風中發出極長極硬的聲音,細細的,不絕如縷,像針尖,一下下扎在心上。白色的花絮漫天飛舞。我靜靜站一會兒,走了。整個冬天,我一次也沒去過。但我老是記著那個溝渠。有時我想,我應該再去看看它。但我最終沒去。我第三次去的時候,已是春天。春天對我來說,更是一種信念。只有一無所有的人,才能看到更多的春天。這次,我順著這條溝渠一直向前走。最細微的事物也能把我帶走。我想,就算從這個水塘到西沙河這段短短的距離,也足夠我走這一輩子的了。我走啊走啊,像個無助的孩子。
第一次看到這些石楠的時候,并不認識它們。后來,回去查了查資料,才知道它們的名字。以前,曾在勃朗特三姊妹(夏洛蒂,艾米莉,安妮)的小說中,讀到過描寫這種植物的文字。它們在哈代的小說中也大量出現。而這幾叢石楠就長在劉關小學校園南面的空地上。厚墩墩的葉片呈暗綠色(它們的厚度很像枇杷葉,色澤稍淺,但葉形要比枇杷葉俊秀)。葉片層疊有致。很多長青樹的葉片只有等到新葉長出后才會脫落,而石楠的葉片則能經受好幾個冬天。現在是春天了,石楠的枝頭又萌生出新的葉芽。這些小小的鮮嫩得不可碰觸的葉片,陽光中閃閃發亮。當你凝視它們的時候,你會感到這個世界正在慢慢融化——融化成旋律、色彩、光芒。我早就想寫一寫這些石楠了。這最純粹的生命。我看到一些事物,如果我不能把它們表達出來,我覺得這就是我對它們的虧欠。我必須浩大。我必須在死亡與永生中寫下最動人的文字。
(選自《安徽作家》,2022年第三期)
作者簡介

文河,生于上世紀70年代,太和縣人。主要寫作詩歌和散文。出版有散文集《清晴可喜》《城西之書》等。
作品欣賞
散文觀:寫作就是與日月星辰、大地山川、草木鳥獸、云霧苔石和古今人默默對話,與另一個隱藏的自己私語。其間情境,秘密又歡愉,孤寂又痛快。接續中國詩騷和文章傳統,繼續發現漢字之美,是我的使命,也是文章實踐上的自覺。
舊年的絲瓜吊在木蘭上
儲勁松
洵 美
藍草染的澆花布真是清美,當年外婆拿來包頭,有青白顏色,也有清白家風。
葫蘆、絲瓜、黃瓜、月亮菜、瓠子吊在豆棚瓜架上,靜女其孌,洵美且異。
闃無人跡的山谷流泉好看。
農家女子壯碩的身板和黑檀似的肌膚,是媽媽年輕時的模樣。
古民居的馬頭墻、魚鱗瓦、瓦當、鎮脊獸、天井、木雕人物,苔色蒼蒼的大青磚,逸筆草草的芝蘭仙鶴圖,墻上掛的草帽、蓑衣、竹籃子,是記憶里的故鄉。
竹葉草洵美,板栗樹洵美,玉米須洵美,水稻花洵美,在上面奔跑、追逐、求歡或者靜伏的瓢蟲洵美,甚至黑殼、黃殼、銅綠殼的金龜子也洵美且異。
流霞好看,騰霧好看,卿云好看。飛鳥好看,螞蟻好看,潛翔水底的魚蝦好看。泥土好看,毛石頭好看,松竹連它們在日月天光下的影子都蕭然動人。
清晨的毛草和石菖蒲,葉片和葉尖上的凝露映射朝陽,其姿色與風情,可謂泠然,可謂清絕,美好得叫人無可如何。
錢鍾書當年鄙視吳宓之為人,罵其無行,順便牽連到他苦戀的毛彥文,用英文諷刺她是“年老色衰的風騷娘們”。其實這個風騷娘們年輕時是養眼的,即使老了,也有清氣,鄉語謂之“清絲絲的”。
天空之下,大地之上,一切原生之物,本質、天然、樸素、至美,沒有不好看的。不好看的,往往是過度變異的人,迷失了天性本心的人,被欲念和利益禁錮的人。不好看的,是人發明制造出來的諸多反生命反自然的物事,譬如槍炮、塑料、地溝油和海洛因。
在大別山里,一個從前幾乎是大荒之境而今依然存有古人遺風的小城,我活了很久。居住在青山之中,浣洗在綠水之畔,日日月月與草木鳥獸、白云蒼狗、園蔬籬落為伍,感覺不到日月飛逝老之將至,以為這一具皮囊,可以與草木同春,與鳥獸同秋。
梅雨季初來的一天,一夜風雨大作之后,第二天望見滿目夏花,石榴、荷花玉蘭、女貞子、一年蓬的花,又望見滿樹膨大的果實,毛桃、五月桃、紅梅和紅葉李的果實。這些夏日習見的花果,我見過數十回了。從前見了,覺得好看而已,心里喜悅而已。那一天見了,忽然想到《知北游》,莊子在文章里說:“忽然而已”。天地自然不老,任他白駒過隙、黑駒過隙、棗紅駒過隙。山川草木不老,由他冬春夏秋。人生易老,一回相見一回老,一生能見此情幾遭,能見此景幾回?
那一天,晨光明亮灑了一身,一念至此,眼前忽然就暗淡了一些。
生活仍然繼續,貌似轟隆其實寂寂地繼續。
在山野里,我以草木鳥獸為師,盡量遵從生物的本能和本性生活,衣但求暖,飯但求飽,住但求安,行但求穩,以為如此就好。安妥肉身之外,以書籍喂養精神,以文章抒發懷抱,以為文章載道,文章也載性。
我是說盡量,因為這種遵從很顯然是不可能的。長安米貴,居大不易,活著并不容易,遵從本心活著更是癡心妄想。但寫作的人,都是耽于妄想的人,所謂妄想,姑妄想之。也都有程度不同的癡心與癡氣,像大觀園里的香菱學詩藝。曹雪芹于這一節寫得尤其細微:“香菱聽了,喜的拿回詩來,又苦思一回作兩句詩,又舍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
寫作將近三十年,持續許多歲月而癡心不改,根子里,是有與時間抗衡的執念或者說妄想的。與時間抗衡,這顯然更加不可能。歲月如馳,馳馳啊,“日馳馳焉而旬千里”。古今人的傳世文章,浩浩洋洋,留在石頭、獸骨、龜甲、竹木、絹綢、紙張中,鍥刻在時間之上。轉念一想,古今那些以文章為性命的人,癡癡復癡癡,有幾人活過了百歲,又有幾人文章傳世?
但愿文章老厚,但愿肉身長葆草木精神,但愿年年寫得幾篇好文章。
草木溫柔敦厚,樸素質直,一如上古的大人君子。《周易》《山海經》《詩經》《楚辭》《漢樂府》《古詩十九首》里,篇什草木華滋。自此而下,古今人的詩詞曲賦和文章,一路草木蓊茂。風行草上,風行木上,時間的風吹過草木,吹過人世。草木不言,生來離離繁盛,枯后養息待發,生死榮悴等閑視之。與上古的大人君子相比,草木更符合《周易》之“易”的內涵:簡易、變易和不易(不變)。
古人說,要多識草木鳥獸之名,又說,要多識前言往行。
久居山野,人在草木鳥獸間,草木鳥獸之名,我識得的萬不及一。某一天我看見一只大鳥走路,像人一樣邁開前后腳,左右左,一二一,又看見一只小鳥走路,它是雙腳并立蹦跳著走的,一跳又一蹦。這兩種鳥在大別山中尋常可見,我不識其名倒也罷了,當時還好奇它們走路的姿勢竟然如此不同。后來一拍腦殼,哦,它們的腳有長有短。
至于前言往行,前代圣哲的言語行事,也與草木一樣敦厚溫柔、質直樸素,像先秦的詩歌一樣,更是難以效仿和企及。
草木樸素,世道人心原本素樸。從孩提時起,就與青梅竹馬的伙伴一起埋鍋造飯:杜仲的葉子錘得像絲綢,拿來當菜;紅芋的莖塊用石片切一切,拿來當飯;折斷蒿子的莖桿,拿來當筷子;松針摟一抱,拿來當柴。五六開襠童子,做飯吃飯裝腔作勢,吃得快活,耍得快活,像草木鳥獸一樣快活。
后來漸漸長大,身條漸舒,喉嚨漸粗,心漸大,漸漸不可收拾。漸漸不可收拾的,不僅是容顏,這舊日的好河山,還有心性,這與陰山巖畫一樣古老的本心。
熱愛草木,景慕草木,親近草木,是本心本性。我們的祖先以草木為衣,以草廬為屋,腳穿芒鞋手執木杖,都很閑,像草木鳥獸一樣閑,像雨點、朝霧、夜星、流水一樣閑,閑得夜夜天天思考來處和去處。我們都很忙,忙得忘記來處和去處,忘記自己本質上是一只動物。
愿心常常閑,愿文章常常有草木氣,愿活著常常有草木心。
我也有一時茍且,我也有許多草木文章。
放 膽
日月星辰,這是天的紋理;山川原野,這是地的紋理;“素履之往,獨行愿也”,這是心的紋理。天的紋理謂之天文,地的紋理謂之地理,心的紋理錄于紙上謂之性情文章。
我有幾卷性情文章,你有陳年老酒不?若有,何不學古人慷慨,“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據說,有青樓鴇兒向蘇東坡虔誠討教寫文章和飲酒的秘訣。
鴇兒問曰:“先生向不善飲,而以文名世,何以臻此,愿聞垂教。”
坡公稍稍沉吟,道:“文章無竅,唯率性耳;酒事無量,唯放膽矣!”
這段對答,是我從他人文章中拾來的,似乎不見于史乘和前人筆記。但書海泱泱、文山蒼蒼,這一典故或許就藏在哪一部我未曾讀過的書里也未可知。即使是后人杜撰,也杜撰得好,很接近坡公的言語行事風格。
言行,君子之樞機;文章,心跡之表露。
一人有一人的言行,一人也有一人的文章。
近年時常溫習坡公著作,越發以為東坡文章是天人之合,有仙狐鬼怪相幫襯。又時常讀張岱,越發以為張宗子文章離經叛道超凡入圣,亦有神鬼暗中撮合。蘇子《記承天寺夜游》《文與可畫筼筜谷偃竹記》《超然臺記》諸篇什,張子《湖心亭看雪》《揚州瘦馬》《瑯嬛福地記》諸作品,放膽直下,率性成文,令人翩躚欲舞謳啞欲歌,妙不可言。我愿效仿鄭板橋和齊白石膜拜徐渭,文章以蘇東坡和張宗子為師,甘作其門下走狗。
席上飲酒,古人以戎事作比,謂之“酒兵”,兇險之事也。放膽,就像霍去病率漢家輕騎出隴西橫掃匈奴,奪其焉支、祁連二山,使其六畜不蕃息,令其婦女無顏色,非胸中有文韜武略又膽子極肥者不能。
率性,順其本性,從其天然之性,于三歲童子容易,于塵垢蒙了身心的成人卻難。這本性,原是天所賦之,在塵世里幾番滾爬早已失去,想撿拾回來,得靠后天不懈地涵養、修為。如《周易·系辭上》所言:“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不斷蘊存和涵養,以成全天性,讓它存續不斷,就找到了進入道和義的門戶。
因之,率性和放膽,貌似信手拈來人人可為,實則,能率性寫出絕妙文章的人,與能放膽喝得雄姿英發如坐春風的人,都非凡人,風徽足式。于前者,我心有所慕,雖明知前輩風誼難以企及,但既然視文章為盛美的事業,就只有放膽、放蹄直追,此外似無他法。我心恒定,如鄉語所云:“瞎子看牛,死一拽著。”
自家意思
檐雨落在青石板上,作木魚聲。
舊年的絲瓜吊在木蘭上。
金絲桃黃花照眼明,色艷而氣清。
夏水渾渾茫茫,一路波折東進,站在河邊望大水的婆娑老叟藏往知來。
檐雨、絲瓜瓤子、金絲桃、逝水和出塵又入世的老者,都有自家意思。天地化育萬物,萬物各有天命。所謂天命,自然稟賦也。仔細體察,日月星辰雷電霜雪,山岳湖海草木鳥獸,屋漏之痕,折釵之跡,冰凌之鋒,晨露之凝,玉石之橫紋,嬌俏佳人之眼波,西楚霸王槍戟之厲風,莫不有自家意思自家面目。所謂自家面目自家意思,一家之言行,獨有之風貌。
我友習書廿三載,以古今妙手為師,以北碑南帖為師,以造化自然為師,手摩心畫日習夜練,硯中墨不干,手里筆常禿,主攻篆、隸之外,兼習楷、行、草諸體。觀其字晉長多年,以為其篆、隸二體,風力雄樸氣勢端凝,漸近古人,漸近自然,也漸有自家意思自家面目。
習書之余,他課徒設教,誨人不倦桃李芬芳,山城書藝后繼有人,有其功勞。
當年,張旭在鄴城街市觀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豪蕩感激,得自家草書心法。索靖傳張芝草法而變其形跡,骨勢峻邁妙有余姿,創自家銀鉤蠆尾字勢。衛夫人《筆陣圖》言:“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也。”她說的是書法之道,其實一切文學藝術之道,“六藝”之道,旁及耕讀漁樵之道,木、漆、瓦、鐵、篾、焗、庖諸百工之道,莫不如此: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之神妙。所謂通靈感物,通而后靈,睹物興感。
通靈,不是不易,而是太難。以書道言之,文字者,象形也,故而首當通文字之學,也即“小學”,知字形之所以然。其次當通古今書法源流變,知字勢之所以然。又當通文章典籍、山川地理、自然物象、人情世事,盡窺眾妙之門,養器識與氣度。博而通,通而感,感而激,激而靈,然后才會成一家面目一家意思,才可以神游于尺幅之上,瀉胸中之丘壑,潑紙上之云山。
大匠通靈。匠本是技,但匠之大者,其所操之技也是藝,也是道。大匠可以通天地鬼神。
我友心地敦樸,人也靈醒勤苦,其書藝精進指日可期。愿其通靈感物,符采克炳,早成大匠大藝大方之家。
(選自《安徽作家》,2022年第三期)
作者簡介

儲勁松,安徽岳西人,中國作協會員。作品見于《青年文學》《天涯》《山花》《長篇小說選刊》等,著有《雪夜閑書》《草木樸素》《黑夜筆記》《書魚記:漫談中國志怪小說·野史與其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