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shí)間:2022-11-14 來(lái)源:安徽作家網(wǎng) 作者:安徽作家網(wǎ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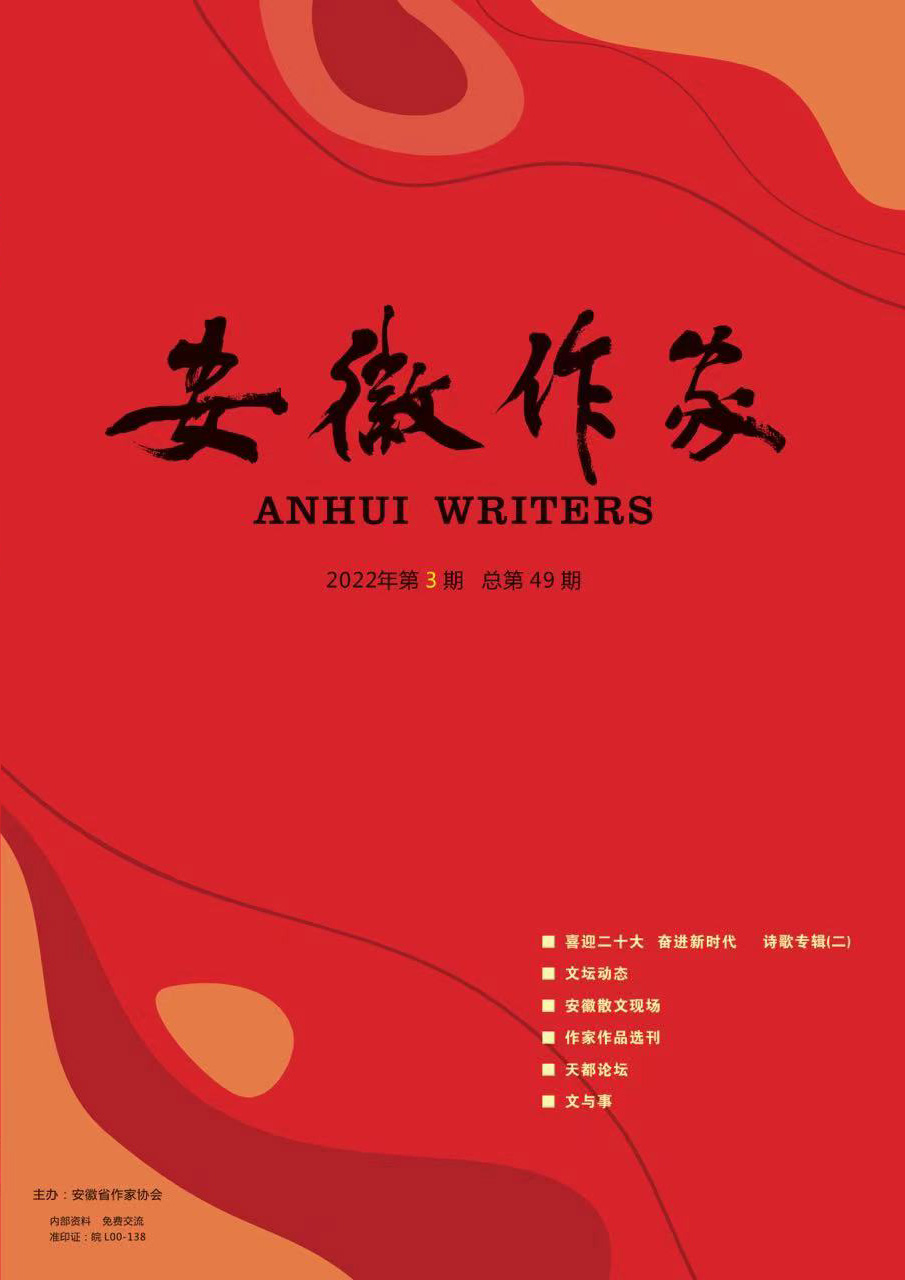
散文觀:散文不好說(shuō),一說(shuō)就走樣。還是呼應(yīng)自己內(nèi)在的情感為好。回歸自在世界,表達(dá)真實(shí)訴求,不佞妄,不偽飾。感受生活的溫度,開掘心靈的深度,打磨思想的亮度。如此而已。
許俊文
秋天是我喜愛的季節(jié),這可能暗中與我出生的時(shí)辰有著某種關(guān)聯(lián)。母親活著時(shí),曾不止一次埋怨自己的記性差,忘了我的生日,但他卻清晰地記得我來(lái)到這個(gè)世界時(shí),是在一個(gè)露水很重的秋晨。當(dāng)時(shí),她拖著沉重的身體走進(jìn)一片晚熟的稻地,發(fā)現(xiàn)前幾天收割后留下的一簇簇水稻茬口上,聚集著一捧一捧的露水珠子,水銀似的晃眼。她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發(fā)現(xiàn)每一顆晶瑩的青露下面,都藏著一個(gè)錐形的小腦袋——次青(收割后的稻根二次發(fā)的嫩芽)。母親的這一段鮮明的記憶,說(shuō)明我是頂著秋天的寒露撲進(jìn)皖東一個(gè)名叫豆村的小村莊,因而,我的第一聲啼哭,想必也就自然而然地留在了露珠里。
我曾在一篇舊文里寫下這樣的句子:一座被樹木、莊稼和野草包圍的村莊,也被露水包圍著。露水與樸實(shí)、懷柔的鄉(xiāng)村,有著天然的血脈聯(lián)系,它是土地的孩子,質(zhì)樸,純凈,又有著頑皮的天性。在露水遍地的清晨,它會(huì)以自己的方式迎接早早下地的人們,伸出微涼的小手弄濕他們的褲管和鞋子,并將微小的草籽和花粉粘在上面,對(duì)此,人們并不介意,誰(shuí)家的孩子能不做出一兩件淘氣的事兒呢?要是在收獲季節(jié),人們最擔(dān)心落雨,尤其是那種延綿不斷的連陰雨,像一個(gè)潑皮無(wú)賴的小人趕都趕不走。黃透的稻子捂在地里,長(zhǎng)期經(jīng)受雨水的浸泡,眼睜睜地看著它發(fā)芽或霉?fàn)€掉。因而,此時(shí)的露水就成了治療人們心疾的靈丹,一顆小小露珠的出現(xiàn),它所給予的救援,往往要?jiǎng)龠^千軍萬(wàn)馬。
那年代,水稻產(chǎn)量極低,生產(chǎn)隊(duì)種植的主要作物只能選擇紅薯。人們?cè)谑斋@了紅薯之后,除了一部分窖藏留種,大多切成薯片,撒在山坡、院壩或翻耕過的犁垡地里晾曬。這個(gè)當(dāng)口,人們對(duì)天氣就格外地操心,要是遭遇了陰雨天,一年的辛勞和口糧就會(huì)泡湯。這時(shí),所有人的目光就投到了的露珠上,那平時(shí)百無(wú)一用的露珠似乎突然間就變成了生死攸關(guān)的“通靈寶玉”。我曾納悶,不就是一顆顆小小的露珠嗎,人踏畜踐的,它們?cè)谌藗冃闹械姆至恐p,還不如那些禍害莊稼的蟲子,每當(dāng)?shù)乩锇l(fā)生了蟲災(zāi),滿村的人便“蟲子”、“蟲子”的喋喋不休,仿佛屁股上著了火似的,一片驚慌和大呼小叫;而短命的露珠顯然沒有這種讓人誠(chéng)惶誠(chéng)恐的能耐。
現(xiàn)在該請(qǐng)露珠出場(chǎng)了。那是深秋的一個(gè)夜晚,父親在磨好了刀片,準(zhǔn)備切紅薯之前,差我到門前池塘邊的草叢里試試起沒起露水。屋外黑得一塌糊涂,只有幾只流螢伏在草棵上發(fā)出微亮的光點(diǎn)。因?yàn)榭謶郑颐榱艘谎劬桶瓮扰芑亓思摇8赣H問我起露水了嗎?我吱吱唔唔地語(yǔ)焉不詳。這時(shí)他拽過我的手摸了摸,說(shuō)你的手焦干焦干的,到底摸沒摸草葉子,我見父親如此鄭重其事,只得實(shí)話實(shí)說(shuō)。于是,父親拉上我重新來(lái)到池塘邊,他在黑暗中將手在草葉上劃拉了幾下,不無(wú)興奮地,有了有了!這一招十分靈驗(yàn),次日果然是個(gè)朗晴的天。看,那毫不起眼的小小露珠,居然如此神奇,它不僅暗藏著天地乾坤神秘莫測(cè)的機(jī)密,還影響著一家人的生計(jì)。從此,我對(duì)露珠便另眼相看,生出一些敬畏來(lái)。其實(shí),又何止于露珠呢?我們身邊那些微小的事物(包括暗物質(zhì)),都是有靈有魂的,它們雖然不言、不議、不爭(zhēng),但冥冥之中想必與上蒼有著某種微妙的聯(lián)系,它們的興與衰,榮與枯,都不是沒有緣由的。
如此神通廣大的露珠,卻是安靜的。反正我從來(lái)沒有見過露珠浮躁或失態(tài)過。露珠的安靜,是那種圣哲與高僧般的大寂大靜。它不像樹木,樹木雖說(shuō)也有根,但卻經(jīng)不起風(fēng)的三蠱兩惑,心性就開始動(dòng)搖了;也不似池塘里的魚,別看它風(fēng)和日麗時(shí)悠然得像個(gè)君子,可是氣壓稍微高那么一點(diǎn)點(diǎn),它就不得不上躥下跳,失了態(tài)。露珠不,它來(lái)了就來(lái)了,靜悄悄地;走了就走了,也是靜悄悄地。露珠使我想起村莊里的一些人,他們一輩子守著土地和莊稼,最后連土地和莊稼也侍弄不動(dòng)了,一撒手,走得好從容,多安靜啊!
在我的豆村,稍有點(diǎn)農(nóng)事常識(shí)的人都懂得,你別瞧不起與草為伴的露珠,其實(shí),哪一茬莊稼都離不開它,這使我想起一件舊事。那是一個(gè)只相信精神的蠻干時(shí)代,與我們豆村毗鄰的麻嶺生產(chǎn)隊(duì),用錘子和鋼釬硬是將半座山頭夷為平地,發(fā)誓要在上面奪高產(chǎn),創(chuàng)奇跡。正準(zhǔn)備下種時(shí),曾在地主家扛過“大鍬把子”的半瘸子站出來(lái)放了一炮,他說(shuō),那個(gè)地方長(zhǎng)不了莊稼,種,也是白種。生產(chǎn)隊(duì)長(zhǎng)是個(gè)熱血青年,當(dāng)時(shí)正在積極追求政治進(jìn)步,哪里聽不進(jìn)一個(gè)“階級(jí)異己分子”的胡言亂語(yǔ),他依然我行我素,照種不誤,可是結(jié)果呢,十幾畝的地,耗費(fèi)了許多人工,可是到頭來(lái)連老種也搭了進(jìn)去。事后隊(duì)長(zhǎng)半威半就地問半瘸子,你怎么就知道那地不能種?半瘸子說(shuō),你先給我一根“大鐵橋”(一毛四分錢一包的香煙),我再告訴你。隊(duì)長(zhǎng)沒轍,就暫時(shí)放下架子照辦了。半瘸子接過從未吃過的香煙,點(diǎn)燃后有滋有味地嘬了幾口,陡然來(lái)了精神,竟忘了自己的身份,粗聲大嗓道,那是新墾的生地,連露水珠子都不肯落腳,說(shuō)明它不成熟,你讓它長(zhǎng)莊稼,不等于在鍋臺(tái)上撒種嗎?半瘸子瞅瞅生產(chǎn)隊(duì)長(zhǎng),見其人面色平靜,又大膽補(bǔ)了幾句:種地可不是娶新媳婦,半年不要就能懷上伢仔。要我看,那樣的地,最好撂它個(gè)三年五載,等野草扎下了根,蓄足了精氣,把露水引來(lái)了,再種也不晚。
半瘸子說(shuō)得在理,露水雖然不會(huì)說(shuō)話,但它也懂得暗示,就看你能不能參透它的玄機(jī)。據(jù)我的仔細(xì)觀察,凡是露水多的地方,野草和莊稼生長(zhǎng)得都比較茂盛,道理很簡(jiǎn)單,因?yàn)槟莾和寥郎詈瘢畹米∮晁У米〉貧狻O嘈棚L(fēng)水的我祖父還有另外一種說(shuō)法,他說(shuō)露水是天地的造化,一塊土地氣血旺不旺,一茬能出多少糧食,早晨起來(lái)看看露水就明白了。這話雖然說(shuō)的有些玄,但管用,經(jīng)得起檢驗(yàn)。我們豆村下禾灣有一片落淤地,種啥都發(fā)旺。為啥?露水養(yǎng)的唄。那一片地,如果是正常年景也看不出與其它土地有多大差異,若是遇到了大旱,別的土地上的禾苗蔫兒巴幾的,而落淤地上的莊稼卻每一棵都精神,葉子油汪汪的;特別是清晨看上去,好像帝母一不小心打翻了珠寶罐子,滿地的露水珠子晶瑩透亮,耀得你眼睛都發(fā)暈。你看看,一個(gè)很玄秘、深?yuàn)W的問題,憑幾顆露水珠子就輕而易舉地解決了。
豆村的“二神仙”說(shuō)得就更玄乎了。他說(shuō),凡物必有用,你可別小瞧了一顆露水珠子,它如果沒用,也不會(huì)空占一片草葉子的。露水這東西,沒它,莊稼雖然也能長(zhǎng),但長(zhǎng)得不活泛,牛羊也照樣吃草,可是吃草與吃草不一樣。我家隔壁的李長(zhǎng)青老人,沒兒沒女,地種不動(dòng)了,就靠養(yǎng)幾頭羊維持生計(jì)。每天老人總是早早地打開圈欄,把羊趕到豆青山上去吃露水草,老人也用不著照看,獨(dú)自捧著個(gè)煙桿坐在門口吃他的煙。得了露水草的羊,安靜得像遁入了天堂似的,只顧低頭吃草,露珠和草汁把羊的嘴唇和舌頭都染綠了。李大爺跟我說(shuō),羊愛吃頭道草,因?yàn)轭^道草上有露水珠子,嫩著呢,養(yǎng)口。要是走在前邊的羊把草葉上的露水珠子碰落了,后邊的羊會(huì)往前趕,搶吃第一口露水草。李大爺家吃露水草的羊長(zhǎng)得快,風(fēng)吹也似的,膘看著看著就起來(lái)了,身子滾圓滾圓的,李大爺曾對(duì)買羊的人說(shuō),咱的羊是喝仙露長(zhǎng)大的,肉嫩得入口就化。
大概是出于孩童的好奇心吧,我曾仔細(xì)觀察過露珠的來(lái)路,我蹲在霧氣氤氳的田野上,看一顆露珠從一棵稻秧的根部緩緩升起,它像一顆掙脫黑暗的小太陽(yáng),順著莖桿悄無(wú)聲息地爬上葉片,挪一點(diǎn),歇一會(huì)兒,挪一點(diǎn),再歇一會(huì)兒,每一次挪動(dòng)和間歇,都會(huì)壯大那么一點(diǎn)點(diǎn),最后在葉端停止了腳步,整個(gè)過程大約需要半個(gè)鐘頭。這可不是一條平坦的路啊,每上升一小步,露珠都要付出極大的努力。我想,那棵稻秧是應(yīng)該懂得感恩的,它用毛茸茸的手掌托著露珠,其專注與珍惜,并不亞于我們托著一件價(jià)值連城的古瓷器輕松與小心。
我的觀察與發(fā)現(xiàn),其實(shí)遠(yuǎn)遠(yuǎn)滯后于古人。很久很久以前,我們的先人就從微小的露珠里窺見大自然的秘密,他們?cè)趧澐止?jié)氣時(shí),竟慷慨地拿出兩個(gè)席位讓給了卑微的露珠,一個(gè)是“白露”,一個(gè)是“寒露”。在我的故鄉(xiāng)豆村,人們習(xí)慣于稱“寒露”叫青露。也就是在我寫這篇小文的一個(gè)月之前,樹葉草叢里的露珠還是白色的,然而在時(shí)間的滴答聲中,不知不覺就變成了青色,而它的體溫漸漸地由“微涼”暗轉(zhuǎn)為“輕寒”了。這一細(xì)微的漸變,也無(wú)法逃過古人銳利的目光和靈敏的感知,他們那細(xì)致入微的生命體驗(yàn),遠(yuǎn)勝于今天浮躁的我們。現(xiàn)在,當(dāng)我們遙想那片古老的深秋原野,不禁會(huì)問,是怎么的一位先民忽而覺出了今朝的露水不同于昨夜?那有別于“白露”的第一滴寒意,究竟是滴在他的腳背,項(xiàng)脖,還是他的舌尖呢?
宇宙浩茫,大地廣袤,一滴起于黃昏,穿越長(zhǎng)夜的露水,凝聚在芊芊的草葉上,滴落在時(shí)間的幽深里,它所傳達(dá)的天地之氣,彌漫在古人感謂人生與世道炎涼的詩(shī)句中,經(jīng)久不散。
見證一滴露水的誕生、漸變與墜落,即便你的心再硬,我相信也會(huì)變得柔軟起來(lái)。
大雪那天下了大雪。這是冰心先生說(shuō)的,也是我祖母說(shuō)的。我的祖母一生窩在皖東那個(gè)渾如一粒豆子的小山村,她壓根就不知道這個(gè)世界上還有一個(gè)叫冰心的老人,與自己說(shuō)過同樣淺顯而深刻的話。
大雪那天下的雪,不是小雪,更不是虛構(gòu)的雪。那紛紛揚(yáng)揚(yáng)的雪花,不偏不倚地偏偏下在“大雪”節(jié)氣那一天,深藏其中的秘密,又偏偏被有心的冰心和我的祖母發(fā)現(xiàn)了。當(dāng)然,其他人也經(jīng)歷了那場(chǎng)雪,但是,他們只看到了雪,并未將雪與某種恒久的非物質(zhì)的東西聯(lián)系起來(lái)。我猜想,這兩位老人所說(shuō)的雪,肯定不是同一場(chǎng)雪,它們一個(gè)落在北方,一個(gè)落在皖東。但是,肯定都是“大雪”那天的雪,且是豐盈的大雪。這其中,是否暗藏著某種微妙呢?
其實(shí),剝離掉知識(shí)和其他后天因素,人在本質(zhì)屬性上對(duì)自然的感知力是相差無(wú)幾的,不論你是大名鼎鼎的冰心,還是我那目不識(shí)丁的祖母。長(zhǎng)年在土地上勞作的人就更勝一籌了。寒冬將盡時(shí),地面上仍零零星星地遺留著一些殘雪,像一帖帖臟兮兮的膏藥貼在土地上,賴著不肯走。然而,人們卻從草叢里蚯蚓翻出的一坨坨新鮮的泥漿,便知道春天已經(jīng)從地下潛行而至了,并不需要花朵與草芽來(lái)證實(shí)——他們有這個(gè)把握。在莊稼人眼里,花花朵朵算什么呀,它們頂多像時(shí)下那些走場(chǎng)作秀的明星,只為坐實(shí)的春天捧捧場(chǎng)而已。
對(duì)于自然,豆村人有著異于常人的感知。譬如下霜,在我的家鄉(xiāng)就不叫下霜或落霜,而是叫上霜。顧名思義,寒霜是地氣化作水汽遇冷而凝成的結(jié)晶體。地氣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想必是帶著細(xì)弱的微溫裊裊升騰的,在它脫離了大地的母體之后,就不得不接受命運(yùn)的改造了——?dú)怏w死了,而一個(gè)新的生命卻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僅憑這一點(diǎn),當(dāng)你再吟誦“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時(shí),或許會(huì)洞見白露與寒霜背后潛伏著的天道,深邃、精微與傳神,真是妙不可言。
秋末或初冬的清晨,當(dāng)人們推開門窗,忽見一地素潔、晶瑩的寒花,自會(huì)不驚不乍地咕噥道:哦,上霜了。其實(shí)在此之前,他們心中早就有譜了。你別以為鄉(xiāng)村雜亂無(wú)章,人也活得懵懵懂懂、毛毛糙糙,但是他們卻深諳自然之道,一陣風(fēng)從哪里來(lái)往哪里去;一朵杏花早開或遲開幾天,一只鳥窩壘在高處或地處,他們都能從中窺見奧義。對(duì)于霜的認(rèn)知,我也是從他們那里得來(lái)的。一場(chǎng)鋪地的嚴(yán)霜君臨之前,泥土通常是溫潤(rùn)的,天氣是晴和的,而空氣卻十分的干冷。上霜的過程非常微妙,干冷的風(fēng)像是一根神奇的繡花針或一把刻刀,在潮濕的草葉上,循著葉脈的紋理繡(刻)出一朵朵霜花來(lái)。這個(gè)過程就好比一根鏈條,缺了哪一節(jié)都不行。這是人工所無(wú)能為力的。
下雪也是如此。詩(shī)人描摹下雪的情景可以大而化之,譬如“晚來(lái)天欲雪,能飲一杯無(wú)?”。就這么籠統(tǒng)的不著邊際。究竟怎么個(gè)“欲”法,并沒有明說(shuō),也不便明說(shuō),只是留下巨大的空白好讓我們?nèi)ハ胂螅ヌ畛洹R晕业挠^察與體驗(yàn),“天欲雪”是有征兆的,就像一個(gè)人饑餓了,空癟的肚腸自會(huì)發(fā)出咕咕的鳴響。一場(chǎng)大雪即將登場(chǎng)時(shí),寒風(fēng)瑟瑟,暮云低垂,大地出奇的緘默,天地之間一片黯淡、渾茫,放眼望去,落光葉子的樹木挺著腰桿,鳥無(wú)蹤影,世間的一切都仿佛在靜靜地等待著某位神靈的君臨。
祖母把這種現(xiàn)象稱之為“捂雪”。大凡浩大場(chǎng)景和重要事件,在它們生發(fā)之前總不會(huì)把底牌一下子亮出來(lái),它們得慢慢地醞釀、集聚、蓄勢(shì)。比如這大雪的雪,蒼天就把它嚴(yán)嚴(yán)實(shí)實(shí)地捂在懷里,等捂熟了,捂出了大境界,大氣魄,便借著呼呼的風(fēng)勢(shì)將衣襟猛地一抖,撲簌簌的雪花自茫茫蒼穹而降,飄飄灑灑幾百上千里,那陣勢(shì),不可謂不宏大、壯闊。
此時(shí)除了雪,世間的一切都顯得渺小了。
我就有這種感覺,置身于紛飛或靜謐的茫茫雪原中,仿佛有種無(wú)聲之聲讓我不得不安靜下來(lái)。此時(shí),經(jīng)過過濾的內(nèi)心是如此的潔凈、豐盈,明澈的思緒會(huì)不由自主地與莽莽蒼蒼的宇宙、起起伏伏的人生這類大問題發(fā)生聯(lián)系,愈發(fā)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
一場(chǎng)又一場(chǎng)的雪,不違時(shí)令地飄落大地,就像一位守信踐約的故友,它在該來(lái)的時(shí)候一定會(huì)來(lái)。我們現(xiàn)在經(jīng)常會(huì)說(shuō)以上率下,以我的理解,這個(gè)“上”,不僅僅指高高在上的權(quán)力,而是超越其上的某種不可違逆的輪回之道。天道。其實(shí),它就是一面鏡子,既制定法則,也守恒法則,從不像某類人那樣,一旦得了勢(shì),就可以胡來(lái)。
在季節(jié)周而復(fù)始的輪回中,雪,早春它是檐前滴滴答答的雨水;暮春,它是煙色迷蒙的谷雨;初秋,它是草尖晶瑩剔透的白露;深秋,它是葉上的寒露與白霜。一朵來(lái)到世間的雪花,循規(guī)蹈矩地走著一條上帝設(shè)定的路線,它不走偏鋒,也不繞道而行,在周而復(fù)始的生命輪回中,遵循著自然的律法,它自己也成為別人的律法。
在我的故鄉(xiāng)豆村,每年都會(huì)降下幾場(chǎng)雪,一般以小雪居多。細(xì)細(xì)碎碎的雪花,像撒蕎麥面似的,均勻地隨風(fēng)潛入草叢、林藪、池塘,它們落地的聲音,窸窸窣窣的,有點(diǎn)近似于春蠶深夜啃食桑葉發(fā)出的沙沙聲,優(yōu)雅動(dòng)聽。因?yàn)槠湫《椋话悴粫?huì)在人們的內(nèi)心引起多大的震動(dòng),它落了就落了,化了就化了,就連像我這樣關(guān)注節(jié)氣和物候的人,都記不清哪一場(chǎng)小雪落在什么時(shí)候。
在二十四節(jié)氣中,有些時(shí)間的節(jié)點(diǎn),給我們的感覺面目比較模糊,譬如雨水、春分、小暑、小滿、白露、小寒等,現(xiàn)在的城里人對(duì)諸如谷雨、芒種、秋分、寒露等,也是模棱兩可,習(xí)焉不察,仿佛它們都是與己無(wú)干的身外之物,他們似乎只在乎自己的生日,鮮花、蛋糕,酒肉、自拍,呼朋喚友推杯換盞地?zé)狒[一番。其實(shí)他們忘了,每一個(gè)時(shí)間的節(jié)點(diǎn)都是自己的生日,也都是自己生命旅程中的一個(gè)驛站。天地悠悠,大道輪回,這世間的萬(wàn)類萬(wàn)物,誰(shuí)又能夠逃脫渾然不覺但又如影隨形的自然法則呢?
而我的豆村,人們對(duì)天道自然是敬畏的,他們不像城里人活在人造的環(huán)境中,因而更接地氣。送走了一茬莊稼或一位老人,與一場(chǎng)寒霜和一場(chǎng)大雪都息息相關(guān)。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置于節(jié)氣的輪回之中。我干爹李長(zhǎng)青老人,活成了豆村的一棵常青樹,他九十多歲還能侍弄莊稼,人們就戲謔地說(shuō)他是被閻王從花名冊(cè)上漏掉的人。你猜我干爹怎么說(shuō)?他說(shuō)自己不就多見了幾場(chǎng)雪嘛,這場(chǎng)不收,下一場(chǎng)說(shuō)不準(zhǔn)就被收走了。他說(shuō)這話時(shí),還是挺精神的。然而,就在當(dāng)年冬天的一場(chǎng)大雪降下之后,他老人家說(shuō)走就走了。他像是從一滴檐前的雨水過度到一朵雪花一樣,完成了自己生命的一個(gè)輪回。
像我干爹這樣的老人,在豆村并不少見。約是七八年前吧,我在寒風(fēng)刺骨的深冬回到故地,發(fā)現(xiàn)幾位老人靠著墻根在曬太陽(yáng)。那冬陽(yáng)像一盆炭火的余燼,散發(fā)著幽微的溫度,老人們就借著它取暖,安詳?shù)卮虬l(fā)余生。當(dāng)時(shí),我沒有看到那些已進(jìn)入冬天的老人的表情上有任何不安與恐懼,相反,他們卻個(gè)個(gè)都保持著豁達(dá)、樂觀的情緒,他們談?wù)撍劳鼍拖襦竟献右粯与S意。其中一位年長(zhǎng)的扯起話頭,他說(shuō),于大個(gè)子要是能熬過去年的那場(chǎng)大雪,也許還能多活一年。在說(shuō)者的意識(shí)里,去年冬天的那場(chǎng)大雪,就是橫亙?cè)谟诖髠€(gè)子命途上的一道大坎。另一位老人則反唇相譏:就算他熬過了去年那場(chǎng)大雪,還有下一場(chǎng)雪呢。這話一經(jīng)說(shuō)出,在座的老人都沉默不語(yǔ)了。是的,他們現(xiàn)在正處在“下一場(chǎng)”大雪來(lái)臨之際。自然界的一場(chǎng)大雪,詩(shī)人會(huì)說(shuō)“夜深知雪重,時(shí)聞?wù)壑衤暋!薄6?dāng)“下一場(chǎng)”大雪真的降臨大地,這些在冬陽(yáng)下談笑的老人,又會(huì)有誰(shuí)像竹子一樣被折斷呢?
似乎只有天知道了。
不過,我在次年大雪之后再次回到豆村時(shí),發(fā)現(xiàn)去年曬太陽(yáng)的老人中,又被雪走了兩個(gè)。
而今,一路穿越過無(wú)數(shù)次霜降、小雪、大雪的我,已經(jīng)越來(lái)越接近冬天了。有時(shí)我會(huì)想,屬于自己生命里那最后的一場(chǎng)大雪,也許還在某處醞釀著,它肯定會(huì)在該出現(xiàn)的時(shí)間出現(xiàn)。它是我的終結(jié),也是我的開始。
人能夠在一朵雪花上輪回,想想,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選自《安徽作家》,2022年第三期)

許俊文,1954年生,安徽省定遠(yuǎn)縣豆村人。種過地,教過書,當(dāng)過兵。畢業(yè)于解放軍藝術(shù)學(xué)院。2002年因病提前退休,現(xiàn)定居皖南美麗小城池州,供職于杏花村文化旅游發(fā)展有限公司。先后8次獲得安徽省報(bào)紙副刊年度優(yōu)秀作品一等獎(jiǎng)及安徽省文學(xué)獎(jiǎng)。
散文觀:散文之散,我的理解是抒散,是散發(fā),是無(wú)有拘束。散文由心而發(fā),呼吸吞吐,用的是氣息。莊子里說(shuō)“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氣息之壯可像野馬奔騰,之廣茫可像紛揚(yáng)塵埃。散文沒有依托,有故事無(wú)故事皆可,可深可淺,可大可小。厘清自己的內(nèi)心,自由呼吸,就能寫出好散文。
許含章
許村古稱“富資里”,這在今天,還依稀可窺見端倪。街景雖是蕭條的,且我們到達(dá)時(shí)已近黃昏,但短短幾百米的一條街上,光是金店仍開有好幾家。臨街有些破敗的老房子,斑駁的磚墻上寫了大大的“拆”字,用觸目的紅筆圈起,仿佛最后的判決。到處可見禁止賭博的標(biāo)語(yǔ),在打工人群未歸的早秋時(shí)節(jié),略略顯得有些寂寞。
金店的霓虹,一點(diǎn)一點(diǎn)亮起來(lái)了。
在皖南綿延數(shù)百里的徽派山水里,這是一個(gè)不起眼的小鎮(zhèn),可在我心里,卻一直暖著。在旅游業(yè)大熱的今天,皖南至江西婺源一線有“小川藏線”之稱,有山有水,有景有物,處處桃源洞天,曲徑通幽。可許村這個(gè)地方,雖然也隱于這片群山之中,卻似乎離這一切還很遙遠(yuǎn)。不僅老房子都不曾“穿靴戴帽”,重新加蓋馬頭墻,就連新建筑也與一般新農(nóng)村建設(shè)中西合璧的“小洋樓”不一樣,只是拼命地往高里蓋,似乎要以此向山外表明,自己也并不落伍。
“最高的有七層。”程大姐告訴我的時(shí)候,眼里隱隱有得意之色。她說(shuō)這話的時(shí)候,夕陽(yáng)正淡定地撒在鄉(xiāng)間小路上,將一切堂皇和破敗傾覆。
是水泥路,路兩邊有沒膝的蒿草。
一路走過來(lái),沿途只看到寥寥幾個(gè)老人和孩童,穿著從城市買回來(lái)的鮮艷的衣服。孩子身后的小書包上,有喜洋洋和灰太狼的商標(biāo)。鄉(xiāng)村正在城鎮(zhèn)化,從這里,或可窺見村莊的凋敝,和進(jìn)步。
程大姐是我在鎮(zhèn)上閑逛時(shí)遇到的,見我脖子上掛著相機(jī),便很熱心地要帶我去看老橋。皖南水多,便橋多,木橋、石橋、拱橋、板橋……數(shù)不勝數(shù)。據(jù)說(shuō)許村有二十二座古橋,像“和睦橋”這樣有名的橋,大抵在縣志中曾反復(fù)出現(xiàn)過。不過關(guān)于和睦橋,程大姐告訴我的,是一個(gè)流傳于民間的故事,說(shuō)的是舊時(shí)許村一對(duì)兄弟鬩墻,被鄉(xiāng)里所恥笑。有一日,兄弟二人重逢于這座橋上,摒棄前嫌,終于攜手重振家業(yè),如何如何。
都是一些老故事,配得上這樣的老橋。
夕陽(yáng)正在快速墜落,老橋斑駁的石縫里,長(zhǎng)滿了蒿草。
許村,許村,你是我的家園么?
許村的大家族當(dāng)然都姓許,歷史上出名的人物有光緒年間的大茶商許暢芝,還有“少年謂子氣橫秋,壯已邊城汗漫游”的南宋名臣許月卿,在有關(guān)許村的方志中,他們是家族的驕傲。當(dāng)然,這兩個(gè)人程大姐都不知道,她是跟著父親從江的上游下來(lái)的,在這里嫁了人,就定居下來(lái)了。我想她即便是許村的老戶,也未必知道這兩個(gè)人,她一個(gè)家庭婦女,上有公婆,下有兒女,中間還有丈夫要侍侯,她要知道這些干什么?
所以她對(duì)我問的一些問題,感到很驚奇。
她也從未聽說(shuō)過我的職業(yè),她問:“編輯是干什么的?”我說(shuō)是編書的,我沒有說(shuō)編雜志,那樣就更說(shuō)不清了。她很高興,要了我的筆,留了地址給我。她很關(guān)心她說(shuō)的話,能不能出現(xiàn)在書里,她說(shuō)小妹妹!你的書印出來(lái)了,一定要寄一本給我噢!
我說(shuō)一定一定!不會(huì)忘的不會(huì)忘的!
回來(lái)后我寄了一本我們的刊物,在里面夾了幾張打印出來(lái)的與她的合影。照片上,老橋拱起的橋洞里,夕陽(yáng)正在墜落,橋身上有紛披的蒿草。
在落款一欄,我填上了“外鄉(xiāng)人”三個(gè)字,但對(duì)于許村來(lái)說(shuō),我是外鄉(xiāng)人嗎?
不知道這本雜志,她收到了沒有?此后我們?cè)贈(zèng)]通過音信,畢竟對(duì)于許村,我們都是匆匆過客。
有的人是沒有故鄉(xiāng)的,而有的人則故鄉(xiāng)不止一處。
我的出生地是皖北的煤城淮北,在很長(zhǎng)很長(zhǎng)一個(gè)時(shí)期,我都把她認(rèn)作我的故鄉(xiāng),想起她時(shí),我會(huì)很安心。
是一座新城,東西向依山而建,從最東頭的東崗樓,到最西頭的電廠,也不過兩三里路。我小的時(shí)候,我媽媽帶我“上街”,一般是步行,長(zhǎng)長(zhǎng)的淮海路上,法國(guó)梧桐斑斕的闊葉上,陽(yáng)光如童話一般跳躍。30多年過去了,我至今記得深秋的淮海路上,鋪滿了金子一般的落葉,給人一種非常華麗的感覺。那時(shí)我多大呢?三歲還是四歲?反正是在上幼兒園之后,反正我媽媽已經(jīng)從武漢讀書回來(lái)了。她說(shuō)梧桐,法國(guó)梧桐,你金子般的落葉,多么奢華,多么美好。她類似的表達(dá),一路上會(huì)有很多。而在上幼兒園之前,我居無(wú)定所,一會(huì)兒在懷遠(yuǎn)老家,跟著我爺爺奶奶,一會(huì)兒又回到淮北,跟著一位我稱呼“韓奶奶”的老奶奶,我爸爸早晨把我送去她家,晚上下了班再去接我。韓奶奶很疼我,我到了上幼兒園的年齡,她仍然不想讓我走。我上了幼兒園之后,她有時(shí)會(huì)站在幼兒園的鐵柵欄外面,一動(dòng)不動(dòng)地看著我。我跑到柵欄邊,大聲喊:韓奶奶!韓奶奶!她就笑了,笑過之后,還會(huì)抹眼淚。
我媽媽說(shuō),韓奶奶30多歲就守了寡,一輩子過得很苦。我不怎么相信,她兒子是媽媽大學(xué)里的書記,我雖然小,這個(gè)我也知道。但我媽媽為什么要說(shuō),她一輩子過得很苦呢?有一次我看見,她和我媽媽說(shuō)她年輕時(shí)候的事,說(shuō)著說(shuō)著,兩個(gè)人就一起哭起來(lái)了。
媽媽是想起她死去的母親,想起她小時(shí)候的事情了嗎?
韓奶奶講一口淮北話,侉侉的,綿綿的,有著泥土的溫?zé)帷_@也是我最先接觸的語(yǔ)音和語(yǔ)調(diào)。之后這幾十年間,淮北話都讓我感到親切,我想,這就是我的鄉(xiāng)音了。
有一個(gè)時(shí)期,我住在懷遠(yuǎn)。
那時(shí)候我祖父母的家,在懷遠(yuǎn)縣城關(guān)鎮(zhèn)的北門一帶,人稱“北門口廖家”,由此可知,這曾是一個(gè)不小的門戶。但早在幾十年前,我父親出生的時(shí)候,廖家就已經(jīng)衰落了。是自家建的房子,磚墻瓦頂,三間堂屋,一間廂房,采光不好,常年黑黢黢的。家里沒有衛(wèi)生間,上廁所要到巷子外頭的公共廁所去,要走很長(zhǎng)很長(zhǎng)的路。
歷史上懷遠(yuǎn)是個(gè)碼頭,在渦淮二水之間,祖父母的家就在碼頭下面,緊挨著渦河大堤,我們叫作“大壩子”。就常年濕漉漉的,尤其是在雨季,好些天不能出去,我就搬一張小板凳坐在家門口。屋檐上落下來(lái)的水,垂成一張雨簾,我目不轉(zhuǎn)睛地看著,一坐就是好幾個(gè)鐘頭。好不容易放了晴,巷子里到處是一汪一汪的積水,就有人在路中間墊上幾塊磚頭。我三媽挎著攢了好些天的滿滿一籃臟衣服,上面壓著一根棒槌,快速地踏過磚頭,到河里去洗衣服。我穿著堂姐穿小了的大背心和大褲衩,一步一跳地跟在她的身后。
我三媽是我“三大”的老婆,似乎應(yīng)該稱作“三嬸”,但我們家不這么稱呼。我們家都是稱“三媽”、“四媽”,“三大”、“四大”,在懷遠(yuǎn),在我們家,“大大”是對(duì)父親兄弟的稱呼。
渦河水在高高的壩子外面流淌,巷子里有穿堂風(fēng)呼呼刮過,風(fēng)里有初夏的青草香,還有陽(yáng)光在樹葉上閃爍。我穿著洗得如皮膚一般細(xì)膩的舊背心,幾步就跨上了渦河岸踏腳的大石頭。我穿著鞋就直接跳到河里,引起一群洗衣婦女的尖叫。我三媽熟練地把一件件臟衣服,使勁甩出去,涮上一涮,然后再“刷地”一聲鋪在大石頭上,舉起棒槌,“啪啪啪啪”地用力捶打著。許多的捶打聲交織在一起,此起彼伏。
這就是古詩(shī)里的“萬(wàn)戶搗衣聲”吧。
當(dāng)然,那時(shí)我還不知道這些,我急急尋一塊石頭坐下來(lái),把雙腳伸進(jìn)水里,讓河水流過我。經(jīng)河水常年沖刷的石頭,鵝卵一般圓潤(rùn),隨便一塊都擁有古董一般美麗的色澤。它們有帶星星的,有帶花紋的,最美的是一種紅石頭,是半透明的橙紅色。這不常見,就如寶石一樣珍貴,我偶爾摸著一塊,就會(huì)把手舉得高高。我透過陽(yáng)光去看,看它在陽(yáng)光下染上一道金邊,它晶瑩的身體里面,有一串小小的氣泡,好看極了。
我興奮地站起來(lái),舉著向三媽炫耀,褲子卻重重地向下一墜,褪到腳脖子上,原來(lái)已經(jīng)被河水灌滿了。
我三媽把我的大褲衩扒下來(lái),就手搓了兩把,順勢(shì)在我屁股上打一巴掌,聲音響極了。我光著屁股跑回家,見到我奶奶,咧開大嘴就哭。她立刻拉著我,帶我去買好吃的,我一邊哭一邊在心里暗笑。巷口的小賣鋪,那時(shí)還是一扇一扇的門板門,開門了,門板就一張一張地靠在墻邊,多年以后我知道了,“開張”二字即來(lái)源于此。每一塊門板的上面,都有“門對(duì)子”的痕跡,破舊而斑駁。“門對(duì)子”是過年的時(shí)候貼上去的,這時(shí)都褪去了顏色。我奶奶把我舉起來(lái),我費(fèi)力但快速地爬上柜臺(tái),仔細(xì)端詳柜臺(tái)上放著的一排大玻璃罐子。那里面可是我的珍寶——又圓又綠的西瓜糖,五顏六色的泡泡糖,還有一粒一粒的“糖豆子”,我的口水要流下來(lái)了。店老板不慌不忙,一點(diǎn)一點(diǎn)旋開罐子,拿出一顆橘子糖給我。橘子糖用透明的玻璃紙包著,一瓣一瓣地拼成一個(gè)橘子,外面涂著一層白沙沙的糖沫。橘子糖紙也是半透明的橙紅色,舉起來(lái)透過陽(yáng)光去看,如一塊色澤晶瑩的紅寶石。
這個(gè)小鋪?zhàn)永铮瑫r(shí)刻都散發(fā)出一股醋和醬混合的味道。有時(shí)候,我和奶奶一起去打散酒,即便是空桶,我也小心翼翼地抱著。鋪?zhàn)永镅b散酒的大酒缸,有半人多高,一半埋在地下,壇口用一個(gè)裹著紅布的大木塞,塞得嚴(yán)嚴(yán)實(shí)實(shí)。我緊張地看著老板,塞子拔開來(lái)了,立刻有一股酒香沖出。我大大地打了一個(gè)響鼻,環(huán)顧一下這間小鋪,無(wú)比快樂。老板把酒漏斗插到我們帶來(lái)的塑料桶上,拿出酒提子,從酒壇子里快速地往外提酒,一提,兩提,三提……很快我就不看了,我的眼睛轉(zhuǎn)移到了柜臺(tái)上的那一排罐子上,等待奶奶來(lái)滿足我。
我爺爺一生唯一的樂趣,就是喝上兩杯,也沒什么下酒菜,有時(shí)是一把炒花生,有時(shí)就空口喝。他七十多歲了,還在廠里上班,傍晚下班回來(lái),第一件事就是脫下身上的中山裝,抖干凈,掛好。如果是夏天,則是挺闊的“的確良”短袖衫,也是抖干凈,掛好。
晚飯前有一段空閑時(shí)光,我爺爺一個(gè)人坐在天井里,擺開一張小方桌,喝他的“兩盅小酒”。這似乎是他一天中最為享受的時(shí)刻,但不知為什么,我覺得他一個(gè)人坐在那里喝酒的樣子,有些孤獨(dú)。他面前一個(gè)破舊的搪瓷小碟里,有一塊鹵雞肝,或是幾個(gè)帶殼的炒花生,也是孤零零的樣子。
這兩樣?xùn)|西對(duì)我,都沒有什么吸引力,所以我在等,等我的堂哥、堂姐,等他們隨便哪一個(gè)放學(xué)回來(lái),帶我去“攪糖稀”。穿過曲里拐彎的小巷,進(jìn)到一戶人家,遞給女主人兩分錢,她就會(huì)把豁邊破碗上蓋著的玻璃掀開,把兩根竹簽伸進(jìn)去,攪一攪,把一團(tuán)醬色的麥芽糖遞給我。
這戶人家的屋子,永遠(yuǎn)是暗無(wú)天日,木板搭的床,褥子下鋪著稻草。床上面常年躺著一個(gè)臥病的男人,是女主人的父親呢,還是她的丈夫呢?我不知道。但這戶人家的窘迫,連小小年紀(jì)的我,都能感受得到。她家的屋頂破了一個(gè)洞,晴天的時(shí)候,有陽(yáng)光灑進(jìn)來(lái);雨天的時(shí)候,我們就繞著走。
現(xiàn)在,現(xiàn)在我終于走出了那間陰暗潮濕的小屋,我舉著兩根竹簽,熟練地一拉、一繞、一攪,把糖稀擰成一股麻花,然后,循環(huán)往復(fù)。
這就叫“攪糖稀”,是我的懷遠(yuǎn)老家,帶給我童年的最大快樂。
走在夕陽(yáng)西下的北門口,麥芽糖的顏色漸漸變淡,從醬紅到金黃,再?gòu)臓N爛的金黃,變成瓷一般的乳白色。夕陽(yáng)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長(zhǎng),影子跟在我的身后,一起從生滿青苔的土墻邊走過。腳下是坑坑洼洼的青磚路面,青磚上斑斑駁駁。
我大了,上了小學(xué)以后,就只有在寒暑假,才能回去看我爺爺奶奶,那時(shí)的“北門口廖家”,已經(jīng)蓋起了大房子。是上下兩層小樓,平滑光亮的水泥地面,有獨(dú)立的廚房和廁所。知道我回去,爺爺老早就站在家門口迎我,老遠(yuǎn)就向我招手。沒等我走近,他就說(shuō)來(lái)、來(lái)、來(lái)!我給你看一樣?xùn)|西,然后牽著我的手,走進(jìn)一樓的臥室,從五斗櫥里拿出來(lái)一個(gè)餅干桶。我看著他費(fèi)勁地把生了綠銹的桶蓋打開,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疊明信片,說(shuō)你看看,看看,這是什么?
是我寄給他的明信片,上面寫著:爺爺奶奶新年快樂!
我每年都寄,每年都寫著一樣的話,我自己已經(jīng)忘了,爺爺奶奶還當(dāng)寶貝一樣收著。我仔細(xì)翻看著它們,像是看到了我的童年,在“收信人姓名”一欄,我用很大很笨拙的字體寫著:廖錦英收。
“廖錦英”是我奶奶,生在懷遠(yuǎn)城關(guān)有名的“北門口廖家”。
我奶奶的父親,我的曾外祖父,解放前在懷遠(yuǎn)城關(guān)北門口,開了一家很大的竹木店,經(jīng)營(yíng)毛竹和木材,外號(hào)“廖胖子”。他沒有兒子,只有兩個(gè)女兒,廖錦英是老大。
倒退幾十年去,我爺爺是廖家竹木店里的一個(gè)小伙計(jì),聰明伶俐,長(zhǎng)得也很齊整。我爸爸說(shuō)我爺爺一生,唯一的愛好就是喝酒,其實(shí)這不準(zhǔn)確,我媽媽就說(shuō)過,我爺爺寫一手好字,打一手好算盤,還有一個(gè)本事,就是能唱“全本西廂記”,而且會(huì)吹笛子,會(huì)拉二胡。
我爺爺會(huì)唱戲?這個(gè)事我怎么從沒聽說(shuō)過。而且這和我爺爺?shù)臉幼右餐耆淮睿矣∠笾械臓敔敚褪且粋€(gè)整日忙碌的“小老頭”。
“公家小老頭”,這是我給他取的外號(hào)。因?yàn)樗刻於家习啵缘氖恰肮绎垺保揖桶l(fā)明了一個(gè)稱呼,叫他“公家小老頭”。
他非常中意這個(gè)稱呼,有時(shí)他下班回來(lái)遲了,我就在院子里大聲喊:“公家小老頭呢?公家小老頭怎么還不回來(lái)?公家小老頭干什么去了!”
如果碰巧這時(shí),公家小老頭回來(lái)了,就高興的“嘿嘿嘿”地笑。他一本正經(jīng)的中山裝上,布滿了塵土,短短的一茬頭發(fā),全白了。
這樣的一位老人,會(huì)唱西廂記嗎?我很懷疑媽媽的這一說(shuō)。
長(zhǎng)大以后,我在一篇什么文章里看到,舊社會(huì)的學(xué)徒?jīng)]有什么娛樂,手敞的會(huì)去喝酒賭錢,更多的是和幾個(gè)同好,組成一個(gè)小小的娛樂班子,吹拉彈唱,做時(shí)光消磨。所以舊時(shí)的學(xué)徒伙計(jì),大都會(huì)一兩樣樂器,聰慧如爺爺,會(huì)唱整本西廂記,也就不奇怪了。
《西廂記》里有一句唱詞:“北雁南飛。曉來(lái)誰(shuí)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這句漂泊的唱詞,想必爺爺也唱過。
爺爺不是懷遠(yuǎn)人,廖家竹木店里的伙計(jì),幾乎全都來(lái)自徽州。
明代著名的戲曲家、文學(xué)家湯顯祖,曾以“一生癡絕處,無(wú)夢(mèng)到徽州”的名句,表達(dá)他在從商和入仕之間的掙扎。為何“無(wú)夢(mèng)到徽州”呢?是因?yàn)榛罩莸纳睿瑢?shí)在是太艱難了。一句流傳甚廣的徽諺,是徽州現(xiàn)實(shí)的寫照:“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徽州男兒十三四歲,就要出門學(xué)生意去了。徽州雖有山水之色,但無(wú)田土之利,怎么養(yǎng)活自己呢?唯有“仕與商”。所以皖南多士子,也多商人,一般人家的子弟,學(xué)生意的多。
爺爺就是很小的時(shí)候,出來(lái)學(xué)生意的,皖南盛產(chǎn)竹木,有個(gè)專門的營(yíng)生是放排。把一個(gè)一個(gè)竹排,像趕鴨子一樣,從新安江“趕”出來(lái),或是趕進(jìn)長(zhǎng)江,或是趕進(jìn)淮河,然后,散向兩岸廣闊的鄉(xiāng)野。
進(jìn)淮河的竹排,要先過八百里巢湖。
我爺爺應(yīng)該就是乘著竹排,從徽州的大山里,漂流到了廖家的竹木店。廖家的竹木店里有很多小伙計(jì),都是十三四歲的年紀(jì)。但廖家沒有兒子,這讓廖胖子很不開心。廖胖子端著一把紫砂壺,站在門邊看,看哪個(gè)小伙計(jì)能做他的上門女婿。最終他看中了我爺爺,一個(gè)許姓小伙計(jì),或是因他老實(shí),或是因他勤勉,但總之,不大會(huì)因?yàn)樗艹疚鲙洝?nbsp;
廖胖子是一個(gè)精明的生意人,他看人的眼光很準(zhǔn)。
他的大女兒廖錦英,是一個(gè)話不多的瘦削女子,一點(diǎn)兒也不像她的父親。她一生都沉默寡言,走進(jìn)走出,幾乎沒有聲息。她為自己的丈夫生育了七個(gè)子女,我爸爸在家中行四,上頭有一個(gè)哥哥,兩個(gè)姐姐。我大姑生下來(lái)后,取名廖銀河,是隨了外祖父的姓。
大了以后,我曾不止一次揣測(cè),我大伯和我爸爸他們,應(yīng)該也曾經(jīng)姓過廖,畢竟廖胖子看重的,是男丁。但隨著廖胖子的過世,他們又都把姓氏改回了許姓。
我爺爺一定很在意他“上門女婿”的身份,他一定很想讓人們知道,他們這戶人家姓許。但“北門口廖家”仍然是人們對(duì)這戶人家的稱謂,幾十年間,流傳至今。
廖胖子的小女兒,嫁給了懷遠(yuǎn)城關(guān)一戶張姓人家,不久就病逝了,留下一個(gè)兒子,三四歲的樣子。她的張姓丈夫后來(lái)獨(dú)自去了哈爾濱,續(xù)了弦,又生了一男一女。但他們一家四口,在1985年8月18日的太陽(yáng)島沉船事件中,全部遇難了,張氏唯一留下的孩子,就是我三叔,我們稱作“三大”的人。
我三叔雖然姓張,但入了我們?cè)S家兄弟的大排行,排在我父親之后,是男丁中的“老三”。而我父親行二,在北門口人稱“二犟”,從這個(gè)外號(hào)你就能知道,他為人有多么不隨和。我三叔后來(lái),也是在我們家娶妻生子,一生都稱呼我奶奶為“娘”。
懷遠(yuǎn)在兩水之間,一水為渦,一水為淮。
淮河是一條古老的河流,自大禹治水時(shí)便赫赫有名。它從碼頭經(jīng)過時(shí),聲勢(shì)比渦河要大得多,它波瀾壯闊,一絲絲風(fēng)就會(huì)激起層層波浪。
梅雨季過后,天氣一天天地?zé)崞饋?lái)了。
懷遠(yuǎn)雖是一座小縣城,但在以河流為大通道的年代,非常熱鬧和繁華。除了水利之便,它還特產(chǎn)一種石榴,荊涂二山簿瘠的夾沙土,非常適宜于這種來(lái)自西域的植物生長(zhǎng)。到了每年的五六月份,空氣中富含的水氣,被漸漸升騰起來(lái)的熱浪蒸干,石榴葉就濃綠得仿佛要滴落下來(lái),淮水榴花,紅艷似火。
這是孩子們最快樂的時(shí)候,我們以“壩上”和“壩下”區(qū)分縣城的地理位置,壩子上寬闊,小孩子們喜歡在大壩子上瘋跑。迎面吹過來(lái)的風(fēng),帶來(lái)一陣陣石榴花的香味,我堂哥找了一個(gè)小池塘,帶著我們一幫弟弟妹妹下塘摸螺螄。當(dāng)然,我們是不會(huì)讓大人知道的,大人知道了,會(huì)懲罰那個(gè)領(lǐng)頭的孩子。但河邊長(zhǎng)大的孩子,沒有不會(huì)水的,譬如我父親,還有他的七個(gè)兄弟姐妹,個(gè)個(gè)都是游泳的好手。不過他們不叫“游泳”,他們叫“洗澡”。他們說(shuō)走!到河里洗澡去!于是一哄而上,涌向渦河或是淮河。
他們中的任何一個(gè)人,都能在渦河或是淮河里,輕松地游幾個(gè)來(lái)回,我最小的姑姑,在十二三歲時(shí),就能孤身橫渡淮河。
為了“一瓶罐頭”,我媽媽嘲諷說(shuō):“你爸爸為了一瓶水果罐頭,在淮河上游了三個(gè)來(lái)回。”
不知道是哪一年,也不知道是一個(gè)什么性質(zhì)的比賽,橫渡淮河一次,可以領(lǐng)取一瓶水果罐頭。我爸爸為了多得一瓶,就擅自多游了幾個(gè)來(lái)回,得沒得到額外的罐頭,具體我媽媽沒有說(shuō)。
我媽媽總是喜歡在這些事情上,取笑我爸爸。雖然在那個(gè)年代,她縣委書記的父親早已被打倒,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我外婆仍然十分看不上我爸爸,看不上我們家。她鬧,拼命鬧,要把他們鬧散,所以我爸爸和我媽媽談了11年戀愛,最后才結(jié)婚了。
解放后公私合營(yíng),廖家的竹木店就歸了“公家”,一起歸了“公家”的,還有我爺爺。我最小的叔叔小名“合營(yíng)”,就是為了紀(jì)念這一重大事件。在漫長(zhǎng)的歲月里,他拿著一月三十六元的工資,養(yǎng)活一家十口。得國(guó)營(yíng)竹木公司的便利,我奶奶在碼頭上給來(lái)往的船只卸貨,一天能掙一塊錢,當(dāng)日結(jié)算。第二天一大早,她攥著這一塊錢,到渦河大壩子上去買“私糧”,9分錢一斤的大米,夠買11斤。那是一段手停口停的日子,哪一天沒有活干,那一天就沒有米吃。
我無(wú)數(shù)次地想象我奶奶在碼頭上卸貨的樣子,想象她瘦小的身體,如何扛起一大捆毛竹,從長(zhǎng)長(zhǎng)的跳板上走過。我小的時(shí)候,她常牽著我的手各處去走,或是把我抱到柜臺(tái)上,看五顏六色的糖果。在我的記憶中,她瘦而且高,走路很快,做事麻利。
很久以后,我看到她一張照片,才驚覺她十分矮小。
那是我剛出生的時(shí)候,她來(lái)到我們家,照顧我母親坐月子,和我爸爸的合影。照片里他們母子站在一起,她只到我爸爸的胸口高。
是一張黑白照片,三月的淮北,還有料峭的春寒,她在照片里戴著一頂毛線帽子。她的毛線帽子是棕色的,這我知道。在我的記憶里,她一直戴著這頂帽子,她一定也有不同的帽子,或是戴其他帽子的時(shí)候,但當(dāng)我想起她時(shí),她一定是戴著這頂棕色帽子的樣子。帽子上有一朵俏皮的小花,鑲一圈白色的毛線花邊,縫在帽子的一側(cè)。我覺得這一點(diǎn)俏皮和我奶奶很不搭調(diào),但如同我爺爺?shù)娜疚鲙浺粯樱谄D窘的生活下面,他們的心里還是有一點(diǎn)亮色。
除了我奶奶帽子上的小花,讓我驚訝的還有我爺爺破舊的中山裝里面,一個(gè)嶄新的假領(lǐng)子。我小時(shí)候看到它,覺得很好奇,沒有前襟,沒有后背,兩條布帶穿過腋下,將領(lǐng)子固定在脖子上。公家小老頭下班回來(lái),破舊的中山裝上,豎著熨得挺刮的假領(lǐng)子,看上去和這個(gè)家庭的其他人,很不一樣。
到我大了一點(diǎn),家里不再靠我爺爺?shù)墓べY過活了,我的叔叔姑姑們,也都陸續(xù)工作并且成家。但我奶奶還是自己霉醬豆子,把干癟無(wú)肉的螃蟹斬成四大塊,燉蘿卜。碼頭上這種螃蟹沒人要,幾毛錢就買一大簍。但是這樣燒出來(lái)的螃蟹真的很好吃,我媽媽的形容是:鮮得掉眉毛!
當(dāng)我爺爺端起杯子,喝他的“兩盅小酒”時(shí),我奶奶就在旁邊淘米做飯,斬螃蟹燉蘿卜條。
她喊我爺爺“小老頭”。她是個(gè)話不多的人,我爺爺則是不多話。他們倆在一起的時(shí)候,大部分是沉默。少年夫妻,相守到老,沒有那么多的話要說(shuō),但他們很恩愛,看他們的眼神就知道。
我沒有聽過我奶奶喊我爺爺?shù)拿帧N矣袝r(shí)候會(huì)想,年輕時(shí)的廖錦英,是個(gè)什么樣子呢?少女時(shí)代的她,是不是也在河岸邊,唱過《摘石榴》?
姐在園子里摘(呀么摘)石榴
哪一個(gè)砍頭鬼砸我一磚頭
剛剛巧巧砸在小奴家的頭喲
要吃石榴你拿兩個(gè)去
要想談心你跟我上高樓
何必隔墻砸我一磚頭喲
呀兒?jiǎn)?呀兒?jiǎn)?/span>
依得依得呀兒?jiǎn)?/span>
你何必隔墻砸我一磚頭喲
石榴花開得正好,月上了柳梢,河面漸漸被水氣所籠罩。《摘石榴》是廣泛流傳于淮河中游的民歌,熱烈,大膽,有著歡快的曲調(diào)。而“夜聽琴勾起了女兒心事,曉窗寒神倦思”也是一首情歌——這是《西廂記》里的唱詞。
我爺爺先我奶奶八個(gè)月過世,發(fā)喪的時(shí)候,我奶奶已經(jīng)得了老年癡呆癥,糊涂了。她操起一根竹竿,一竿子打過去,把跪著守靈的我爸爸和我的叔叔姑姑們,打得捂著頭就跑。她也不認(rèn)識(shí)我了,雖然我是她最疼愛的孫輩,她抓住我的手問,毛姍呢,毛姍呢?臉上是焦急的神色。
有時(shí)候她還會(huì)突然發(fā)問:“小老頭呢?小老頭到哪里去了?”
現(xiàn)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在他周歲的時(shí)候,我?guī)亓艘惶宋业睦霞摇ky得人齊,堂哥堂姐做東,請(qǐng)所有的弟弟妹妹吃飯,坐了滿滿一大桌子。各自的懷里,都抱著第四代,很快,孩子們也能湊成一桌。我堂姐——我三叔的女兒,抱著她的兒子坐在我旁邊,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一下子就想起了我三叔。
我也有好久好久,沒見過我三媽了。
我三叔去世好多年了,是兄弟姐妹里唯一走了的。我大伯八十多了,我小姑姑也六十多了,他們都很健康,生活得很好。
我爸爸這些年也越來(lái)越愛回老家了,喜歡和老兄弟幾個(gè)聚一聚,喝兩杯小酒。酒桌上他問我大伯:“大哥!人家說(shuō)我爸是外鄉(xiāng)人,知道是從哪里來(lái)的嗎?”
我大伯說(shuō):“不知道。”
然后他們就沉默,沉默地坐著,沉默地喝酒。老兄弟幾個(gè)也越來(lái)越相像了,身上都有了他們父親的影子。他們端起酒杯的樣子,讓我想起幼年時(shí)的無(wú)數(shù)個(gè)黃昏,我爺爺坐在堂屋的一張小方桌前,喝他的二兩小酒。他面前的小碟子里,有一個(gè)鹵雞肝,或是一把帶殼的炒花生,他喝得很慢很慢,二兩酒要喝一個(gè)多鐘頭。
他會(huì)想起自己的少年時(shí)代嗎?想起他如何跟著竹排,來(lái)到懷遠(yuǎn)城關(guān)的北門口?
我爺爺這一生,都沒有提過他的故鄉(xiāng)。
是不愿意提呢,還是已經(jīng)忘記了?他的后代,都不知道他是從哪里來(lái),他們年輕時(shí),也似乎從沒有問起過。我爺爺鄰居家的兒子,在上海工作,愛好文學(xué)。我們互加了微信,他在微信上和我說(shuō):你們家是徽州人,廖家的竹木店里,都是徽州學(xué)徒。
我爺爺名春濤,字少波,“三十以后以字行”,許少波是他戶口本上的名字。他來(lái)自于古徽州一個(gè)許姓聚族而居的小山村,具體是哪一個(gè)村子,就不知道了。
他出生的地方,應(yīng)該有一條河。他長(zhǎng)到十三四歲,要自己養(yǎng)活自己了,他就乘竹排順流而下,到山外去尋找出路。最后,載著他的竹排,停在了渦淮交匯處的懷遠(yuǎn)縣,他上了岸,來(lái)到了北門口。
(選自《安徽作家》,2022年第三期)

許含章,1984年生,作品散見《大家》《飛天》《西部》《湖南文學(xué)》《紅豆》《廣西文學(xué)》等刊物,并有作品被《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等多家刊物選載。全程參與長(zhǎng)篇報(bào)告文學(xué)《一條大河波浪寬》創(chuàng)作,該作入選中宣部2019年主題出版重點(diǎn)出版物選題、2019年國(guó)家出出版基金,并獲安徽省第15屆“五個(gè)一”工程獎(jiǎng)以及安徽省“十三五”省直機(jī)關(guān)精神文明建設(shè)“五個(gè)一成果”獎(ji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