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11-09 來源:安徽作家網 作者:安徽作家網
作品欣賞
不醒之塔(外一篇)
沈天鴻
散文觀:文學就是意味。散文自然如是。而有意味的作品,必定有其意義在——這意義被包融在意味之中,甚至是已經無痕地成為一體。文學性散文因此是立體的:既是一篇散文的結構的立體,也是一篇散文的意義的立體。立體即空間,形成空間才能生成意味存身、變化和蒸發的境。
一座寶塔在一個城市的一隅站立著,周圍是比它更美麗的樓房、大廈——這個“更”字并不意味著我認為這座寶塔也是美麗的,不,一座寶塔從來就不可能是“美麗”的,它只可能是莊嚴的,肅穆的,或者是陰郁、壓抑的,而現在這座寶塔已經老了,一座老了的寶塔經歷了足夠多的風雨,它已經與莊嚴、肅穆這些形容詞無緣,甚至連陰郁的壓抑的力量也已經遠遠不夠了,這就像一個人老了之后只是一個老人,此外什么也不是一樣,一座塔老了僅僅就是一座塔。
這個“更”字也沒有認為那些樓房大廈是美麗的意思。用鋼筋水泥藍色玻璃等等建造裝潢起來的樓房大廈,有可能是美麗的嗎?至少是我認為不可能,我寧可用“堅固的”、“豪華的”,或者其他諸如此類的等等等等形容詞來形容它們。我用這個“更”字只是構成一個對比,在這個對比中,一座塔以自己衰老的容顏、形影相吊的身姿,使那些雨后春筍般不斷竄出的樓廈有了虛假的美麗的性質。
這個城市的名字是安慶,一個已經存在了七百多年,而我才居住了十幾年的古城,它位于長江北岸,不舍晝夜的江水,日夜擊打著它臨江的城墻。
這座塔的名字叫做振風塔,一座比這城市略為年輕,但也已目睹過幾個世紀的死亡的古塔。
那日夜擊打城墻的濤聲曾經是金兵的馬蹄聲,一千里色中秋月,半夜軍聲萬馬潮,1217年,風雨飄搖的南宋在這江畔筑城駐軍以御金兵,城未破于金卻被破于元,國破山河在,城破之后城池也仍在。在“安慶”這個名字上“定居”下來的這個當初的駐軍小城,已是初呈繁華的商業之城了。
那塔,當是為佛所建。但并未能供奉舍利,因此只能說是為佛教所建吧。但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于是,塔在我眼里便只是塔,不為任何存在,甚至也不為它自身存在,它只是存在而已。
塔因此成為一個我眼中的象征。
象征就是那種什么都可以是,惟獨不是它自己的東西。
也是總是就在這兒,卻又根本就不在這兒的那種東西。
對塔一直有著濃厚興趣的我,很長時間里并不清楚自己為什么對塔有興趣,我曾經以為那是因為塔可以使我登高遠眺,放目八極,而我的確不曾放過任何一個登上任何塔頂的機會,安慶的振風塔我更是登臨過多次。但后來我終于明白了,我喜歡塔的原因只是因為我與塔都不是自己,都是既總在這兒,卻又根本就不在這兒——蘭波的那句“生活在別處”,在我和塔的存在中得到了印證:我們總是生活在別處,即使也生活在此處,那個此處也僅僅只是被微弱地包含在別處之中。
感謝那位米蘭·昆德拉小說《生活在別處》的翻譯者,他讓像我這樣的讀者得以讀到那部小說,但他在譯后記或者譯者前言中(在我看來,后記或前言都是一樣的,它們并沒有前后的區別)對書名所做的美好的生活總是在別處的解釋,我是不能接受的。名詞和動詞有著本質的不可混淆的區別。
塔是一個名詞還是一個動詞?這全在于怎么看。但即使是只從修辭角度來說,一個靜立的名詞,一座靜立的塔,一個死去的人的名字,一旦它成為了象征,它就是動詞了。
這是我的修辭學,不是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
亞里斯多德沒有見過塔,尤其是沒有見過我見過的塔。塔是東方的,傳入中國后又變成中國的,它是中國獨有的象征,獨有的名詞與動詞,與它所從來的印度的浮圖已經沒有多少關系,證據就是塔那收藏舍利和經卷的本來用途,幾乎已經被中國“叢林”之外的所有人們有意無意地淡忘了,并且早已就不再習慣用“佛塔”“浮圖”這些佛教名稱來稱呼它,干脆給它起了個“寶塔”的俗名。寶塔已與佛教無關,似乎它只是總是與寺廟在一起出現而已。
中國寶塔的建筑類型有樓閣式塔、密檐塔、金剛寶座塔、喇嘛塔等等,安慶的振風塔據說是仿北京天寧寺塔建成的,那么,它就是密檐塔了。但我對此并不關心,以我登臨的經驗,所有的塔都是相同的,這就是它們是從內部盤旋向上,在那狹窄黑暗的內部,向上的道路總是極為陡峭,上和下總是激烈地沖突,而每上一層都有找不到向上的路,似乎階級已經斷了,只能到此為止的感覺。更進一步地相同的則是塔影,它們的區別在影子中被取消,在秋天,塔影里鈴聲冷如一株寒菊,開放了一夜,也凋謝了一夜,早起的僧人,打掃院子的僧人,和絡繹而來的游人,看見的只有落葉,只有深秋的早晨,只有逐漸打掃得干干凈凈的塔影。
塔影甚至比塔更真實。它總是能從空中回到地面,然后又回到塔回到空中。
塔做不到這一點。聳入空中的塔已不能從空中回來,它指向的方向永遠是天空,“永遠”的含義對于塔來說就是一直徒勞而無望,它獲得的其實只是空間,而不是天空。
當然,這只是我,一個平民知識分子的想法。偉大領袖毛澤東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曾經乘軍艦到過安慶,軍艦一泊碼頭,毛澤東就興致勃勃地說,走,“過了安慶不說塔”,看振風塔去!讀到記錄此事的文章時,我記得我曾略為驚訝,毛澤東也知道“過了安慶不說塔”這句話?但我更想知道的,是毛澤東見到振風塔說過什么或會想到些什么?不得而知,能夠肯定的,只是絕不會有我這樣一介平民的想法。
過去的十幾年中,我先后寫過幾首雖未點明,但實際上是寫振風塔的詩,自己以為其中以寫于1982年初的那第一首最差,可不知為什么,現在我想起的卻就是這第一首:“一座古塔/一柄開裂的古老的時針/它從來沒有動過/永遠記錄著/它誕生的那個時辰/幾條蜥蜴/蛇一樣從裂縫中竄過/攪起了一片厚厚的/時間的灰塵//我凝視著它/歷史 //掛在它衰退而斑駁的塔頂/那兒,曾停留過/多少個世紀/過客的眼睛//我想起了許多/但實際上誰也沒有想起/……一群上學的孩子/背著書包從我身邊走過/風吹起/落葉覆蓋下堆積的鐘聲”。
最后我想起的,是那在安慶民間流傳甚廣,也不知道是何時何地何人出的那據說是“絕對”的上聯:
迎江寺,寺迎江,迎江寶塔,塔影橫江,魚上塔。
明長城到此為止。
祁連山卻仍一脈地西去,只扔出一座文殊山,憑著山腳下嗚咽的討賴河之險,與立于北的黑山對抗。鐵青著臉的黑山山脊如馬鬃微露,似有伏兵萬千,隱隱騰起猙獰的殺氣,逼視著扼兩山之間十五公里寬峽谷的嘉峪關。
孤峙于嘉峪塬上,三面臨戎的灰黃色的關樓卻悄無聲息,漠漠平沙在鉛灰色的天穹下四面輻射開去,一種鉛灰色的肅穆,如重重又重重難以數清的帷幕靜垂大地,夾著晚來天欲雪的的沉重。遠遠地,幾匹瘦駝啃著枯黃的塞草,在沙上悠悠晃晃,逆著西沉的夕陽看去,如黑黑的剪影,那牧駝的人也如一剪影,使人幾疑那是從帷幕深處走出的歷史中誘敵的兵士,一場刀光劍影,血濺枯沙的惡戰爆發在即……
這兒是古戰場,數百年前英雄系馬磨劍之處,單于獵火照狼山,長煙落日孤城閉的地方。
我們的旅行車,便是從這冥冥中仍回響著銅的嘶鳴、鐵的冷嘯的古戰場穿行而過,幾個小時,行盡我從小學課本上知道嘉峪關后的二十余年的夢寐,停在關下。
雙腳踏踏實實地踏上嘉峪關的土地,我深深感到1986年9月里的一天,我出現在這兒純屬偶然。不論過去與未來,這一瞬間和另一瞬間都有許多選擇,但偶然不容選擇。偶然沒有過去與未來之分,它永遠是現在時。
現在的關門大開。
大開的關門也仍是關門,盡管再無士卒把守,我的思想,仍然已中重重埋伏——
羅城,甕城,內城,道道城墻邊的埋伏者中,必有一人是我未知姓名的祖先。他來自關內何處?他知道他出現在這兒也是純屬偶然嗎?偶然構成人的命運。他到這兒來了,他執行了命令,他進入了陣地。通往敵樓的馬道上,他和他的同伴們的腳步明明滅滅……
我輕輕移動的雙腳,每一步都出其不意,踏在數不清的看不見的手上。
漢代,在這兒設有玉石障;五代,這里設有天門關。而從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征虜大將軍馮勝置關首筑土城算起,至今也已有六百多年了。數百年風雨,數百次血戰,城墻和箭垛仍十分堅固。傳說,修筑城墻用的黃土經過認真的篩選后,還要放在青石板上讓烈日烤干,以免草籽發芽。夯筑墻身時,更在黃土中摻入麻絲、灰漿和糯米汁,以增強黏結能力。驗收也異常嚴格:在距墻一定距離處以箭射墻,如果箭頭沒入墻中,便要返工重筑。終于,城墻堅固,箭頭觸壁落地,攻打關城的時間之縱隊,也在相持中與戍守者一起風化為齏粉,散成沙丘一片了。
唯有關城無恙,掛過號角的鐵釘還在那兒,被黃昏和望歸的靴子磨平的石級還在那兒,甚至,當年構筑關城,經過精心計算,完工時僅僅多出的一塊磚,也仍毫無變動地,還呆在西甕城“會極”門樓后邊的狹窄檐臺之上……
既往的一切,都如這塊可望而不可及的磚了:多余而必須。既在當初的那兒又不在當初的那兒。呈鎖的形狀卻根本不是鎖,沒有鑰匙開啟也無須鑰匙開啟。
這塊磚就是歷史。
歷史就是人們所記得的東西。
人們記得它首先必須看到它,而能看到的磚或文字都是一種障礙,它們使讓我此刻立足的嘉峪關,已絕對不是歷史深處那個真正的嘉峪關了。真正的歷史深處的那個嘉峪關,是卡夫卡的城堡,誰都聽說過,但誰都無法進入。它永遠屬于幾百年前的那些戍守者,他們明明滅滅的腳步在我身前身后雜沓,甚至就從我身軀中穿行而過,而相互毫無知覺——對于他們,對于歷史,我們是不存在者。歷史是他們的,只有當代史才允許我們廁身其間。在我無法參與的那么多為歷史所忽略了的夜晚,甕城積雪盈尺,戍守者們于怔忡中凍醒,寒風撲打關門,宇墻上傳來凍脆的刁斗聲……春來了,而這里仍然是塞草未青,白發的戍卒于關樓的墻角下以兩石相擊,然后流淚聽擊石后發出的啾啾燕鳴——那是關中春暖的燕鳴,那是家鄉吳語般的燕鳴啊!
如今,“擊石燕鳴”作為一景傳下來了,那些為歷史所忽略的夜與晝則是永遠地遺失了。
歷史忽略那些晝與夜,是因為那些日子里沒有發生值得記載的戰事,但那些日子這兒有活生生的人,有比在緊張激烈的戰斗中可能更為豐富更為立體的人在。忽略了人的歷史,分明有幾分假了,歷史深處的嘉峪關因這遺失,更分明有幾分虛幻了。
權且把它當作布景吧。
我和同行的幾位詩人分別了照了幾張相。
離去的時候,車出關門,我回頭隔著玻璃望了一眼,驀然發現關門外的斜坡上立有一方石碑。莫非是戰死在這兒的古代將士的墓碑?
我再次回了一下頭,嘉峪關已遠,那塊石碑更是虛渺不見了。
我閉上眼睛。我這次偶然的嘉峪關之行到此為止。
我的確到了嘉峪關。
我確實沒有到過嘉峪關。
這兩種說法都對。
作者簡介

沈天鴻,詩人,評論家,散文家。安徽省作協第四、第五屆副主席。中國作協會員。高級編輯。著有詩集《沈天鴻抒情詩選》、《另一種陽光》,文學理論集《現代詩學》、散文集《夢的叫喊》等。主編有《當代精品美文》叢書20卷。大陸、港、臺40多家出版社出版的多種詩文選如《新中國60年文學大系》、《中國當代詩歌經典》、《中國當代青年散文家八人集》、《中國新時期文學研究資料匯編》、《中國現代名詩三百首》等收有其作品。
作品欣賞
八月,我在老家住了十天
晚 烏
散文觀:我沒有書寫的野心,也不勤奮。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現實生活給我帶來了更多的思考,我把自己的觀察和思考融入零星的散文創作中。散文可以抒情,可以敘事,但它對現實的關照應永不缺席,我用散文書寫記下自我心跡,記住當下生活中我們的模樣。
母親到家就抱怨
我們進村后,沒遇到任何人。
夏末秋初的村莊,樹木蔥蘢,綠意濃釅。
到家,已是下午四點多。父親在村廠還沒回來,他養的一群雞在院里閑庭信步。我把行李搬下再送到屋里。孩子滿心歡喜,下車時,他犯難了。他嫌棄水泥地上的雞糞,他踮腳一蹦一跳地挪到到屋檐下,急著讓我把雞屎打掃干凈。母親打來井水,我們沖洗地面。
母親一邊灑水,一邊嘀咕,她對父親獨立生活的審查,從一把木椅子開始。那椅子用桐油刷過,光潔發亮,父親沒保管好,隨它在屋檐下日曬夜露,變得灰暗,陳舊。母親無法忍受這種隨意浮躁的生活態度,她覺得父親有義務珍惜一把木椅子。家里共有十來把椅子,這些年家里人少,椅子的使用率不高,有幾把已被蛀蟲咬噬,人坐上去會發出輕微的咯吱聲。除了一把椅子,門前小菜園也是母親的重點關注對象。她不能接受父親鏟除她所種洋蔥的事實,她認為他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語氣里有隱憂與不滿,憂在他不能好好地照顧自己,不滿于他照看家門的本領。
做晚飯時,母親又是一通牢騷。這么多年過去,她用嘮叨不斷對父親進行臉譜化的塑造,而我對她的很多看法表示認同。這是我家的常態,母親在批判里展現她的智慧與要強,我父親,要么沉默不語,要么在沉默中爆發。一旦他爆發了,我母親也會就事論事據理力爭,跟他磕到底,往往最后失了分寸的還是我父親。
親愛的冬瓜
這個季節的鄉間,日常蔬菜挺豐富。
這得益于父親,他在勞作間隙種茄子、辣椒、西紅柿、冬瓜及山芋。從前,暑假里天天吃這些,心里不免有些排斥。此時,我并不反感這些鄉間的當家蔬菜。母親用小火油煎茄子,再紅燒,口感軟糯有肉香。山芋桿撕皮,清炒,口感脆爽,也頗讓人喜歡。年紀大了,心境已改變,我不再貪戀肉食,這些蔬菜倒是表達出日常生活的底色,就算一日三餐吃,也不覺得厭倦。
屋內的角落睡著父親收回的冬瓜,大大小小,給人豐收的喜悅感。保存妥當,冬瓜擱放到冬至也不會爛。今年的這些冬瓜,來路特殊。在皖南,妻有天買了個細長的小冬瓜,母親覺得它體量合適,品種獨特,一兩天能吃完。她留種帶回老家給父親種,父親按指令行事,取得成功。回家頭幾天,母親忍不住多次贊美這些冬瓜,她直抒胸臆:看了真是讓人愛。她決定,這次回皖南時再帶幾個走。
這些疊羅漢般堆放在一起的冬瓜,會讓往事沁出心頭。以前,家里的冬瓜放在我寫字的木板桌下,我一伸腿就能觸到,它們像是我靜默的伙伴,看我讀書學習。我和哥哥有時犯錯,免不會被父親責罵,棒喝。幼小心靈的挫折與悲傷,被我一股腦地潑向桌下冬瓜。我拿出鉛筆刀,蹲下身子,劃過某個瓜的身體,給這個扎一刀,再給那個扎一刀。那些傷口無痕,不仔細觀察很難發現。明顯,這是一個男孩的泄憤表達,我把委屈和不滿發泄在一只只冬瓜身上。它們替我接住負面的內心情緒,如果它們能感受疼痛,一定會在我窗下發出疼痛的呻吟和吶喊。沒多久,冬瓜開始腐爛。刀劃的地方,變黑,變暗,再流出陳腐味的液體,慢慢地,整個身體開始塌陷,癱軟在地上,母親會捧著將它們扔進門口的竹林里,至始至終,她并不知道我曾傷害過它們。
跟冬瓜蹲在一起的,還有南瓜。它們扁平,敦實,扎起來手感很差,再加南瓜的自我修復能力很強,如果受傷,它們會分泌出油狀的汁液封閉傷口,不易感染。因此,它們不會遭殃。在往后的日子,如果南瓜和冬瓜再次一起睡在墻角,南瓜也該因冬瓜替它們承受的疼痛而致謝。
鄉下的瓜果蔬菜,不僅是果腹的日常物資,也在庸常的時光里盛滿生活百味。我從它們身上汲取來自樸素歲月的力量與精神依托,當我變成城里人丟失土地后,我格外愛它們,愛它們在生命里留下的慰藉與體驗。
疼痛與死亡
我凌晨三點醒來,在院子里坐了會。
夏末秋初的涼爽讓人清醒。蟲鳴一陣接一陣,四周寂靜,我在暗黑里發現一絲燈光。
弱光來自鄰居的窗戶,兩片簾子像并未合攏的嘴巴,而那一點亮,則是它存留的虛弱呼吸。屋里躺著的女人來自云南,本地人喊她唐芬。她在我們這個皖東南的縣里生活了20多年,丈夫意外去世,便來到我的村里。她的現任丈夫,是個本分的人。這些年,他外出打工,生活無憂,不久前翻新了屋子。
在我看來,隔壁叔叔踏實,加上唐芬很勤勞,他們的生活還算安頓。她跟前夫生的女兒也長大成人。那女孩,我見得少。生活的風暴有時會突然降臨,車禍將這個平和的家擊碎。唐芬陷入重度昏迷,身體多處骨折。三個月來,她有微弱的呼吸,靠插管飲食。前兩天,母親去看望她,回來說她的眼球會微微轉動。東奔西走的生活,并沒有給唐芬帶來最后的安然與穩定,她沒有身份,沒有戶口,直到跟隔壁叔叔領過結婚證,才真正落戶。那個20來歲的女孩,聽說在戶籍上跟她沒有任何關系,如果要確認關系只能靠親子鑒定。當前,女孩在家照顧媽媽,翻身、喂食,她一定在期待奇跡,然而希望萬分渺茫。
在鄉下,村人習慣放棄跟疾病抗爭的勇氣,微弱無力的醫療保障和物質的缺乏讓他們對大城市的高級醫院望而卻步。有些人生病,病因沒弄清楚,就不明不白地死了。隔壁唐芬在縣醫院住段時間,就回家了。肇事者是隔壁村的,拿出幾萬塊后,再也無力,只能等法院的判決。
唐芬不到五十歲,她只是近年來村里遭遇不幸的人之一。去年,壯年W被車撞身亡。W走后,他的妻和在讀高中的女兒相依為命。村人說,有時半夜會聽到他妻子的撕心痛哭。沒多久,W的母親得病去世。這些遭遇不幸的人,是我從前格外熟悉的人,他們對我十分了解,知道我是通過讀書從這里離開的人。
今年,我還失去了生命里的一位親人,我的大姨父。這個早年念完高中,后來發奮通過招考進入政府的男人,分管農業工作。他人緣極佳,對親戚也多會傾力相助。他意外摔跤,沒能搶救過來。他的離開,我一直覺得像夢。葬禮上,我幾度流淚,內心情緒無法形容。正月,我去給他拜年,他暢想今后的生活,還向我炫耀他養的蘭花。只是,這次我回來,他人已不在,他養的花異常茂盛,生出許多新葉。
笤帚廠的鄉親們
我開車去父親工作的笤帚廠,孩子跟著一起。
父親的工作臺靠近一個墻角,他帶著老花鏡,看到我們,喊了聲孩子的名字。父親從前根本看不上扎笤帚這樣的指頭活,他覺得一天到晚坐著,枯燥乏味,掙錢還少。去年冬天,他生病住院,身體虛弱。我們認為那是干重體力活所致,全家合議后,讓他去扎笤帚。
這廠子有20年的歷史,產品是環衛大掃帚,出口韓國。老板按件計酬,多勞多得。手快的人一天能掙一百元,手慢的掙得要少些。20年前,扎一把掃帚掙五毛錢,現在可以掙一塊八。
父親是新手,一天能掙八十塊左右。他早晨5點不到就出門,下午6點左右回來。父親自帶午飯,在廠里蒸著吃。他的工友跟他有著相同的生活節奏,早出晚歸,天天如此。在廠里看到的工人,我都認識。我的大舅,他目前獨自守在老家,因為表弟結婚后有了孩子,舅媽去了城里。大舅患有哮喘和眩暈癥,不久前還摔傷骨頭,休養了好幾個月;我的小姑,我父親的二姐,70多歲,前年患過直腸癌,手術后繼續在廠里干活;我的表哥,我小姑的大兒子,智商有所欠缺,從前在外做體力活,目前轉戰到笤帚廠;還有遠秀大媽,她將近80歲,丈夫去世10多年了,大兒子遭車禍走了,她目前獨立生活;還有良秀大媽,年紀超過70歲,丈夫不久前癌癥去世,目前和單身的大兒子一起生活;我的三嬸,他跟我叔一起在廠里干活,一年前,她在附近的蘑菇基地做事,后來跟老板產生矛盾,也轉戰到這里。我叔叔自從摔傷大腦后,看起來有點呆滯;開榮嬸目前不在廠里,她摔傷,在家休養。以前,我去廠里還能見到熱情的老板娘鄧嬸,這次她也不在,她去浙江給兒子打下手去了,兒子在外地開家效益挺好的網點。母親說,笤帚廠可能不久要關閉,因為老板不斷被催促去浙江幫忙,但獨立自由的蔡老板目前還在堅持,他不想受拘束。
如果這廠子停歇,這些平均年齡超過70的人,靠什么生活呢?這些天,我去過菜市、逛過鄉村雜貨店,物價之高不輸城里。我買三根排骨71元,一條鰱魚26元,買點鹵菜50多元,一眨眼,我花了三百多。鄉村人的人情往來也多,紅白喜事隨禮300起步,掙得錢也只夠日常開銷,積蓄寥寥,遇到大病大痛,出縣治療,報銷并不多。
想到這些,我總會有些不安。這些人是鄉村農民的代表,他們的暮年生活里充滿憂慮。我從父母那里感受到他們內心的極端不安全感,他們要強、自尊,根本不愿意過著伸手向孩子討要的生活。我的父親剛好70歲,在我看來,他缺乏智慧且不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和知識,一直用個人的經驗來應對多變的世界。他僅剩的是自我體力,他似乎并不認輸,覺得自己可以搞定一切。他拖沓的腳步、瘦弱的身體以及不合格的身體指標證明他的想法是虛妄的,不真實的。
大家對我格外客氣,紛紛跟孩子說話打招呼。我知道,我們已變成他們眼里的外鄉人。在廠里,并不是想帶孩子去獵奇參觀什么,只是,我真的是想去看看他們。
搖晃的鄉間
當我用文字來梳理短暫的鄉村生活時,寫著寫著,我的情緒變得復雜起來。
表面上看,鄉村有田園生活的詩意底色。陰雨天,遠處的山頭頂著灰白的霧,林木在雨水中散出更為明亮耀眼的光;門前的田野草木茂盛,白鳥飛翔其間,我走在某條小路上,有種沉醉的心緒。這么多年,我一直覺得風景在遠方,殊不知,我的老家也美麗如畫。
現在的生活贈與我不同的欣賞視野,我用游子的情感打量我曾生活過的村莊,自我與對象之間有別樣的情感互動。簡單點說,這些年,故鄉在我心里已然成為陌生的觀察對象,我是它的局外人,此刻我帶著距離審視它,贊美它。
然而,一旦回歸養育過我的小院,我卻體會到一絲沉重的憂傷。進入鄉村生活的內部系統,我從父親身上窺見大多數村人的鄉間命運,他們是留守者,是兒女帶不走的行囊。他們基本喪失跟新鮮世界溝通的能力,被衰老與病痛糾纏,是困在土地上的某顆棋,四面楚歌。但他們又極具道德感與自尊感,他們不想成為兒女的拖累,不愿過早依附他人。尊嚴對鄉間老人來說,是奢侈品。他們可能會為人生的最后體面選擇絕路,跟世界匆匆而別。
樓房、馬路,電器,這些確實提升了鄉村的生活質量,但在本質上,村莊是被動的,被城鎮化拖著邁步。年輕人把城市的生活習氣帶入村里,鄉村開始模仿城市。村人把一生的積蓄用來為兒女搭建一座漂亮小樓,兒女在外,他們是看門人。有限的物質積累一旦耗盡,他們又不得不重新開始,用羸弱的身體一點一滴積累,只為兩個目的,一是日常開支,二是攢錢。攢錢做什么,在我看來,是緩解內心的不安全感。在精神角度,他們是極度不安全的,缺乏對晚年生活的底氣。老人留守村莊,這些只是問題的表面。一個村莊如果沒有人氣,那也就不再具有活力,老人們內在精神是被人忽略的,不是因為兒女們不想重視,只是兒女們也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他們有的雖然已在縣城買房,但謀生依舊靠打工,他們把孩子送城里讀書,壓力巨大。
父輩這一代人經歷過饑荒,沒有文化,生存技能單一,他們的現狀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也許等我老的時候,一切會有所改觀,只是那時的鄉村可能人會更少,我們留在老家的樓房只會成為我們節假日回歸鄉土的據點。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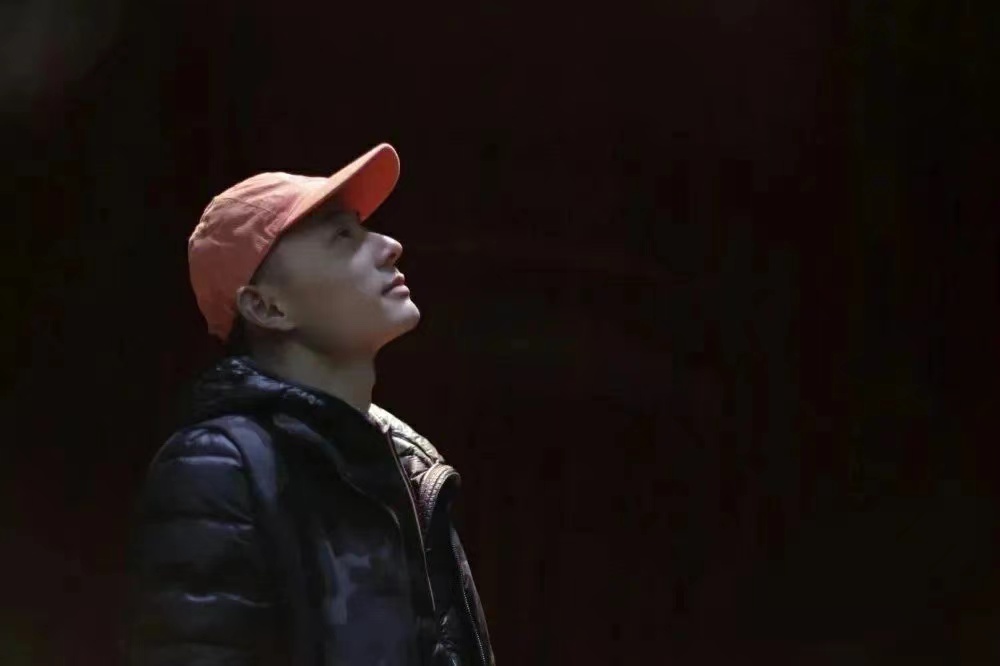
晚烏,80后,居皖南,散文寫作者,高校英語專業副教授。作品散見《散文》《安徽文學》《黃河文學》《美文》《廣西文學》、《北方文學》等,出版作品《天亮前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