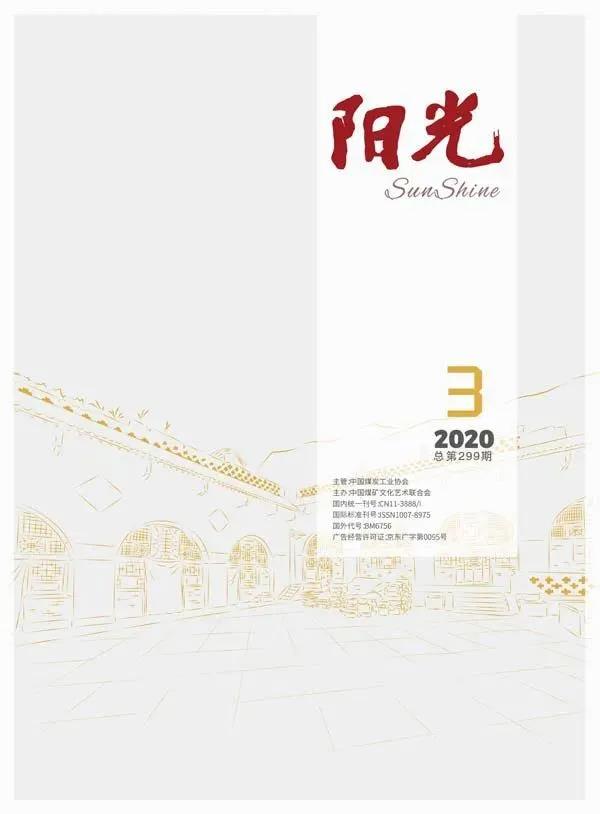近日,作家王漢英散文《漁家住在水中央》刊于《陽光》2020年第3期
陽光2020年第3期 總第299期 目錄
【藝苑風景】
生命重于泰山
——中國煤礦文聯抗擊疫情書法、美術、攝影作品選
【中篇小說】
還鄉記 / 廖靜仁
云 牙 / 閆桂花
【短篇小說】
三十里河東,四十里河西 / 蔡竹筠
代理礦長 / 周脈明
【美文天地】
五連軼事 / 星 明
漁家住在水中央 / 王漢英
“老大” / 凌 海
【報告文學】
馬背上的逐夢人 / 張彥婷
精彩閱讀
漁家住在水中央
王漢英
姐姐的微信頭像換了,點開一看,是幾只鳥雀圖。圖中,鳥媽媽正在向懷中的四只小鳥逐個喂食,四只小鳥一齊仰頭嗷嗷待哺。點開圖片時,我正在大太陽底下趕著回家。像熱哄哄的枝頭,突然掉下來的一陣涼風,瞬間,忍不住落淚。站在這春天的路口,一株株桐花送來花香。我茫然四顧。
往常,掉頭,穿過這條路,過三個紅綠燈,就到媽媽家了。媽媽老早就站在陽臺上朝來處張望。
沒有系統的寫過媽媽,一直說,不想歸納媽媽,還早,還早,連媽媽老去了這個意識,我都不具備。意識里,媽媽生命力極其頑強,她很少有頹唐的時候,或許是攜老拖幼的大家庭生活,讓她沒功夫頹唐,似乎我們的母輩盡是如此,也沒有多少特別的地方好值得稱贊。但,是不是還存在著另外一種生活呢?
在整理舊物時,紙箱里,發現她將外孫子的語文書悉數收藏好。其實,平時也常見一兩本放在她枕頭邊,實在沒想到,她收藏的課本如此之多,程度如此之深。看到玻璃板下壓著她書寫的生活清單和黃梅戲的唱詞,我由衷地感知我的基因來自于她。
我們姐妹幾個,在一起談起媽媽,都很感慨,最感慨的還是讀書這件事。媽媽的一生,是對知識渴慕的一生。
從一個只上過幾個月夜校掃盲班的少女到七十歲,成了老太太,還自學語文,差不多有初中的水平,如果中間生活的艱辛不一直磨折她,自學的成就應該還優異些。
讀書,是她理想的總和。
一生之中,她的理想無數次破滅,她的挫折,差一點點就要摧垮了她,總歸,她都撐過來了。甚至不如人的還有,她努力到超生罰款,還是沒有生出兒子。一輩子,她說,我就這么幾個小丫頭,我當命。原生家庭帶給一個人的影響是巨大的,或許正是基因里的這點韌性,她傳遞給了我們姐妹幾個。
Felitsa,是希臘音樂家雅尼寫給母親的音樂,并以他母親的名字命名了這首樂曲。我常單曲循環。旋律像江水滑過手指,蓬勃、悲愴,在心里奔流。流水的一生,多像媽媽———
江北洲是她的故鄉,江北洲的江堤外,媽媽織過魚網,捕過魚,辯識過江輪上的字,在江灘的沙地上一遍遍臨摹,她割過江邊洲頭的粽葉,在江邊的土屋里織過蘆葦席,之于這些舊事的記憶來源,雖得益于親戚中的口口相傳,但是我知道,她與長江的關系卻是血脈相連。
她原本就是江邊長大的漁家女。她身上有長江的屬性。
我小時候,聽戲臺上唱黃梅戲,“漁家住在水中央,水中央,兩岸的蘆花似圍墻,撐開船兒撒下網,一網魚蝦一網糧,一網糧”,聽著聽著,就怔了——唱的原來是媽媽呀。
我真正清晰的記事,是住在江北洲的鎮子上,一條通往另一個鎮子的馬路,一端又通往江北的碼頭。鎮子上有一家百貨公司,白白胖胖的女店員,若干年后變成了黑胖大嬸,舞蹈在縣城里的廣場舞中,郵局里盡是漂亮阿姨,卷發,長裙,那是小孩子們的偶像,食品站是最受追捧的好單位,土產公司一直不景氣,馬路邊炸油條的有三兩家,鄉政府還有點遠,隔個河能望得見。
我的家離郵局近,合六間的青磚瓦屋,勾著白水泥的磚縫,古意盎然,房子的前后廳堂,用一個園林的復制版月洞門作了隔斷。月洞門,是媽媽一生中美學思想的最高境界,我奇怪她是怎么構圖的?還是她內心有一個閨閣小姐的夢?
房子周圍媽媽種了許多樹,屋后有幾畦菜地和一口方塘,初夏時,方塘里,絳紅色的菱角菜漂浮水面,甚是好看。傍晚,鎮后鄉村的鄰居會拿長長的竹篙使勁撈菱角。這時候,郵局里的女孩子會擔著兩個小鐵筒前來方塘擔水。媽媽也會嗔怪我們,擔水擔不過人家,引爐子生火,引不過人家,打架也打不過人家。擔水的工具,我們家是特粗笨的木桶,一大一小,而郵局里的女孩子,完敗我們的是有一副神氣的小鐵筒——那里是擔水,分明是走秀,媽媽不會知道我們這點心思。
鄉鎮府的女學生,頭上會綁一個大大的紗質蝴蝶結,馬尾辮一甩一甩的,像個驕傲的公主,我穿的都是二手衣,還頂著男孩子頭,一個丑小鴨。少年的我是缺乏自信的,在別的小姑娘都收到各種禮物的同時,我竟連棵狗尾巴草也沒有收到過。
翻媽媽年輕時的老相片,張張都很好看,外婆的相片只有一兩張,但是鄉間七大姑八大姨的總會傳說,我的外婆是方圓百里的美人,應該更好看。雖然媽媽生養的幾個都是姑娘,據媽媽說,幾個姑娘,花朵一樣,這多少還是慰籍了父母的心,估計基因還是不錯,以至于沒有收到狗尾巴草這事,后來講與媽媽聽,她始終不信。
其實,也與媽媽拌嘴。
有個村支書,常到我們家打秋風。父母待村支書上賓,好吃好喝招待。村支書喝酒一上頭,就拽文。席間,話說我爸日后要“五馬分尸”,村支書文盲一個,他不懂五馬分尸涵義,他本意是,我爸媽只有幾個姑娘,將來無人養他們二人老,父母一笑置之,繼續閑聊。
我在后廳聽到這個詞后,小小的孩子,已懂得這個詞的惡意了,熱血上涌,沖到前廳,沖我爸喊:讓他走,讓他走,壞人,壞人,他五馬分尸,他全家五馬分尸。支書訕訕走掉,等待我的就是一頓笤把絲,未等媽媽動手,激憤之下的我,拒不認錯,撒腿跑出了家門,一路跑過河塘、田埂、跑到江堤外,江堤外楊樹成林,一路綿延不絕。我在楊樹林中茫無目地瞎走,小小的孩子被孤獨的大雪覆蓋。
走到了黃昏,走到了天黑,走到了輪渡碼頭,在昏暗的燈光中,遙望長江對面的江南,要不要渡過碼頭?還是恐懼占了上風,又擔心外婆會找爸媽拼命,左思右想,就跑到路中間顯眼的位置晃蕩,這樣容易被找到,最后,確實很容易的就被找到了,據說,動用了好幾個生產隊的人力。回家沒有挨打,還吃了好大一碗糖打蛋。
媽媽后來一直覺得這個“成語故事”很勵志,很爭氣,說打我,也只是“過點"的話,“過點"是村莊語言,指臺面上的話,給村支書一個臺階下。現在想,這是媽媽的情商體現。
客觀上看,我媽的情商不高,媽媽太重視“做人",家里人可以餓肚子,人情禮周,必不能節省,所以在鎮上,人人習慣喊她“小姑"。“小姑”也是村莊語言,即是這片土地的女兒,是每家每戶的親人。這個“做人”,媽媽是一路做到底的。她半生的磨難起因,皆因“做人”做的太好。也因這“做人”,后半生她也回收到周圍人的信任和敬重。我們姐妹幾個一直不以為然,就“做人”做到什么份上,跟她糾纏許多年,終難勸醒于她。
現在回想,這做人,也是她這一輩人,活在這人世間的根基。我們在信息時代里打滾,漸漸蛻變,離精致的冷漠主義者越來越近。
合六間的房子,最后賣給了土產公司,那些花草樹木在午夜屢屢入夢。
我一直有個愿望,要尋訪一個山青水綠的鄉村,租幾間民房,在四周種樹,種花,槐樹、泡桐、苦楝,香樟,烏桕,桃花,杏花……田園回歸,以前不在我的人生規劃之中,反觀自己,半生都在對城市化的追趕中渡過,對于自然的眷戀,近幾年成了我最大的鄉愁。
也許未必會隱居村野,但能偶爾有暇,白日與清風綠樹相伴,夜晚在庭院中仰望星空,發呆時,一定會對著星星喊“媽媽”,你從未離開過,只是穿著隱身衣,我看不見而已。
前幾日,音樂頻道里,正在插播一首民謠,“多想在平庸的生活里擁抱你”,唱作人顯然很年輕,“平庸"從來不是人生的困頓,"軟埋"才是!思想、激情、興趣、真誠度、價值,統統的銹掉、一點點的消散,這是生而為人,最大的耗損。媽媽你是懂的,你始終放心不下,被你號稱丁香一樣稚嫩又敏感的女兒,你像個老母雞,拼盡全力,都想護佑我。媽媽啊,若人生簡單到你的翅膀就能保護住我,那你千山萬水大約也會飛到,只是命運的未知,你總有無能為力的時候。
我反復的聽這首歌,聽到最后,心酸良久。媽媽,我終究在平庸的生活里,再也不能擁抱到你。
你燉雞湯的瓦罐還在我家,得知我患感冒,你從老屋,十里的路程,打的,再走到我家樓下,爬上樓梯,將燉好的雞湯,放到門口,怕我埋怨你,你連門都沒敲。前面我說你像老母雞,誠然,你恨不能燉了自己,也要滋養你的孩子。因為你覺得,這是你僅能為我做得到的事,但凡做得到的事,你的付出都到極致,你的一生,是用力愛的一生。
你是愛的優等生。
所幸,你的幾個女兒還算孝順,你帶大的外孫,還算懂事。
近幾年,尤其搬進新居,你整日都快樂得很,跟老鄉,你夸贊你的幾個孩子有多優秀,要有多偏愛,你眼中的孩子,才完美得亮光閃閃。妹妹跟你有過徹夜談心,好像預言,你說,你的人生很圓滿,沒有遺憾。可是怎么能沒有遺憾,你叫來的木匠,打的柜子尚未動工,你新買的冰柜,今年的新茶還未品嘗……桐花正開的仲春,賞花的日子尚未安排,我陪伴你的時間還那樣少……我們和你都未作過這種遺憾的預設啊。
媽媽是什么時候走向衰老的,我竟不知。始終覺得她離老還很遠,始終是我壯年的母親,生命力極其頑強的母親。這些錯覺遮閉了我們的眼,我們的心。愚蠢的我們,不知,生命從不等待。
清晨猛然醒來,鳥雀在窗外鳴叫,這不是夢,媽媽也不在夢里,電話那頭再也沒有人喚我的乳名,喊我回家吃飯。你的老式手機24小時都是開的,你生怕電話不暢通,孩子會聯系不到你。后半生的你,心性恬淡,越來越像尊佛。
我們姐妹幾個商議,將你的電話一直續費,永不報停。
又到江汛的時候,江北洲的故鄉,江水浩蕩。江水奔流過的地方驗證著人間的哲學,是那樣的準確:“漁家住在水中央,兩岸蘆花似圍墻,撐開船兒撒下網,一網魚蝦一網糧”。
作者簡介
王漢英,安徽省作協會員,主要創作散文、詩歌。有個人詩集《人海》。作品見于《人民政協報》、《文匯報》、《解放日報》、《工人日報》、《散文百家》、《陽光》、《讀者》、《意林》、《詩林》、《散文詩》、《詩歌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