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4-04-11 來源:安徽作家網(wǎng) 作者:安徽作家網(wǎng)
近期,我省作家陳家萍短篇小說《獨角牛》發(fā)表于《莽原》2024年第1期;短篇小說《白天鵝之傷》發(fā)表于《當代小說》2024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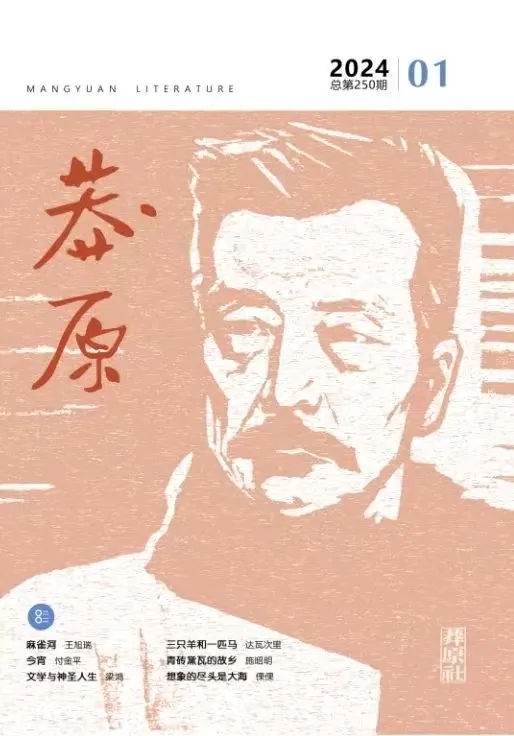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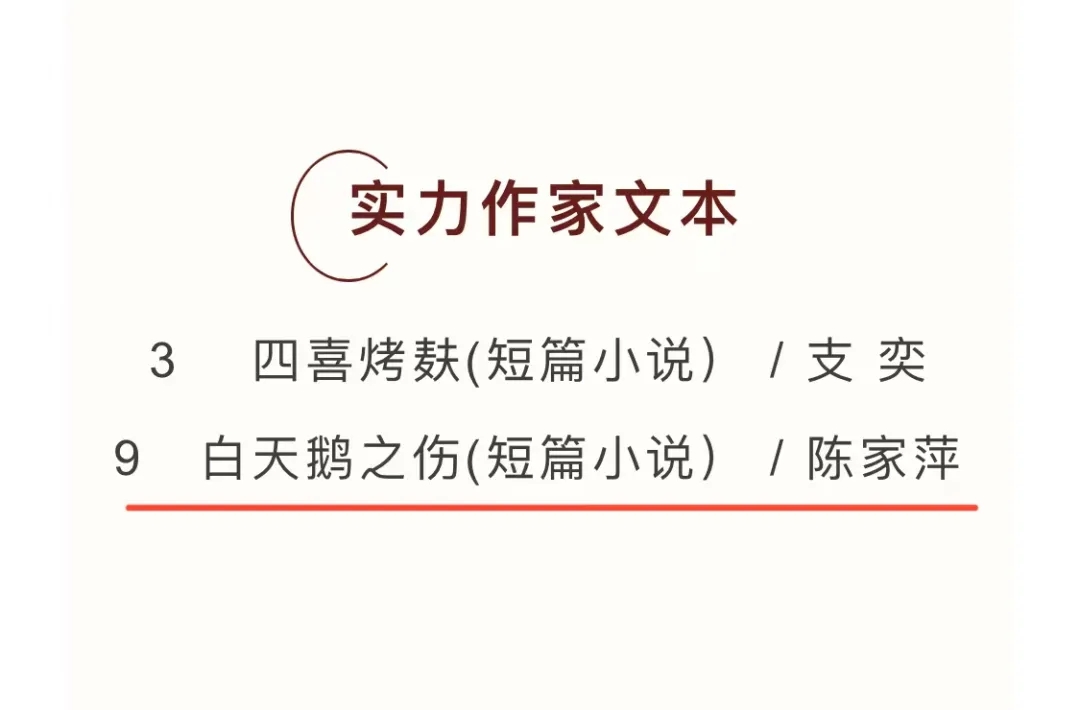
作品欣賞
獨角牛(節(jié)選)
陳家萍
尕老漢是被窗外的月光燙醒的,睜開眼,一片軟刀正砍向胳膊,放出黃燦燦的光,他伸手握了握,握一手酥軟,不由得激靈靈打了個冷戰(zhàn),皮膚傳來一陣緊似一陣的透骨的冰涼和尖銳的滾燙。哪里傳來的酒歌?他屏息凝聽,混入夜色和霧氣中的蒼茫歌聲伸出一只手,牽引他下了床,“嘎吱”一聲抽開門閂,踩亂一地樹影。
遇迎頭風,走兩步,退一步,酒歌趔趔趄趄,這才驚覺,酒歌不在別處,發(fā)自他的腹腔。啊,我又能唱酒歌了!尕老漢仰天長嘯,聲震林樾,“酒—酒—歌—歌”,風愈狂,歌愈烈,山谷回音,余音不絕。
尕娃時代的他受高人指點,學會用腹腔唱酒歌,這絕活讓他出盡風頭:在首席坐定,眼風一罩,四圍安靜,他從腹腔吟出的酒歌,一搓一揉一推一搡將酒意繚繞至酣暢,把宴席的氛圍推向高潮。突然一天,腹腔啞了,他再也吟唱不出酒歌了,這是哪天的事?
被風卷到山頂,月華兜頭澆下,淋濕岡頭一只拜月的黃鼠狼。以前聽老人講古,什么月圓夜黃大仙集體拜月,以為那是胡編,今兒個真就見了!尕老漢不錯眼珠地瞅,這黃大仙顯見得也老了,動作遲緩,姿勢僵硬,拜完月,它扭頭瞅了眼尕老漢,點點頭,倒把尕老漢驚出一身冷汗。它笑瞇瞇地走了,走的方向正是菩提村;月光下的村子也老了,被黃鼠狼一步一步給走老的。
尕老漢眼前出現(xiàn)兩條歪斜山道,它們像兩排犬牙,把這座鳳凰山一咬兩半:東邊為生道,山下住著數(shù)戶人家;右邊為魂道,亂墳崗上棲息著無數(shù)往生的靈魂。腳自動朝向亂墳崗。也不知怎么就坐上高高的墳丘,手一摸,摸到一瓶酒,喝一口酒,對著月光唱一段酒歌,那模樣像極一匹孤獨的老狼。
金杯銀盞斟滿酒,大姐端來米粉肉,爺兒們,甩開膀子喝個夠,喝夠酒沒煩憂,春天過完到夏天夏天過完又是秋,吃塊米粉肉潤潤喉,米酒喝了不上頭,做人也像酒醇厚。
尕老漢唱酒歌不需要腳本,可以望風采柳,他唱天上那盞圓燈籠,月光像亂箭般在密林里“噗噗”躥來躥去,有幾支射到他身上,把他射清醒了,認出坐的是老伴的墳。他顫著手摩挲著墳土,摸到一塊土疙瘩,捏成碎末,均勻地撒在墳上。捏完一塊又捏另一塊,他捏得如此細致,神情肅穆、姿態(tài)虔敬,似乎碾碎的不是土疙瘩,而是艱難歲月中的磕磕絆絆、世事紛擾。他碎碎念:這墳土呀,就是她的衾被哩,萬一硌著她可如何是好?
他那永生的泥屋新娘喲,可愛美了,一頭青烏烏的頭發(fā)梳得一絲不亂,衣服褶子捋不齊整就不出閨門。
“你傻啊,我比你大。”
新婚之夜,速速打發(fā)了一幫酒鬼,他早早到洞房,挑開紅蓋頭,她頭一抬,眸光一閃,晃得他失神。
不,他心里話,我才不傻:“我太奶奶說,‘打獵要打獅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娶要娶世上的好女子。’”
“你傻啊,娶了個空殼。”
他抓住她的手,放到自己的心窩——她的手冰冰涼,燙得他一哆嗦,望著她的眼睛,他一字一頓:“不怕,我——”他想說,這顆心是滾燙的,掏給你,隨便用。這些話不知怎么打了結,絆住了嗓眼。
“你傻啊,”丹鳳眼里浮上了霧,“為啥把我從棠梨樹解下,我本……”
他捂住她的嘴,沉聲道:“我太奶奶說,除死無大事。”
“好個除死無大事,”這句話就像火柴噌地擦燃了那雙著名的丹鳳眼,他被那瞬間迸發(fā)的璀璨驚住了。她的美,照亮了泥屋。連屋外聽房的人也噤聲。她咬破手指,把血擠到掌心,抹上嘴,唇紅齒白;抹上臉,粉面桃腮,整個人都活過來了!
“好,好。有你,有這些話,足夠我活上十年。我給你生兒子。”
地上晃來一只牛角。他揉了揉眼,沒錯,獨角牛。他摸著獨角,“果然是你。二十多年未見,你我都老了。”獨角蹭著他,把泛黃歲月中的熟悉感覺給蹭出來了,這熟悉感覺在全身到處跑,蕩到心里,心發(fā)癢;躥到鼻孔,鼻子發(fā)酸;鉆到眼里,眼睛發(fā)脹。他哭了又笑:“你個沒良心的,還知道來見我啊。”
它曾有一對威風凜凜的雙角。
它曾是方圓百里遠近聞名的犁田好把式,力氣大得邪乎,有他的酒歌助興,拖著犁馱著耙,行走如飛,再大的田也不夠它耕。卷幾舌青草,它就恢復了力氣,追著母牛跑,四處找伙伴打架,兩只角像鐵鑄的彎刀,發(fā)出凜冽寒光,牛們打眼瞅見它掉頭就逃,它還不依不撓,他只好返住角好生相勸:“窮寇莫追。”
獨角牛和尕老漢都曾擁有激情燃燒的青春歲月。
婚房是五間茅草房,堪稱當時的豪宅。松毛扎大脊,土坯取自他分得的地,泥墻、泥地都用白泥一遍遍刷得平滑光亮——白泥是本地特產(chǎn),可當水泥用。
泥堂軒敞豁亮,她是永生的泥屋新娘。
動物親昵泥屋。堂前燕子呢喃語,檐下麻雀叫喳喳,清早喜鵲來報喜,撒歡的還有貓狗、雞鴨與墻頭的喇叭花。墻上無數(shù)洞眼,那是蜜蜂的家。——它們飛進開成一片金的油菜花地,飛進桃花叢,連滿院陽光都嗡嗡有聲。
婚后第二天,她把自制煙絲倒在紙上,卷好,到灶火上點著,遞給他:“太奶奶說,不能斷了煙火。”
他懵懂接過,糊里糊涂去抽,半年后頓悟:指間一縷閃爍的微光,一日三餐的炊煙,她微微隆起的腹部,絞的剪紙,氤氳在他腹腔的酒歌,共同構成這五間泥屋不滅的“煙火”。
黃爪搭在巢穴,雛燕探頭,睜著小黑豆似的眼睛瞅啥?一束太陽光柱從門外射入,罩住了她,給她鑲上金絲銀線,鍍上金粉,她端坐竹椅上,臉上毛茸茸的細絨毛清晰可見。她穿著鵝黃色細開司米毛線夾,脖上系著柳綠色絲巾,只見剪刀在白紙上旋轉翻飛,白菜和小兔子、和平鴿和牡丹花很快就剪好了。她在和搖窩里的小嬰兒說話哩:“用鋸齒紋,白菜、牡丹花的花脈、葉脈,貓毛、鴿子、馬的鬃毛,動植物就有了質感。”她把剪紙抖開:“瞧,鴿子邊上還有銅錢紋呢,在民俗當中,鴿子是吉祥物,牡丹花開富貴。”
可不,她一刀刀剪出來的都是對人世的好意。
“還有月牙紋、云朵紋、火焰紋……這都是老祖宗傳下來的寶貝啊。”
胖小子咿咿呀呀,小東西能懂個啥?荷鋤而歸的他笑了。
他倚門而立,看著她,這永生的泥屋新娘,她把周圍的世界照亮。一株巨傘樣的杏樹抱持著東廂房,雨絲一撩,杏花就開淡了,紅紅白白;西廂房一墻牛屎巴巴,陽光一曬,一股子松爽干甜的青草味兒,惹得蜻蜓滿場飛。她專挑白凈的,捏碎了,放瓷罐當粉用。這粉混合了嬰兒的汗味、奶腥味,散發(fā)出一種特殊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味兒,他一直沒能辨別出來。不像姜,不像蒜,不像花果,不像任何莊稼,回憶到這兒,他猛地抽了下鼻子,深呼吸,從時光深處撲過來的一股清香撞得心口疼,他恍然大悟:那是幸福的味道啊!
那時,門前,鳳凰山上白鷺飛,雨后草叢中冒出一嘟嚕一嘟嚕的松菇,那是鳳凰山神的恩賜,油公雞炒松菇,咬一口,媽呀,鮮死人!
那時,屋后鳳河,一網(wǎng)下去,就能熬一鍋蝦糊。船上立著鸕鶿,一個猛子扎下,捉了紅尾,再捉鯽魚。蒼茫的漁歌響起,泥屋炊煙即起,裊藍了菩提村的天空。
那耕牛遍地走的村莊,到處彌漫著蜂飛蝶繞的幸福味道,當時渾然不覺,如今想起,甜得扎心。哦,我的泥屋新娘,我的獨角牛,這一切都和你們密不可分!
村里輪流使牛,生小牛那天恰趕到她家。一村的人都跑去看,他注意到,一大半的人頭都扭向她。脖上系著的紅紗巾把她的眼襯得像天上的星子。他的眼睛不夠用了,看一眼小牛,再看一眼她。老牛呢,誰都不看。甚至顧不上看一眼小牛,只顧低頭吃干草。那是他從草堆扯來的,他心疼它,懷著小牛照樣犁田,現(xiàn)在,它像卸貨一樣卸下了肚里的小東西,肚里癟了,神情松快,大眼沉靜,悠遠。他驚奇地看著老牛卷起干草一下一下慢慢反芻,世界真奇妙,灰黃如土的干草能化為乳白的奶汁!老牛咀嚼干草的樣子極莊嚴,像在咀嚼它的前生。他也扯了一根草,放在嘴里沒嚼兩下“呸”一聲吐出,他嚼到的是灰塵與草渣。
為這一抱干草,她當眾夸了他,說他糍粑心腸,是阿彌陀佛一個人。一句話讓他的心生了羽翅,飛向云霄。
……
作者簡介

陳家萍,中國作協(xié)會員,合肥市拔尖人才,研究館員。著有長篇小說、散文集和中短篇小說集六部。中短篇小說散見《莽原》《時代文學》《安徽文學》《海燕》《當代小說》《伊犁河》《六盤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