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25 來源:安徽作家網 作者:安徽作家網
近期,我省作家凌元芳散文《我的“花園里”》發表于《鴨綠江》2023年第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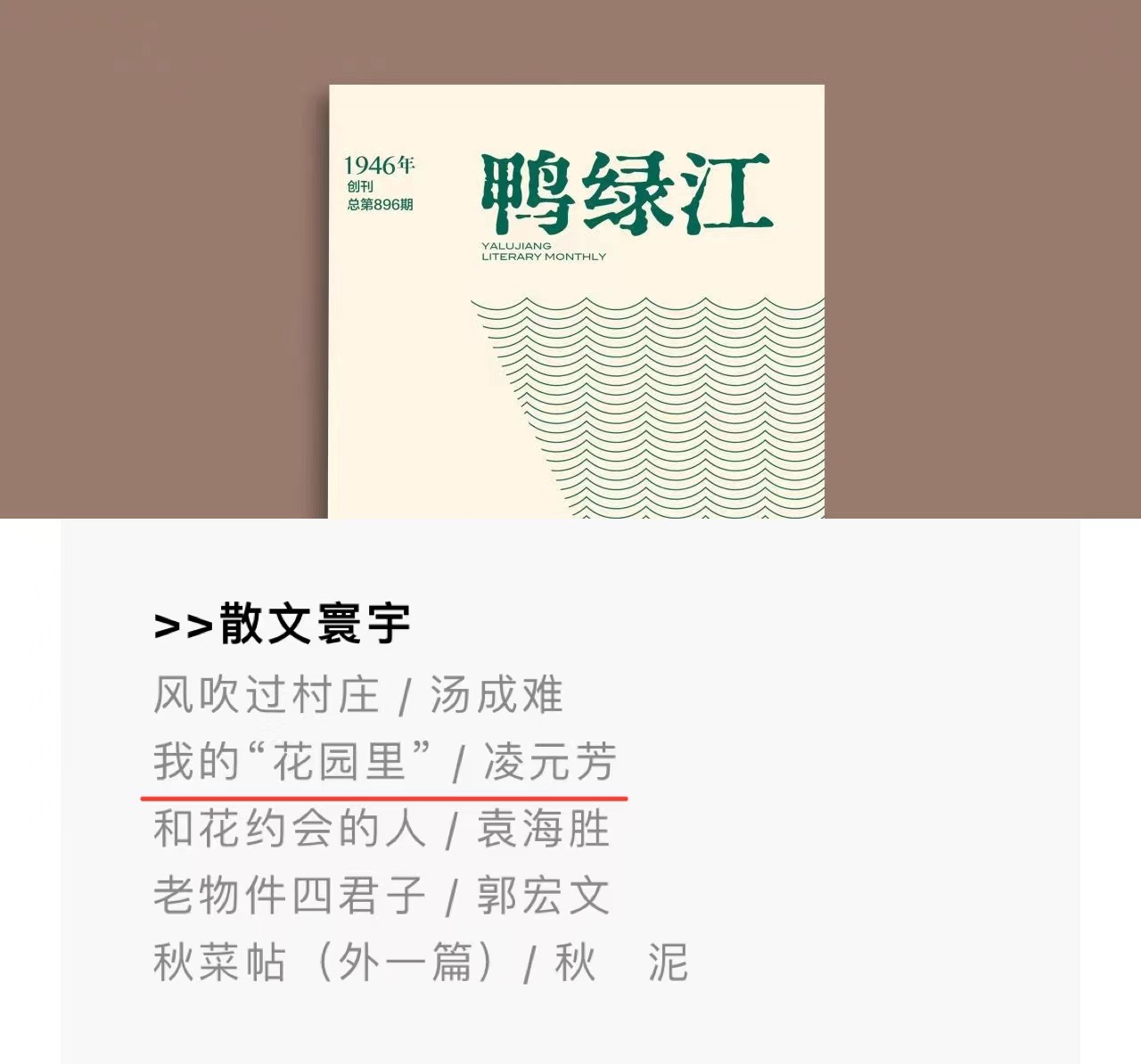
凌元芳
“花園里”這三個字,一度左右著我們一大家子的年貨準備,“新正月,多備點下酒菜,不出初四五,花園里二舅一來,那就有得嘮磕啦!”父親這句叮囑,多在1980年代漸至年關的當口。母親嘴里依舊“嗯嗯”地應承,像是胸有成竹,讓父親的提醒似乎有些多余。不是么?那可是娘家二哥,從幾十里之外的花園里趕來拜年,大正月里迎客,哪能虧待了孩子他二舅?
畢竟,一端酒杯就是話癆的二舅擺起龍門陣,哪回不聊到三更半夜?
莫非,他那么多的話語也是一朵朵盛開的花?從“花園里”采擷而來,一句句蘸滿露珠,還帶著清香的鮮汁?“他姑父,那年……你可沒見過那世面。南京城隍廟會,那個擠的,筷子都插不進,大人小孩的鞋子,擠掉了不知多少雙——那個熱鬧勁,唉,能看一眼,一輩子,值了!”幾杯燒酒下肚,得瑟的二舅述說起“高光時刻”,盤來盤去的總是那么幾件。
“嗯,那是。”父親的附和有點兒重復,可一時也想不出來其他的點贊方式。在這位遠道而來的二舅哥面前,的確翻新不出更好的奉承。
“他姑父,你不曉得,1958年,你二哥我……那個風光啊。代表我們花園生產隊,去淮北開會取經。那個大禮堂,一窩蜂塞進去的農民代表,至少兩三千人。就憑生產隊一紙介紹信,蓋上公章。有了這枚紅戳子揣在胸口,走再遠的路,心里暖著呢。說起來你們可能不信?我們那真是一路走到哪吃到哪住到哪,一分錢不花,全國人民那個親啊,像是一家人,那個熱乎喲——唉,八輩子都沒遇到過呀。”
“嗯,那時候,人人一心,共產黨是咱老百姓的天,上頭怎么說,我們就怎么干!”許是二舅說得有些累了,父親補充的這句,似乎想給睡夢里的母親與我,輕輕地掖了掖被角。
一頓天南地北散聊似的“二人談”,每年正月初四五的晚上,都會在我家那間小屋里準點開場。至于何時謝幕,夢境里我們不得而知;感覺二舅和老父親這對老哥倆的對話,汨汨流淌成溫馨的波濤,一浪浪地枕著我的夢境。難得的夜闌臥聽,嗚嗚叫的北風乍起之際,摻雜著間斷的一問一答,宛如子夜報時的鐘聲。這當兒的老父親估計漸入困倦交加,一度只聽得“嗯嗯”應付,怎奈母親的娘家二哥談興甚濃,南京城隍北京土地、東家長西村短的拉扯開來,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里的又繞了一圈。
2
除夕守歲、正月初一開財門,農家的這兩件大事,作為一家之主的父親可不能缺席。等到大年初二,父親必定去一趟花園里,給各位舅舅家拜年。每回都少不了的一場酒醉,到頭來幾乎落座于二舅家。過不了一兩天,最多也就是兩三天,二舅回拜而來,怎么說也得住上一晚。老兄弟倆個邊酒邊聊,更多的時候,父親到后來只能是成了聽眾。
兩人一見面,話匣子那就沒了開關,二舅操著濃厚的“此地佬”方言,我先是聽不太懂,幾回半蒙半猜,也只是知道了一個大概。每年初四初五聊的話題,幾乎一個模樣的年年如此,無非就是莊稼人的農耕家事。一方水土一方人,哪家的事說開了還不是差不多?真不知這些有啥說頭。可是說者不厭,聽者不煩,一問一答,一應一和,老兄弟倆積攢了一年的情感,如同汗水浸透每一管毛孔,必須要有噴涌而出的那種酣暢淋漓。
這個花園里的二舅,哪來那么多的閑話?年年都是“老三樣”。我是母親最小的女兒,當年農村大集體年代,記事始起母親已過半百歲數,諸多繁重的農活體力不支。二舅的這場正月走親戚,老母親進入臘月就開始了準備。“十碗頭”齊齊地擺上了飯桌,尤其是那一塊塊肥瘦相間的粉蒸肉切得方方正正,而且都是上好的五花肉,連皮帶肉的四指膘厚,還有那一粒粒雞蛋大的肉圓堆得滿滿當當……母親拿出了看家廚藝接待“花園里”二哥。一座座雞鴨魚肉堆砌的“峰巒”直抵二舅面前:二哥,你吃,你吃啊!說了好半天了,怎么不動筷子?
說話間,母親手里的筷子飛舞起來。好在二舅身體也棒,牙口正好,吃啥都香,少不掉的一番大塊朵頤。二舅面前那只大碗堆起的“峰巒”,轉眼間海拔削了一半,一旁的母親這才有了些安頓。可不是嘛,那是母親大半年難得一見的娘家二哥,那又是我們家那些平日里難得一見的菜肴——畢竟也只有到了歲末年初的“新正月”里,我們才能一飽眼福口福的烹調絕活。直到她的娘家二哥吃累了,母親這才咧開整齊的白牙,撩起圍裙收拾殘桌……遠望母親忙碌的身影,我有了些后悔,也不知母親她自己吃沒吃飽吃沒吃好——她可是忙了大半天,難道就是為了聽到二舅這些陳芝麻爛谷子的嘮叨?
只有去過“花園里”之后,我才看出來了,我的這個二舅,在那個村子可有名氣了:老黨員,老隊長,少說多做的他可有威信呢。之所以每年新正月里到我們家一吐為快沒完沒了,可能是忍辱負重久了,心里憋著太多的事。
3
那些年,與“花園里”的一次次親密無間——跟在父親或是母親身后走親戚,一溜煙地直奔“花園里”。
其實,昨晚上就有小伙伴搗亂了,他們告訴我:你家二舅住的村莊,怎么能叫花園里?別聽名字叫得好,其實那就是一個光禿禿的村子,滿村里哪有什么花兒?
我才懶得信他們呢。
要不,你就聽聽——村上大人怎么與我父母拉的家常:“去花園里?”
“是的喲?”似乎遙遠的前方,昨夜那個村子里的誰,送了一朵花兒綻放在父親或是母親的臉上?那么,是不是每個像是我二舅那樣的村里人,都住在鮮花盛開四季的花園里?女的嘛,是姐妹仙子;那么男人呢,又是怎么稱呼?
我哪能搞得清楚?要不,怎么大年初一天還沒黑凈呢,我就睡不踏實,一心想著第二天一大早,一根“小尾巴”似的墜在大人后面,去“花園里”拜年?
回回都是上下一身簇新。這還不算,母親臘月里納好的黑燈芯絨松緊口鞋,讓我飛快的小腳瘦成“三寸金蓮”;雪白的布紋牙邊踩著上凍的土埂,那不就是多了一個他鄉的小公主神龍活現?兩尾剛剛梳起的丫丫辮子,一左一右對稱翻飛的紅絨花——哦,哦哦,可是等不及了,直奔“花園里”,那幾個表姊妹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等著我,再怎么說咱也得在那個鮮花泛濫的村子颯爽一把。
沿著圩堤一路疾走,清亮亮的小河纏繞著,恨不得摘了這樣的一條玉帶扎在腰際。十幾里地下來,還沒到“花園里”,鞋口的雪白布邊污黑著臉,一雙腳恨不得扛在肩上,那可真的是拖不動了。“二舅那里,昨晚下塘起網的鱖魚,嘿嘿,我都聞到香味了。那可是我家丫頭最愛吃的。這要是去晚了,你那些老表,兄弟姐妹們,他們才不客氣呢。”
父親這么一聲“嘿嘿”,立馬的我騰起身子撲進村子。“這是——哪家的小妖精?一陣風來下凡塵?”二舅母還沒笑完,身旁的一聲喊叫洶涌而出,“哎喲,我的老姑娘真漂亮!花園里哪見過這么個美人胚子,從年畫上飛來的吧?”
二舅,真煩人!我一個白眼一撅嘴巴,一溜煙出了屋。早就等在一邊的表姐妹們,拉扯著我一路瘋玩,哪里還想著什么鱖魚?
一時間,仿佛村上所有的樹,靜靜地站立成了淺淺的水草,我們才是穿梭不停的鱖魚呢。
可不是么?正是仲春的日子,濃烈的油菜花隨手灑成漫天滿地的金黃毯氈,嫩青的麥浪卷成一堆堆浪頭,還有粉色紫云英撐起一傘傘云霞……是不是她們這些花朵們,一朵朵一束束一叢叢地對我無言抗議著,“那個外村來的小姑娘,你不是一直猜疑么?沒有這金黃嫩綠粉色的千紅萬紫,還敢叫‘花園里’?”我才懶得回話呢,那把母親從小鎮上買來的花紙傘,還有在村上小伙伴那兒借來的花汗衫——姹紫嫣紅之間穿梭的我,不就是一只紛飛的花蝴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