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3-08-12 來源:安徽作家網(wǎng) 作者:安徽作家網(wǎng)
我省作家張琳中篇小說《奔馬》首發(fā)《四川文學》2023年第04期,見刊后,被《小說選刊》2023年第07期、《中篇小說選刊》2023年第4期轉(zhuǎn)載。《中篇小說選刊》同時刊發(fā)張琳《奔馬》創(chuàng)作談《逐夢中的隱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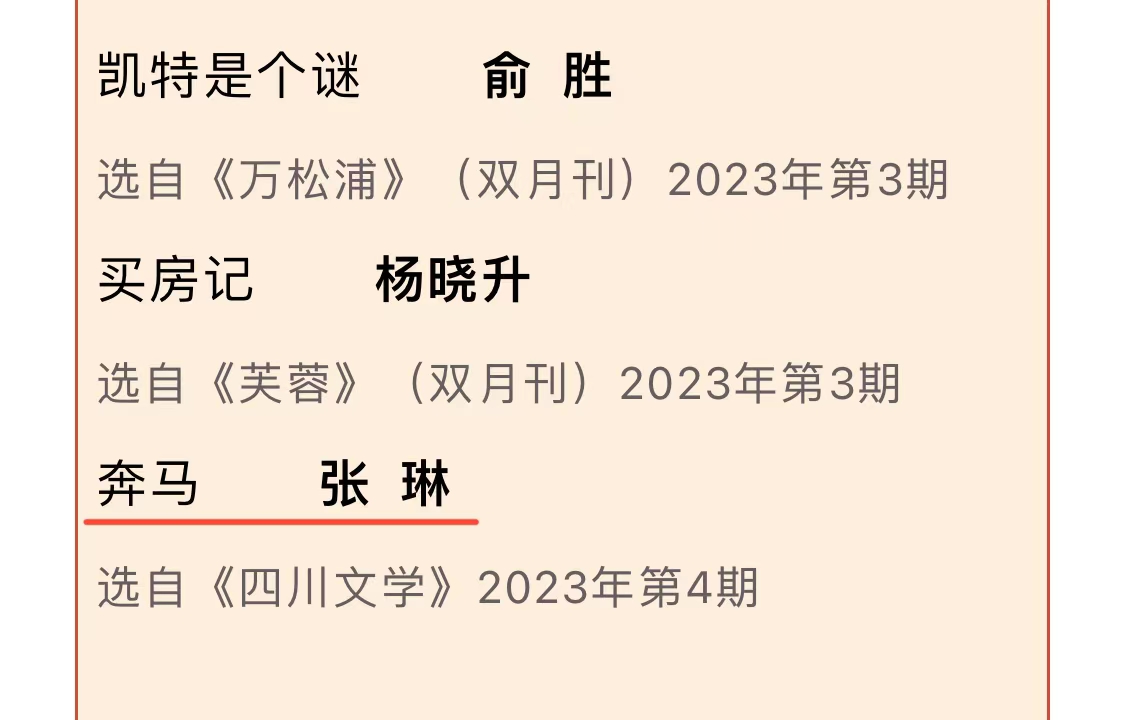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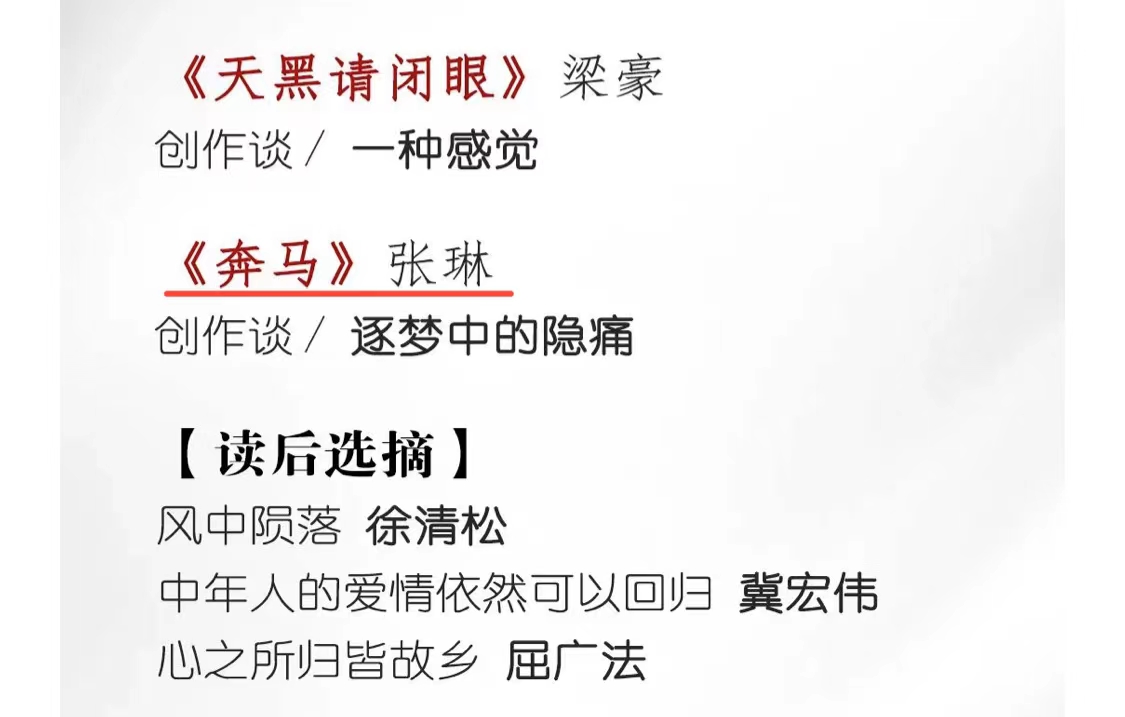
胸前口袋里別著鋼筆,騎奔馬牌自行車,村里第二位吃上公家飯的馬紅旗,伴隨著陣陣記憶里動人的車鈴聲,在黑夜中從村頭的公路上,由行將遠去的從前,悠悠駛來,緩緩清晰,那群隨著自行車恣意奔跑的無憂少年,倏忽之間,已然中年。張琳的《奔馬》,語言自然樸素、清新靈動,描繪了曾經(jīng)有限的鄉(xiāng)村教育資源下,以馬紅旗為代表的一群青年和少年的往日時光與人生選擇,有熟悉和遠離,也有傷感和蛻變。一代人的青春、成長、蒼老、逝去,如無盡宇宙中的星辰燦然明滅,深深淺淺的軌跡證明每一個個體確乎存在過,亦將湮滅于時間的塵埃中。
(《小說選刊》2023年第07期)
逐夢中的隱痛(創(chuàng)作談)
張 琳
很小的時候,到外婆的村莊走親戚,遇見了一場相親。相親的姑娘是表舅家女兒,我該喊她表姐。當相親的小伙子騎著自行車由遠而近,我看到他極力控制身姿的左右搖擺——那是個子矮小、腳踩不到底腳踏子的緣故,近了又看到他皮膚黝黑滿臉粉刺,心底直為表姐叫屈。表姐長相俊美,身材高挑,在十里八村都可稱為一枝花,她曾經(jīng)因為聯(lián)合幾位村里的姐妹發(fā)出移風易俗、不要彩禮的倡議,被當時的地區(qū)黨報報道過。聽圍在院外的村里人議論,才知道小伙子是一位煤礦工人。這次相親無疾而終,表姐后來也走出鄉(xiāng)村,成為一家國企下屬服務企業(yè)的總經(jīng)理。
少年時期無意中遇見的一位相親的小伙子,多年后在我的頭腦中形象愈加鮮明起來,我總在想,他此前及以后的生活是一種狀態(tài)?終于有一天,我給他取個名字“馬紅旗”,叫他成為了《奔馬》中的主人公。
黃淮海平原上的盛莊,遙遠,閉塞,貧困,是馬紅旗追逐夢想的起始點。他志存高遠,心地善良,身處厄境,卻不安于現(xiàn)狀,執(zhí)著地追尋著自己的夢與遠方。圍繞著鄉(xiāng)村青年馬紅旗,小說中又設置了幾個角色,鄉(xiāng)村中年盛世榮,鄉(xiāng)村少年前茅、山貍貓和豆蟲等人。盛世榮是他們的老師,同時,他又是馬紅旗的文友,而幾位鄉(xiāng)村少年則是馬紅旗的“跟屁蟲”,就仿佛師徒之間的“傳幫帶”一樣,他們一人影響一人,有的彼此影響,潛移默化中萌生了各自的夢想,向往外面絢麗多彩的世界,希冀走出鄉(xiāng)村,闖蕩遠方……我試圖直探他們的心靈深處,寫出他們成長的苦悶與追求,寫出那個年代所有鄉(xiāng)村青年的內(nèi)心隱痛。
小說結尾,盛世榮站在村口大路邊,頭腦中依次閃現(xiàn)出馬紅旗、前茅們的生活現(xiàn)狀,他發(fā)現(xiàn),懷揣遠大夢想渴望走向遠方的他們,如今大都在普通而平凡的崗位上默默工作,他們的遠方其實就在不遠處,有的甚至從一處鄉(xiāng)村到了另一處鄉(xiāng)村……當夢想照進現(xiàn)實,兩者的光圈鮮有能高度重合的,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產(chǎn)生或多或少的交集。——其實,這才是生活的常態(tài)。現(xiàn)實生活中,每一位追逐夢想的人,或許內(nèi)心都存有一段難以言表的隱痛,卻很少有誰怨天尤人,不管他們身處何時何地,總是默然走著自己的每一步。小說用“奔馬”自行車作為道具,就寓意只要騎行者不停歇,它就一路前行。——這更是生活的常態(tài)。盛世榮頭腦中對各人現(xiàn)狀的梳理并非閑筆,盡管水平有限,我依然想借此使小說的內(nèi)涵豐饒起來,從而讓一個原本是農(nóng)村青年奮斗、婚戀的故事,有了深層次的解讀空間。
黃淮海平原遼闊、坦蕩、肥沃,是我的家鄉(xiāng),我熟悉平原上吹過的每一縷風,每一聲鳥鳴,每一段悠揚、粗獷的牛歌……和《奔馬》一樣,我寫過一些以黃淮海平原為背景的中短篇小說,我以后還會寫,以此向這片令我魂牽夢縈的大平原——哺育我成長的神奇厚土——致敬。
張 琳
……
清晨,馬紅旗騎著摩托車從村街上拐上公路,駛上了返礦之途。昨夜的一場小雨,將路面的浮土打濕,黃沙土路面被水滋潤透了,平坦得像礦上的柏油路面,被兩旁高大的白楊樹護衛(wèi)著,綢緞一般飄向遠方……正是秋高氣爽的時節(jié),空氣中,滿是清新的泥土和莊稼味兒。坐在車斗里的歐明麗哪有過這樣的生活體驗,她極為興奮,嘴里不停地啊著,說她有寫詩的沖動了。
馬紅旗突然發(fā)現(xiàn),前方平坦如鏡的泥土路面上,似乎被人用樹枝之類的東西涂畫上了什么,他減慢車速,接近了,才發(fā)現(xiàn)是幾個字。這個時候,歐明麗也發(fā)現(xiàn)了,她興致勃勃地辨認著地上的字,并大聲讀出來——美、土、陳。哎呀,美土,美土,美麗的土地呀,是愛情的紅線,把我與這方土地牽連,我甘愿做盛莊的素凈村姑……歐明麗兩手托舉,似乎捧著硬殼的文件夾,在礦禮堂的舞臺上,聲情并茂地朗誦詩歌。口占了幾句,歐明麗收回手,又發(fā)感慨說,這個姓陳的人是鄉(xiāng)土詩人哪,他將詩歌發(fā)表在故鄉(xiāng)的大地上。她仰頭問馬紅旗,紅旗,你說你是盛莊的外家姓,你們盛莊還有姓陳的呀?這個人還蠻有才的呢。馬紅旗咕噥了一句什么,手旋油門,摩托車立馬加速,噴出一股黑煙,將歐明麗口中的發(fā)表在大地上的詩歌越甩越遠……
一開始,馬紅旗讀到“美土陳”三字的時候,覺得匪夷所思,摩托車駛過這幾個字,他又扭頭瞥了一眼路面上的字,這時候,他讀到的是“陳土美”。馬紅旗心底不禁一懔,他知道,寫字的人不僅將中間的字寫成別字了,而且還將別字寫成了錯字。是有意為之,還是無意出錯呢?
馬紅旗知道,他在村人的眼里,已成了陳世美一般的人物。
那一年,豆蟲回鄉(xiāng)過春節(jié),他大學畢業(yè)做了老師,早已成為公家人。當年高考填志愿時,豆蟲想都沒想,就填寫了淮北煤炭師范學院,這所大學,曾經(jīng)叫過安徽師范大學淮北分校,他少年時從馬紅旗那里知道的,之后就一直銘刻在心上。他還知道,馬紅旗考了三次都沒考上,就放棄了,而他豆蟲考了兩次,幸運地被錄取了。畢業(yè)后,豆蟲被分配到淮北一家煤礦的子弟中學教書。
前茅和山貍貓都沒有讀高中。前茅成績好,初中畢業(yè)就考上省郵電學校;而山貍貓讀書不行,但身材靈巧,上躥下跳,如履平地,初中畢業(yè)第二年,參軍到了部隊,成了一名偵察兵。
臘月廿七那天中午,豆蟲叫娘準備一桌子酒菜,請村里幾個干部和走得近的人喝酒,盛世榮也被邀參加了。一桌子人猜拳行令,酬酢甚歡,全都喝成了關公臉。不知是誰說了一句,豆蟲,你和紅旗都在淮北,應該見過不少面吧?村人關心馬紅旗,是因為他結婚成家后,回村的次數(shù)越來越少,后來又把他娘接到了礦上,村人就難得再見到他一面。豆蟲說,到淮北這些年,我也只見過紅旗哥寥寥幾次,淮北大著呢,比咱縣面積都大得多。
豆蟲喝得紅頭漲臉,說話也口無遮攔了。他說,你們都見過紅旗哥的媳婦歐明麗吧?她現(xiàn)在是紅旗哥所在煤礦礦工醫(yī)院的護士長,正巧,我們學校一位老師的丈夫是那家醫(yī)院的醫(yī)生,我向她打聽歐明麗,她就問了她丈夫,告訴我了歐明麗的故事。盛世榮一聽,想打斷豆蟲的話頭,忙說,豆蟲,換話題,來咱哥兒倆搳幾拳。豆蟲卻沒接茬兒,兀自往下說——
歐明麗呢,其實是紅旗哥舅家表哥的媳婦。他表哥好像叫趙什么軍,礦上的保衛(wèi)干事,愛釣魚,一休息,就在江河湖汊邊轉(zhuǎn)悠。有一年,在塌陷區(qū)釣魚的時候,不小心觸電身亡了。當時,歐明麗還不到三十歲,帶著倆小孩,一個讀小學,一個上幼兒園。歐明麗是知識女性,有主張,敢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向紅旗哥的大舅大舅媽說出了改嫁的想法。紅旗哥的大舅大舅媽很頭疼,改嫁是人家的自由,不能干涉。但兒媳婦改嫁了,倆孩子咋辦呢?紅旗哥看在眼里,也替大舅家著急。紅旗哥想,他要是和歐明麗組成家庭,大舅家的后顧之憂不就解決了?有一天,紅旗哥來看大舅大舅媽時,鄭重其事地說,表哥不在了,我就是您家兒子,然后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懇求大舅大舅媽向歐明麗提一提。大舅大舅媽一合計,感覺這主意不錯,就瞅個機會,向歐明麗說了。沒想到,歐明麗一聽,就扭扭捏捏同意了,她早知道紅旗哥發(fā)表過文章,有追求,是一個前途不可限量的人。而她呢,也是一個做文學夢的詩歌愛好者。不久,紅旗哥就由井下調(diào)入了礦保衛(wèi)科,成了一名整理文字材料的內(nèi)勤……
其實,豆蟲剛剛唾沫橫飛開始說上面一番話的時候,盛世榮就走出了豆蟲家,一個人搖搖晃晃走上村街,向公路走去。豆蟲講述的故事,盛世榮當時就知道,馬紅旗向他和盤托出了,并央求他向吳校長家打個圓場:說他馬紅旗只是一個井下采煤工人,配不上人家?guī)煼渡鷧呛Q啵徽f他馬紅旗是一個自卑心很重的人,和吳海燕在一起,他心里頭有壓力,出不開身。馬紅旗婚姻的事情,盛世榮一直替他保密,就連前茅娘他都沒給說,怕娘兒們嘴碎,不小心給捅出去。沒想到,擔心娘兒們說出去的事情,卻被一個讀過大學做中學老師的男人散布出去了。
豆蟲家離公路近,盛世榮很快就拐上了公路。這時候的公路已鋪成柏油路面,且拓寬許多。因為路面拓寬,路兩邊高大的白楊樹也被砍伐掉,新栽植的樟樹還很幼小,沒有形成綠樹夾道的氣勢。盛世榮一邊極目向路的盡頭眺望,一邊任自己的思緒翩飛。村子里他教過的幾個學生的面孔,一個一個在他腦海里浮現(xiàn),他在心底默念著他們的學名,想著他們的行蹤……馬紅旗,一個執(zhí)著于夢想的隱忍青年,到現(xiàn)在,也沒能成為知名作家,卻一直堅守自己最初的夢想;盛加旺,兒子前茅,那個調(diào)皮然而成績優(yōu)異的家伙,如今在百多里外的一個山區(qū)鄉(xiāng)鎮(zhèn)做郵政所副所長,其實就是一鄉(xiāng)郵員,每天早出晚歸,騎著綠色的自行車在山道上奔波;盛世俊,就是反應敏捷動作靈巧的山貍貓,他出身于雜技世家,天生的做偵察兵的好料,幾年前就已長眠在南疆;盛世庭,剛才在飯桌上抖摟馬紅旗情史的豆蟲,口若懸河,侃侃而談,真不愧是做老師的;盛大巧,一個健壯質(zhì)樸的鄉(xiāng)村姑娘,如今跟著丈夫在蘇南打工,整日忙碌在一家民營紡織企業(yè)的流水線上……盛世榮想到了村里自己教過的幾位學生,也想到了做了一輩子民辦教師的自己,他的心突然感覺很酸很軟。也許是酒精的作用,盛世榮的眼睛漸漸濕潤了,他望向遠方的視線模糊了。
可盛世榮分明無比清晰地看見:鉆天的白楊樹枝葉相接,濃蔭匝地,樹間的一條黃泥土路平坦筆直,鋪向遠方,像極了一條穿越時空的隧道。馬紅旗騎著奔馬牌自行車從遠處快速駛來,自行車的前梁上斜身坐著前茅,后面車座上騎坐著胖乎乎的豆蟲,而山貍貓則撒開腳丫子一路追隨……青年跑調(diào)的歌聲和少年們的歡笑聲交織在一起,在丁零丁零的車鈴聲伴奏下,一波比一波更猛地撞入了盛世榮的心腔。

張琳,安徽碭山人,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安徽文學院第五屆簽約作家。有小說、散文等體裁文學作品發(fā)表在《中國作家》《清明》《飛天》《朔方》《廣西文學》《廣州文藝》等文學期刊,有部分作品被《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作家文摘》《新世紀文學選刊》等刊(報)轉(zhuǎn)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