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11 來源:安徽作家網 作者:安徽作家網
近期,我省作家木葉短篇小說《野放牛》發表于《山西文學》2023第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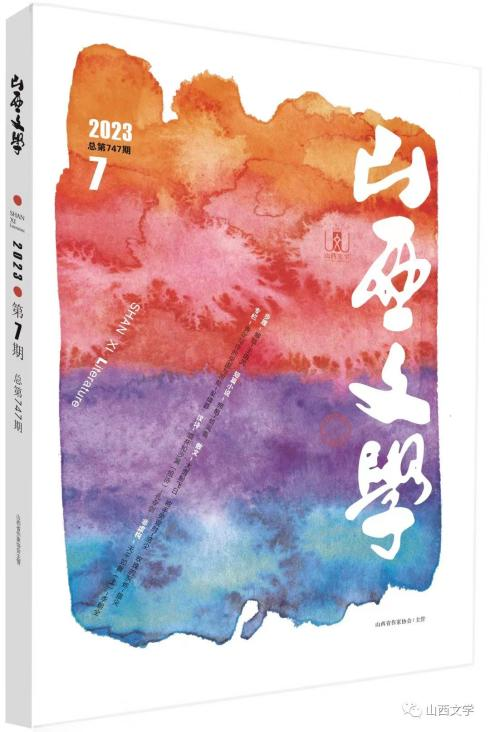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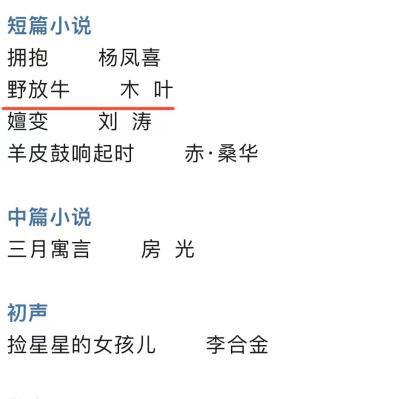
野放牛
木葉
一
報友五牛販六馬,不曉得該怎么去講他,總之,他潮流跟得緊,人活絡,哪種營生時髦,必定脫不了他報友的身影。這不,疫情起來后,報友看做口罩就像印錢一樣嘩啦啦,不覺心動,籌資收了縣開發區一家倒閉企業的廠房,辦了起來。本錢不夠,六七幫忙弄來三分息的集資;連他弟弟報才都被鼓動,投進了十萬塊錢。哪曉得這種生意,都野狼般盯著,于是山洪暴發一般,來得快,去得也快,口罩的價錢像扎破的氣球迅速走低。高利息的借貸款繩子一樣牢牢捆住了報友。報友要解掉這個套,否則他也很快要“資金鏈斷裂”了。報友老婆為這已經氣得跑回娘家去住,口口聲聲要和他離婚。
好像任何時候、對任何人都會出其不意地“雪中送炭”的六七,昨天忽然找到報友,講現在有一個“天大的機會”。這“天大的機會”,是下倉鎮要把上馬墩上一群先前說是野牛、但后來冒出了主家的牛給處理掉。
上馬墩是湖里的一個荒墩,以前并不見有牛呀什么的,忽然出現了幾頭牛,也沒人當個事,沒想到不知不覺中繁衍成了一群。至于牛的主子,現在下倉鎮老一輩的人也傾向于認定,的確應該是住在老街上的時而昏昧、時而神神叨叨的一姝。
既然有主家,鎮里不好貿然自己就動手把這群牛捉了。但一姝腦子清晰時,根本不理會鎮上的勸,只說上馬墩是荒土墩子,只說牛在上面過得好好的,礙了哪個的事?有人給六鎮長出主意,說鎮上本就不宜也不應主動去和一姝談。一姝說她是牛的主家,只能算一姝一面之詞。現在是法治社會,講究證據,法律上無法證實,只能將就著,暫時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真談也談不攏。倒不如找個收牛佬,讓他私底下去和一姝談,悄悄地把事情解決了,不就皆大歡喜了嗎?六鎮長于是想到了六家畈的六七,一個電話把六七喊過來,說鎮里出面強行去捉上馬墩的牛,影響不好;比較好的方法,是讓你六七主動聯系一姝老太,一則說要生態保護,那么多野牛散在上馬墩,已經對墩上的環境造成了破壞;二則趁著牛肉行情好,賣了是一筆不小的收入,怎么買、怎么賣,談好了捉走就行,鎮里不干預。若實在工作做不通,鎮里最終可能還是要組織強行捕捉。最后一句話是六鎮長重重補的,說六七你要把政策和鎮里的意思,都宣傳到位,不能因為她一個人,不能因為這群野牛,誤了全鎮社會經濟發展的大事。至于怎樣說更妥帖,你自己去想。
六七姓六,但和六鎮長并沒有親戚關系。猴子精一樣的六七,不愧被人稱作鬼子六七,立馬想到了報友、報才兄弟倆。一姝是他倆的胞姨娘,一姝又一生未婚,無兒無女。
找到了這兄弟倆,事情不就有七八分的眉目了嗎?六七的眼珠骨碌碌地轉。兄弟倆當中,弟弟報才不像圓墩墩的報友那般慣于在社會上縱橫。他起先的時候,在報友腳下,種平菇魔芋、養黃鱔老鱉毛蟹,如此三番,做了一段時間,也積了一些小錢;后來遇上個機會,在派出所里做輔警,算是安定下來。
二
一丁早就聽說了鎮上要把上馬墩的牛處理掉的事。一丁后來在鎮教育辦主任的任上退的休。不大不小的下倉,他要算個人物。
狹長的老街斷斷續續還在,雖說禁了湖,空氣里依然飄蕩著隱隱約約的魚腥味。剛下過一場暴雨,暑氣因此不重。鎮政府大樓右側有一條向下的砂石路,通到湖邊。大早上,一丁穿著長筒膠靴,立在湖邊,正專注地撈湖浪打過來的菱角殼,完全沒注意到已經悄無聲息走到了他身邊的一姝,待側過臉,猛地瞅到一姝,不覺一驚,忙問:“一姝姊,你怎么不多睡一會,這么早就起來?”
一姝說上年紀睡不著。
“收牛佬昨天上午托我那兩個侄子來做說客,可笑。”待了會,見一丁還在忙碌,并不和她搭腔,一姝低聲補了句。
“報友和報才回來了?我冇見著哦……好啊,發財了啊,你將一下都好了。”
“發么事鬼的財,我一把年紀,還要發財做么事!我就不賣。”一姝嘀咕。
湖面上,一座大橋突兀地直戳戳立著,在湖心拐了個彎,通往渺渺茫茫的湖對岸。橋有十來公里長,雖已經造好,但兩岸的連接線工程還沒有完工,因此沒有通車。
一丁直起身子,說莫孬了,這些牛說是你的就是你的,說不是你的它就不是你的,你當真犟得過?邊說邊作勢晃了晃手掌,遙遙對著邊上的鎮政府大樓。
“做么事,我放的,養的,還變得脫?”一姝來氣了。湖風吹過來,掠起一姝稀疏的頭發。忽然又癡癡地看著一丁:“這些牛本來都是你的。”
一丁下意識避過眼神,彎下腰,繼續去撈蓬在腳邊的菱角殼。湖浪從湖心一層一層地涌過來,帶來黑褐色的菱角殼。湖里野生的菱角,有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死了,浮在湖面,漸漸就發黑。現在一丁把它們撈上來,預備曬干后做柴火。按說現在家家都是液化氣,柴火早就不怎么用了,但一丁家老屋保留了大鍋灶,一丁老婆說想煮鍋巴粥,指著一丁去嶺上扒柴。一丁先是撿了嶺頭上的松枝和松毛,這兩日在湖邊釣魚,見湖畔淤積了一片黑乎乎的菱角殼,就想著撈上來。
見一丁并不搭理,一姝莫名嘆了口氣,兩只腳一扯一扯地,松松垮垮走了。即便這樣,從背影看過去,依稀能見得出一姝的當年。話說回來,這里的女子,生在湖邊,長在湖邊,皮膚生嫩,面盤子姣好,身材婀娜,實在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待一姝怏怏走遠,一丁直起身子,抖了抖竹筐,瀝了下水,邁到岸上,拎起竹筐,估量了一下分量,覺得還適中,一把提溜了起來,也往回走。
天色還早。
拐過一截碼砌得整整齊齊的院墻,推開虛掩的院門,一丁進來,順手把竹筐放在右手邊的柿子樹下面,脫下長筒膠靴,套了涼拖鞋,正準備進屋里。一丁矮矮墩墩的老婆也早就起來了,正無頭的蒼蠅一樣在廚房里忙得不亦樂乎,她從窗子玻璃上瞥見了一丁,轉出來,立在門口咋咋呼呼地嚷:“毛魚!毛魚!昨夜叫你把曬干的毛魚收進來,你不聽,讓狗嚼的貓翻得爛七八糟,你看,你趕緊來看一下……”
一只腳已經在屋里頭、一只腳還在門外邊的一丁一看,果然,本來齊整地攤在竹匾里的毛魚,現在亂七八糟,有的頭沒了,有的半個身子不見了。一丁有些心疼,這些毛魚都是他前幾天摸黑打上來的,預備曬干后帶給城里的女兒。平日里一丁一般是任他老婆怎么說都不回嘴的,今天居然破天荒沒好氣地說:“啊,我冇收,你不曉得收一下,百事從來只曉得怪我,我又不是神仙……”
“么事神仙不神仙,這滴事,動一下手和腳,跟神仙不神仙有么事關系?懶!懶了一輩子,我也跟著你受累一輩子,百事都是我的!”
“反正將快著,橫豎日子也到了頭!”
一丁怕老婆是全鎮的人都知曉的事。這幾十年過來,下倉從一條破舊的老街開始,已經大大地變了好幾回模樣,比如新街上如今竟然辦了一家“國際大酒店”,這事要放在三十年前,不可想象;一丁怕老婆這件事,從他青年時期到現在,卻沒有任何改變,幾乎被本鎮所有的居民始終津津樂道,無論鎮上的干部,婦孺,還是行路的青年男和女。甚至成了典故。對于一丁怕老婆,一般來講分成兩種觀點,一種是“你看一丁那慫樣”,另外一種是“你看人家一丁對屋里頭人多好,冇得一滴脾氣”。
突然響起了鞭炮聲,在這個早上,清清脆脆的。那是下街的滴五家昨夜老了人,早上一丁從他家門口過的時候,看到他家的子侄們正在搭靈堂。一丁老婆還在數落,聲音又粗又大,毫無美感可言。一丁跨進堂屋,坐下,順手搗開收音機,按鈕輕輕地轉——他居然還保留著聽收音機的習慣,真是稀有的事——里面陸續傳出黃梅戲、國內新聞以及臺風山螞蝗會不會橫掃本省南部的討論等等,最后定格在經濟信息上,先是汽車空調等“家電下鄉”情況,后是天然氣啥的,再往后,女播音員字正腔圓,歡快地播報:“近期受消費需求以及國際牛肉收購價格上漲等多重因素疊加影響,我國牛肉制品價格漲幅已經超過兩成,這對于養牛戶是重大利好消息……”
“賣脫,賣脫,聽我的話不會錯。” 吃罷早飯,一丁在下街離剛搭起靈堂的滴五家不遠的鐵匠鋪正對面又遇見了一姝。這次一丁主動對一姝說。
“怪哉!是收牛佬托我外甥不成,又托你來跟我講?”一姝斜著眼,盯著一丁。
“哪里的話,人家找我做么事?我這真是為你好。”
“我曉得,你總是為我好,從來都為我好,好,都快要好到黃土里去了……”
“你不要老是包著氣講話,都這么大歲數的人了,不怕小輩看笑話?”
“我有么事氣?橫豎一輩子都過脫了……”
一丁語塞。訕訕地轉了話題,忽然說,一姝姊,你說我們當時怎么就有那么大力氣,能夠把兩只牛犢弄上船,也不怕它們亂動,翻了船?
這話頭沒轉好,一姝揚高了聲音:“還不是因為著你!哦,你慫,你一輩子慫,慫一輩子,現在老了,我還要跟你一樣慫?我偏不!”
又說,當日翻了船才好,大家都冇得煩心事了。
說話的時候,邊上沒有人。一丁不惱,嘿嘿地笑。
一姝娘家哥家早年丟過兩只小牛,沸沸揚揚好一陣子,當時還驚動過縣公安局派人下來調查,算得上本鎮治安史上轟動一時的大事。
三
回縣城的路上,天色暗得厲害,雖然才下午三四點鐘光景。報友先是把車子開得飛快,到底還是迎頭撞上暴雨,才過宋家塝,雨水就從天上嘩嘩潑下來。
報才縮坐在后座,無聊地看著車窗外面。什么都看不清明。車子現在速度放得很慢,報友小心翼翼地開著。圓墩墩的報友一副自來熟的好脾氣,他從后視鏡里看著報才,說天氣變得太快了,剛才還是白日頭當空,烤得人發懨,下午這一茬暴雨下得!
肯定是上馬墩那些野牛,在天上撒野,亂踩一氣,把老姨惹毛了,也把今天的氣象一下子搞亂著。報友故作輕快地說。
“再莫講著。要不是鬼子六七這個鉆土的,今天不得來!”報才截住話,顯然不想多說。忽見一輛車子四仰八叉翻在路邊,尾燈還一閃一閃亮著。“呀,呀……這……這喲……喲嚯好,冇把……把人傷到……到吧?”報才有些緊張。報才一緊張,容易口吃。車窗外,疾風急雨。
“車里頭冇得人。人應該冇得事,尾燈還在閃。”報友扭轉脖子,邊看,邊說。但車邊上并不見有人。“報……報個警……警……警吧。” 本來斜著身子靠在座椅背上的報才豎起身子,忙說我來,邊說邊從褲子口袋里掏出手機,撥了110。對方聽清楚后,說前面已經有人報過了警,救援隊已經在路上。放下手機,報才復又斜靠上座椅背。
約莫大半個鐘頭過后,車子進了縣城,雨也徹底停了。空氣豁亮,離城有好幾里遠的河西山被洗得就像長在眼前,清晰得格外青蔥。七拐八拐過幾條街,兄弟倆到了家。報友和報才兩家毗鄰,當初一起買的地皮,又是同一伙石匠師傅造的,都是兩間三層,前后各有一個院子,前院淺小、后院深長,院門一個式樣。這里是城西,以前管理松懈,起屋的時候四周還都是稻田,得騎自行車或者摩托歪歪扭扭才能進來,現在不同,房子聯絡著房子,儼然一條街巷。也確實是一條街巷了,街口前幾年豎起路牌子:紗帽街。
報才先下車,走進了自家的院子門;報友倒了車,拐進他自家院子。
報才進了大門,見他媳婦正在堂廳和隔壁的幾個女人吆五喝六打麻將,空調開得嘶嘶的。報才悄無聲息要上樓。剛到樓梯口,手機響了,掏出來一看,果不其然,六七的。報才緊走兩步,進了二樓房間里,接通電話。六七也不寒暄,直接就問,到家了吧,你姨娘工作做通冇有?報才說,我……我幾個做外……外甥的,難……難哦,一上午,嘴……嘴都講干……干了,死……死都不……不同意……同意哦。電話那頭,六七抬高了聲音說,這咋辦?實質上,我看這事同意要同意,不同意到最后還是要同意,這個道理,你哪會不曉得?再講,這也是個機會,順水推舟。完全是天上掉下來的機會,我這真是為你哥好,為你兄弟倆好;按理,上馬墩上的牛,縱使是你姨娘的,你們也該占份……催債的人天天找我,我只能抵擋一時……
報才說,我咋不……不曉得,這……這樣,我再……再去和……和我哥商……商量下。忽然又說,急不脫的事,催個么卵。報才說這句話倒是利索,一點都不見口吃。
那邊六七掛了電話。
報才轉身下樓,去隔壁他哥哥報友家。報友癱在沙發上正埋頭刷抖音,手指頭滑動個不停,見報才來了,也沒起身,只用眼神示意了下,意思是坐。報友比報才要大八歲。報才手機又響了,低頭一看,老婆的,問剛到家,又要跑哪里去,夜里在家過夜飯不?報友說,什么哪里去,我就在隔壁哥家坐,你們在堂廳打麻將吵死個人,我在這邊坐一下再回去,夜飯肯定在家吃。不光我,還有我哥也一起吃。不等他老婆再講話,快速掛斷了電話。
報友、報才兄弟倆這次去下倉鎮,沒有料到會是這么個沮喪的結局。在他姨娘寒傖但整潔的老屋里,一姝冷茫茫地對著兄弟倆,當說起請收牛佬來捉牛的事的時候。冒失的報才自以為委婉而又不失聰明地提及牛原始的來源,被一姝一下子激烈地嗆了回去:你去叫你大舅舅從黃土下面爬上來和我爭。她口里的“大舅”,是她故去多年的娘家哥。
無本得利的“天大的機會”,就像天大的燒餅,遠遠地掛在兄弟倆面前,看得見,手伸過去,暫時又不能夠著。
“莫急,總會有法子。”一直在刷抖音的報友忽然抬起頭,對報才說。
“明朝我冇得工夫,要上……上班。這陣子縣里一直在……在創建文明城市,工作壓力緊得很,今天冇得法子,才勉強調……調的班。”報才回道。
四
下午,鎮里來了幾位省里的作家,說來采風的。一丁自告奮勇,和鎮干部一起陪他們。湖封了禁,并不允許漁船下湖。鎮上找來一條漁政船,突突駛進了湖里。湖面浩渺,船速度降下來,徐徐抵近上馬墩的時候,鎮里的宣傳委員細細介紹這汪大湖,以及當前的發展和規劃中的遠景。一丁瞪著一雙老眼,豎起身子,眼珠不錯地注視墩上,他想親眼再看看那群鬧得鎮上沸沸揚揚的牛。一只都沒有看見。
剎那間,一丁覺得有關那群牛的吵嚷是一場虛妄。
上馬墩靜靜地泊在湖中央,四周被蘆葦簇擁。菱角禾四散開,湖面上鋪了一層。對,就是這個季節,鎮小學英俊的青年教師一丁,和裁縫店里學做裁縫的一姝,竟然奔了大半夜,跑到一姝家屋場,把她家剛產下還不太久的兩只牛犢,神不知鬼不覺牽到湖邊,一丁搖開自家的船,搖到湖梢無人居住的上馬墩。兩人七手八腳,費勁地撥開菱角禾,把兩只牛犢趕上墩子。
兩只小牛犢,怯怯地,先是不肯上船,后是不肯下船,把他倆可累壞了。
現在,牛呢?都說是已經繁殖成了上百頭的牛群,為啥一只都看不見呢?湖水平靜,宣傳委員充滿激情地向作家們介紹,相傳媽祖娘娘去鄱陽湖,路過這里,一不小心落下兩只繡花鞋,一只是下馬墩,另外一只就是這上馬墩。現在,上馬墩有上百只野牛,鎮里正在考慮采取什么措施……作家們聽到居然還有野牛在墩子上,眼睛一亮,齊聲嘖嘖。
一丁的面前,同時浮起青年時代嫦娥般的一姝,和已然干癟的老婦人一姝。
全下倉只可能有一丁最清楚上馬墩那些牛的由來。時間太久遠了。回憶一丁的大半生,他可能也就在那天晚上豪壯了一次。一丁從來不敢跟人提及,相反,他諱莫如深,就像他常年不洗的茶杯,內壁里結了一層垢。
“你不要我,我也不要你。反正我把你放在上馬墩上了,隨你去野。再野也野不出上馬墩。”人說一姝心智不好,瘋瘋癲癲,一丁知道那是胡扯,瘋癲的一姝斷然說不出這樣的話來。那是有一年,一丁正襟危步路過一姝的裁縫店,一姝忽然追出來說的話。不過那時候,一姝的瘋癲已經全鎮都有名,大家都對她說的話不再當真,更不會驚訝。
但是一丁必定不能忘記,當年的青年教師一丁,不曉得有多少回,在湖邊明晃晃的大月亮下,曾對著嫦娥般的青年女裁縫一姝傻傻地說笑。他說要考研究生。他說要去好遠的地方。他說要娶一姝做堂客。不過不是現在。他說現在他沒錢,他說甚至現在鎮教育辦卡著他,連報名考試的門路都沒有。
一姝比一丁大三歲,不知道哪來的熱烈,說有辦法,說她哥正籌辦養牛場。是的,她哥辦養牛場啟發了她,她也要養。養牛的地方她已胸有成竹,湖梢有一個荒土墩子,常年無人,草長得又茂密,牛犢放上去,既不會被人發現,又一定能長得好。牛犢哪里來?她顧不得了,她哥家的牛剛下了崽,她說先去偷偷捉兩只牛養起來,然后,牛生牛再生牛……說百事都要用錢,等賣了牛,再賣了牛……生活自然會肥肥美美……
一丁那時候一點都沒計較一姝“z、c”不分的方言。他一丁說話也從來都是“z、c”不分。相反,一姝銀珠子般的話,一串串雨滴般圓潤地落下來,經常讓一丁心慌打顫。
一姝娘家哥果真莫名其妙丟了牛犢。偷盜,尤其是偷盜牛啊之類,在讀書風氣淳厚的下倉,是稀有的大事。人們實在想不出,會有什么人能干出這種逆天的大事。她哥查訪了好多地方,既沒有發現哪個地方買賣了牛犢,也沒發現誰家忽然多出了兩只牛犢。牛犢蒸發了般無影無蹤。公安也調查了好一陣子,依然冇有頭緒,只得不了了之。她滿腔熱忱預備發家致富的哥罵罵咧咧了好一陣日子,也就算了。她哥做夢也不會懷疑到自家乖巧的妹子頭上。
青年一丁激動得有一陣子攛掇青年一姝,“我們一起私奔算了。”——二人畢竟沒出五服,注定得不到雙方家人的支持。一丁和一姝都姓胡。全下倉沒有雜姓。
“有手有腳,哪里不能過日子?”一姝說的時候,神態很媚。那是另外一天,湖邊上,無燈也無火,只有螢火蟲在四周亂轉。一丁記得,正是像昨天一樣,那天剛下過雨,腳前面一方泥地。一姝穿著長裙,腳下一雙涼鞋。“你背我過去,我不想把涼鞋弄臟了。”一姝吃吃地笑,揚起的眸子一閃一閃。
一丁二話不說,一把摟抱了過去。
美好的生活并沒有生出來。倒是愛情的火最終因何熄滅,無從問他一丁。一丁后來并沒去考學,和青年女裁縫一姝也漸漸疏遠了,有一陣子他去老街,會特意繞著走一條小巷子,以避開裁縫店。沒多久,他娶了供銷社剛分配來的一個外地姑娘,也就是他現在的老婆,人們說,他當時娶得那么急促,是因為外地姑娘已經顯了懷。是不是這樣不知道,但青年女裁縫一姝的確眼睜睜地看著一丁此前怎么討好、追逐那姑娘,甚至,那姑娘還到她店里做過衣裳,一丁陪她一起過來的,只不過斜斜地掉在裁縫店外面,假裝抽煙。他掩耳盜鈴地以為一姝不知道。
裁縫店逼仄的漫漫長夜里,一姝是否也有過悲痛欲絕,不得而知。人們看到的是一姝后來平淡無奇地繼續做她的裁縫師傅,直到很多年后,裁縫事業凋落,大家都更習慣去城里的服裝店買現成,也更洋氣的衣服為止。
一姝終身未嫁。下倉街上對此最具殺傷力的傳言是,不曉得什么原因,漂亮活潑的裁縫師傅一姝,那年春天,油菜花開得滿坂的時節,忽然身子燥熱,奔了油菜花田,脫了衣服,癡癡地又唱又舞,又哭又鬧。自此全下倉十里八鄉,一姝聲名大噪。這聲名自然斷送了她婚姻的前程。那時報才尚小,哪里辨得清這些世事的流轉?在他幼小的眼里,看到的是他的姨娘有時神神叨叨,有時寡淡無語,直至他漸漸長大,姨娘漸漸老去。
現在,報友躺在他縣城的家里客廳的木沙發上,看到的是實實在在的上百只牛,雖然是水牛。
五
一姝指著黨政辦的牛干事說,你姓牛?虧得你也姓牛!哪個敢講墩子上的牛不是我一姝放養的!我跟你講,我把話放在這里,誰都不能動,天王老子都不中!
鎮政府大樓上辦公的人都不做聲。年紀稍微上點的,知道一姝的瘋勁又上來了;年紀輕尤其剛招考來的公務員,有些面面相覷。六鎮長很惱火,他的辦公室就在黨政辦的隔壁。又不好從辦公室出來。民政辦的闊臉武主任趕緊從對面辦公室走了出來,說老人家,你上個月的低保打到賬戶上了吧!正好你現在人來了,單子還要你本人簽字哦,你來你來,來我辦公室。武闊臉邊說邊作勢伸開手,既像要把一姝拉了走,又像在保持某種時間和空間的停頓,并不去真正觸及一姝的身子。
一姝在鎮政府鬧的時候,一丁在家里渾然不知。那一刻,他老婆正兇著臉數落他全部人生的不是,一如平常,仿佛數落糟老頭子一丁就像她每天早上都會用臟兮兮的鋁茶壺給水瓶灌水,是他家生活必要且必需的一部分,雷打不動。也難怪,供銷學校畢業分配到下倉供銷社的一丁老婆,輕易讓一丁縻住了腳,好景不長,隨著國企改革的深入,成了下崗職工,尤其,受了一丁的蠱,年紀輕輕買斷工齡,搞得自己和家庭婦女沒有區別。
六鎮長按捺不住,從自己辦公室走了出來,清了清嗓子。他覺得可以用自己鎮長的威嚴鎮住這亂糟糟的場面。沒成想一姝瞥見他,照面撲了過來,六鎮長本能一偏身,邊上的人沒逮緊,一姝也沒穩住,直挺挺撞到墻上,轟隆一聲,癱軟地上,額頭上霎時血汪汪地。牛主任慌了神,忙叫六鎮長,鎮長你先回,先回你辦公室里,我來處理;那邊喚人趕緊聯系鎮上的衛生院。
鬧哄哄的場面一陣風樣瞬間散了,走廊里又恢復空空蕩蕩。工作人員都縮在自己的辦公室,大多數都假裝什么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忙碌自己手頭的活。幾個婦女在低聲七嘴八舌,說真想不到,一姝都一把年紀了,還會發瘋,太嚇人。
牛干事折到六鎮長辦公室匯報,說一姝還在鎮衛生院折騰,不過有護士看著,翻不起事;一姝之所以大清早跑到鎮上來鬧,據講是有人昨晚偷偷上了墩,不曉得誰眼尖看見了,告訴了一姝。一姝肯定以為是鎮里派人上去的。
六鎮長坐在椅子上,點起一根煙。煙細細的,不比以前的粗煙卷。六鎮長說我曉得了,你去忙你的。待牛干事出了辦公室,他掏出手機,慢悠悠撥了出去。電話那一頭是六七。六鎮長問,你昨夜是不是使人上了野牛墩子?六七也不隱瞞,說工作還在做;先叫人上去查訪,看究竟什么個情況。六鎮長大為生氣,說六七你是想渾水摸魚,人不知鬼不覺地先捉幾頭牛再講,對吧?六七忙賭咒發誓地辯,冇有的事,只是先上去看一看。六鎮長說你搞不好,我就叫旁人來搞,冇得這樣做事的,還冇開始,就搞得雞飛狗跳。你這樣個搞法,那我鎮里要找你做么事?!
六鎮長掛了電話,氣沖沖拎起包,招呼黨政辦安排車子,說要去縣里開會。
六
一姝從鎮衛生院轉進了縣精神病院。一丁是聽衛生院的人說的,據他們說,在于一姝住進衛生院后,太烈了,有天晚上趁著護士不注意,翻上了窗子。這可把衛生院里的醫生都嚇壞了,說皮外傷好治;但若是要跳窗子,我們可治不了。請示了分管鎮長后,送去縣城的專門醫院。
“牛氣又犯了!”他們說。
報友和報才弟兄二人去了一趟精神病院。她姨娘什么話都不說,枯枯地坐在房間里,除此之外,兄弟二人沒有見到其他異狀。從精神病院出來后,報才對報友說,哥,等姨娘完全好了過后,不讓她去下倉了,我們把姨娘接過來,就在縣里一起住,我家半年,你家半年。不行我家八個月,你家四個月。我前幾日刷到一個視頻,說合肥一個老頭,還是文化人,大熱天死在家里,兒子在國外,冇得人曉得,尸體都發臭了,叫來警察,撬開門,送到火葬場。也只七十多歲。姨娘即使從醫院回來家,一個人住,總歸讓人不放心。媽媽要是還在世上,肯定會支持我們這樣做。
鬼……鬼子六……六七去上……上馬墩捉……捉捉牛的時……時候,你要……要時……時時刻刻陪……陪在邊……邊上,過……過點細,莫又受他捉……捉弄,他……他這個人,不……不可信。頓了頓,報才忽然又結結巴巴,口吃的厲害。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四日

木葉,1970年生,安徽宿松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級文學創作。著有詩集 《大運》《象:十三轍》《我聞如是》《在鐵錨廠》《流水中發亮的簡單心情》等五種。另有小說及評論若干。曾獲安徽省政府文學獎等數種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