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6-26 來源:安徽作家網 作者:安徽作家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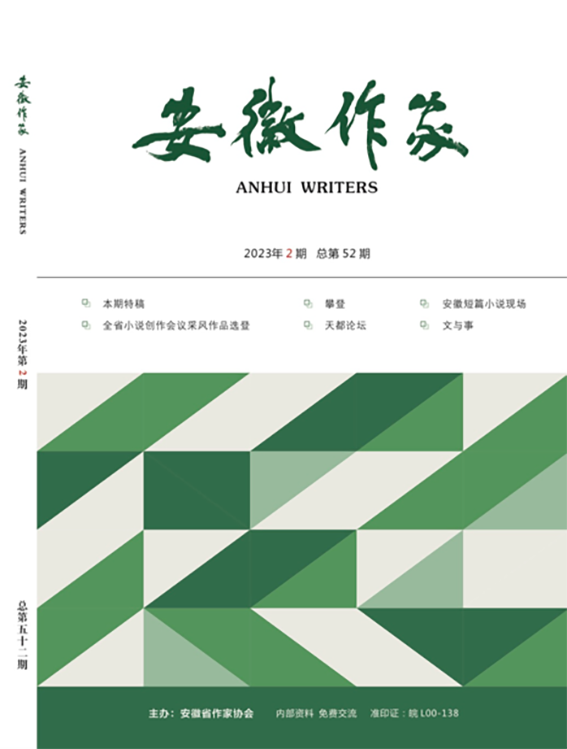
作品欣賞
樟腦丸
程迎兵
天色一暗下來,對面那個小房間的燈就亮了。丁小兵覺得那盞吊燈也許一直是亮著的,像在耐心等待著每一個黑夜的來臨。
那個大男孩頭戴耳機,坐在電腦前手忙腳亂,女孩則安靜地趴在床上看手機視頻。他倆好像從不到另一個房間去,洗的衣物也只是掛在防盜窗的格柵里。另一個房間的燈幾乎沒怎么亮過,偶爾亮一下也是男孩的媽媽在陽臺翻找什么東西,更多的亮光來自電視機的熒光,就如每個家庭都會有的那一兩個秘密一樣,微弱而模糊。
搬進這棟小高層快十年了。當初單位為了解決最后一批無房戶而把他安置在了這里。房子建筑面積六十三平方,兩間臥室朝西,客廳挺大但沒窗戶。丁小兵簡單裝潢了一下就搬了進來,剛搬進來時他和兒子都嫌小,現在丁小兵卻嫌房子太大。如今這三棟高層里更多的是老人,大多數中年人早已搬離這里買了新房。丁小兵不想折騰,也不想重復著上班下班,如同復印機般的生活,他想跟樓下那些老頭一樣活的悠閑和無聊。可時間久了,那些老頭看出他是真無聊而不是假裝無聊,就逐漸不帶他玩了。
今天早晨參加完同事的追悼會,丁小兵并沒有登上單位接送的大客車。頂著寒風的那一刻,一周前剛辦理完“提前退養”手續的他,忽然間感覺自己也老了。順著圍墻往前走時,身后的大客朝他禮貌性地按了兩聲喇叭,他停下腳步轉過身,朝司機擺擺手,卻抬頭看見山邊那根高聳的煙囪。他有些恐懼,抬手攔了輛出租車,飛也似地逃回了市區。
現在,丁小兵趴在窗臺上想一件事。對面樓里的燈光正漸次亮起,冬夜的心事如同這燈光,沒等徹底想明白,整棟樓就燈火通明了。
對于在單位選擇“提前退養”這件事,事后他還為此糾結了一段時間。還有五年退休的他,恰好符合單位新出臺的政策。對他來說應該五十五歲退休,但想想自己在單位也沒多大奔頭了,他便響應號召辦理了退養手續。其實丁小兵盤算過,也給自己留了條退路,本以為一套程序走下來至少要半個多月,萬一其間自己后悔了或許還有周旋的余地。沒曾想,辦事員僅用一個小時就給他辦理完結了所有手續,白紙黑字一眼便能望到頭,其效率快的像是擔心丁小兵下一秒就會后悔。
丁小兵事后甚至懷疑這項政策就是為他量身打造的。
走出單位大門的那一刻,丁小兵回頭望了望。兩株梧桐樹光禿禿的,凜冽的寒風對它沒有太多的辦法,此時的梧桐樹再也藏不住一只鳥,遮不住一滴雨,卻更像一個歷經滄桑的長者,在清冷中站出了豁達的姿態。
沒什么舍不下的,梧桐開春照樣會返綠。他對自己說。又想起臨出辦公室時,他還詢問辦事員五年后誰來通知他辦正式退休。誰知辦事員說,我明年就退休了,不過到時肯定會有人來通知你的。別急。
丁小兵蜷在被子里,像深陷一堆黃沙之中。
他想趁著夜色出去喝兩杯,便給朋友打電話。連打了兩個電話,其中一個在加班另一個還在外邊辦事,朋友們語氣匆忙,丁小兵都能聽見手機那邊傳來的呼呼風聲。他不甘心,又給另外一個朋友打電話,但對方懶洋洋地說,時間不早了明天還要上班,改天我請你吧。
丁小兵覺得無趣,便從床上爬起來煮面條。看著清湯寡水的面條,他更覺無趣。于是從冰箱里拿出西紅柿和雞蛋,做了個澆頭,再撒上一把青蒜末,面條頓時就好看了很多。吃完面,他趴在陽臺上點了支煙。
對面樓層的燈光沒什么變化,偶爾能看見人影在房間里晃來晃去。丁小兵仔細想了想剛才打出去的三個電話,誰又不在為掩飾自己的生活而撒謊呢?
看著依舊在打游戲的那個大男孩,他想起上大學的兒子很久沒給他打過電話了。他撥通手機,電話響了一會才被接聽。
我想起一件事。丁小兵說。
什么事?兒子壓低嗓門問。
我再想想……可丁小兵想了半天,也沒想出什么事。
兒子說,沒事我掛了啊。
別急。你在干什么?
我……在談戀愛呢。
哦,那我掛了。
對面大男孩正在拉窗簾。“呼啦”一聲窗簾擺動了幾下,一小片光亮從沒拉嚴實的窗簾邊鉆出來,散落在窗臺上。
這時候,丁小兵終于想起一件事。他想起剛進單位沒多久那會,那是一個夏天的夜班,二十出頭的他和師傅坐在廠區棧橋上乘涼,對面是檢修車間的小二樓。丁小兵記得當時他喝的是免費冰汽水,而師傅手里握著個搪瓷缸,喝著滾燙的勞保茶。
檢修車間大院里漆黑一片,只要沒有搶修的活,這個大院包括那棟二層樓,夜間沒有任何聲響,有時甚至能在身后嘈雜的機器聲中,聽見蛐蛐的叫聲。抽完一支煙,他準備起身再去接一杯冰汽水,他喜歡這種味道。他剛剛站起來,師傅卻一聲低吼——快蹲下!丁小兵本能地捂住腦袋,以為有什么安全事故突然來臨。
二樓靠西邊的一個房間燈亮了一下,又滅了,但很快又亮了。一對中年男女進了辦公室。“哎喲”,丁小兵看見師傅的嘴巴被熱茶燙了一下。
丁小兵說,有檢修?
至少今晚我們工段沒有檢修任務,師傅把右手食指豎在嘴邊,不耐煩地對丁小兵說,噓……話比屁多!
男人在窗前站了幾分鐘。丁小兵看見師傅把安全帽往下壓了壓。隨后辦公室的燈,滅了。丁小兵沒看出什么名堂,想轉身回休息室喝冰汽水,但師傅像早知道他要干什么似的,斷喝一聲——別動!
沒過十分鐘,大院里傳來幾聲狗叫,緊接著又傳來踹門聲。對面辦公室的燈亮了,門外多了個男人,屋內的男人“撲通”就跪下了,然后不停扇自己耳光,腦袋也不住地往地上磕。而那個女人則趁機一溜煙跑不見了,就像從來沒出現過一樣。
丁小兵至今還記得師傅當時的那句話。師傅說,這三個人我都認識,但做夢也沒想到他們之間會有這樣的故事。
大約半個月后,丁小兵在一次下夜班的路上,被人劈頭蓋臉打了一頓。多年后他想起這件事時,隱約覺得是他的師傅出賣了他。更多年后,他才得知那個跪下的男人,是自己初戀對象的丈夫。
此刻,不知哪個房間傳來悠揚的小提琴聲,丁小兵卻聽的很不耐煩。提前退休后,他發現其實生活許多時候都只是生活,那些發生過的事件,其實并沒有太多曲折,不過是隨著時間的河流平靜地打著漩,最終歸于生活。就像抽水馬桶里被人隨意扔下的一個煙頭,跟著水流旋轉了幾圈,最后還是頑強地漂浮在水封上,猶如有人吐了一口痰。
現在,丁小兵想起了早已退休多年的師傅。他想知道是不是師傅當年出賣的他,導致他被人莫名其妙打了一頓。
他翻看了一下手機通訊錄,發現自己居然沒有保存師傅的手機號。他問了幾個同事,都說不曉得。他有的是時間和耐心,把手機里同事的號碼挨個問了一圈。其中一個同事說他正準備出門喝酒,讓他也過來。
丁小兵下樓打車。街上的路燈昏昏欲睡,遠處擁擠的樓群看起來距離很近,但又都遙遠得那么真實。
出租車行車記錄儀里的畫面速度很快,完全超越了實景。巴掌大的畫面像是一個巨大的口袋,把前方的夜景吞噬進去,又吐給后排坐著的丁小兵。他感到眩暈。從前擋玻璃看去,夜晚的燈火卻又是靜止不動的,他宛如進入了一個奇幻世界。十字路口堵得厲害,前方汽車的白色尾氣徐徐上升,像某個人一聲不響地抽著悶煙。
飯店并不太遠,幾杯白酒下肚,丁小兵暖和了。他散了一圈香煙,然后翻看著手機里的頭條新聞,順便打聽了一下他師傅的聯系方式,同事毫不猶豫地告訴他,說他師傅去世至少有三年了。
這條消息與無數的頭條混雜在一起,顯得毫無特色更不抓人眼球。桌上的一個同事正給老婆打電話問能不能晚點回去,獲批后,對著電話說老婆你真好真寬容,掛了。隨著電話的掛斷,他臉也掛了下來,像什么都沒發生一般安坐桌前繼續喝酒。丁小兵注意到此人碰杯時他的酒杯永遠要低于對方。很多人都有這個好習慣,丁小兵也曾一度愛和他們較勁,比誰的酒杯端得更低,以至于倆人幾乎都是蹲在地上干了一杯酒。
丁小兵的手機響了,來電顯示是“快遞送餐”,他便直接掛斷了。退休后每次與同事聚餐時聽到手機鈴聲,他還是會下意識緊張一下以為又有搶修,隨后反應過來自己已經沒有了崗位。同事們還在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單位的事,他聽起來很陌生。同事之間不說真話地活著,深藏自己以維持彼此的關系,也許這對大家來說就是幸福的形式。當然,這也包括他自己。
鄰桌是四個女人,她們瞬間就吃完了,隨后三個服務員瞬間也收拾干凈了桌面,然后哼著歌——“夏天夏天悄悄過去,留下小秘密……”一切都神秘得如同周圍警惕的眼神。丁小兵端起酒杯,一口干了,然后扶住一個同事的腦袋,親吻了一下他油亮的光頭,說,我愛你兄弟。像在做最后的道別。
那天下午落了幾滴雨。
丁小兵抬頭看了看天空,天色陰沉。多年來,他在冬天看到過無數次這樣的天色,每一次他都有一樣的判斷,這天氣可能要下雪。但他又不確定,以前的經驗沒有使他確定過,總像是第一次產生了這樣準確的預見,將這種天氣和下雪聯系起來,像是提前看到了雪。
樓下的老頭們坐在大院門口的長椅上。丁小兵下樓轉了轉,想找老頭們玩,更想像老頭一樣活得沒有牽絆。但老頭還是不太樂意帶他玩,他想發火卻又找不出什么理由。有個老頭被牽著的兩條小狗扯得直趔趄,卻又不敢松開狗繩。看見丁小兵過來,老頭說,小伙子,最近是不是下了個文件說遛狗不牽繩要罰款?
丁小兵笑了。他說,規范養犬人人有責嘛。
兩個人坐在長椅上。老頭問,我看你年紀也不大,怎么不上班啊?丁小兵把提前退養政策說了一遍,老頭盤算了片刻,說,呆!你現在每月只有一千七百塊,還不到我的一半,月收入少了等你退休后工資會更少。呆,要是還有份掙錢多的事等著你嘛……你提前退養還差不多。呆,你以為有大把大把的時間是件好事?人閑著會閑出病來的。
丁小兵說,你說的有點道理。在職的沒退休的拿得多,不閑著能干什么呢?除了會開天車我也沒其他技能啊,再說了,干了一輩子天車工,我是再也不想干了。
那我倆還是同行。老頭拍拍丁小兵的肩膀,說,今年我六十五了,剛工作那會兒我才二十歲,從開始上班那天我就想,我肯定討厭一輩子干這重復的活。
沒錯。整天吊在半空中,無非就是把鋼錠吊來吊去,毫無意思。丁小兵說,那你后來換過工種嗎?
該死的,我到退休一直干的就是這個活兒。老頭話音沒落,就被兩條小狗拽走了。
丁小兵抽了支煙。是的,有大把的時間看來不是件好事,那只是一個幻覺,會讓自己感覺每天都很漫長,也很無趣,眼下就很難讓自己為個什么事而高興起來。剛退養那陣子,他覺得自己充實的生活即將開始,可是總會遇到某種障礙,他想是不是得先適應新節奏之后生活才會開始?
看著走遠的老頭和他的兩條狗,丁小兵反應過來,無趣本身就是生活。他只是長時間被束縛在了固有的生活節奏中,以至于他從來沒有嘗試過任何新事物,也沒有真正了解過。
他站起身,手機響了。電話是單位一個小領導打來的,先是關心了一下他的近況,又詢問他的天車操作證有沒有過期。丁小兵彎著腰如實作答。電話那邊說近期客戶訂單太多,而且很多有經驗的老師傅都退休了,年輕人又沒接上,問他是否愿意回來頂崗,倒夜班,每月暫定三千元。
丁小兵想都沒想,便同意了。
走出小區院門,穿過馬路就是一座公園,他想都沒想就走了進去。公園深處有個動物園,上次來的時候兒子還很小,大概只有三四歲,那個時間段丁小兵經常抱著他來玩。現在,他想自己去看看。
可能是天氣原因,公園里沒什么人,一個老師傅牽著一個小男孩走在前面。那是他以前的同事,丁小兵想上前去打個招呼,但最后還是放棄了這個想法。他看著那個老師傅把小男孩舉起放到肩膀上,吃力地往前走去。幾條小土狗,正在枯草地上亂跑,互相之間還時不時跟見到仇人似的拼命叫幾聲。
動物園近二十年沒有任何變化,蕭條得近乎荒蕪,飼養的動物品種都沒變,連鐵柵欄都沒換過,還是那么銹跡斑斑。孔雀、駱駝、梅花鹿、猴子都孤零零地呆在籠子里,一個飼養員模樣的人穿著膠靴,臉上毫無表情,拿根皮管在沖籠舍里的糞便。丁小兵轉了一圈,有點冷,他覺得這應該算是世界上最荒涼的動物園了,但它始終就在這個城市存在著,既不上規模,也不搬遷。讓人不知所以。
第二天一大早,丁小兵就穿著工作服去了單位。
干凈的工作服穿在身上有點緊,他活動活動胳膊,就登上了通往駕駛室的漫長樓梯。一切都沒變,廠房里那些鋼錠整齊排列著,一言不發,只等待著被丁小兵一塊塊吊起,輪流送進加熱爐內。地面上的同事忙碌著,從駕駛室往下看,他們仿佛一根根會移動的火柴,紅色的安全帽像是一個個火柴頭。他們聚攏片刻,分散開,然后再次聚攏。
雖然在半空中,丁小兵還是能夠聞到熟悉的鋼錠氣味,那是鋼鐵特有的腥味。不同的是,他現在聞到的氣味沒有了以往的那種冰冷。
幾個夜班上下來,丁小兵有點吃不消。在崗時每年年休假后回來上班,一點也沒覺得有什么不適應,現在才在家休息一個多星期,就有些適應不了以前的生產節奏了。他很清楚自己的這種變化,生活秩序從退休前的無序,突然變成了有序。準確地說,是現在的無趣變得有序,而且毫無變化。以前的無趣可以被無序遮蔽,現在的有序則變得更加無趣。
天氣預報一直說要下雪,但整個冬天卻一直沒下。尤其是寒冷的冬夜,只有凌冽的風醒著,讓人睜不開眼。已經零點了,丁小兵的夜班才剛剛開始。他去了趟廁所,廁所里的燈壞了,借著手機屏幕的反光,他順手帶上了蹲坑的木門。沒多久,又進來一個人,嘴上罵罵咧咧,重復著他剛才的動作。丁小兵沒吭聲。
手機鈴聲響起,與丁小兵的一模一樣。他看了下手機,屏幕并未亮起。隔壁的在說話,“我在廁所……急啥……丁師傅不是在天車上嘛……讓老家伙發揮余熱就是,休養費拿著還額外掙份工資,哈哈,打著燈籠都找不到啊……好好好,我馬上來。”
丁小兵仔細分辨著這是哪個同事說話的腔調,但這聲音很快就被廁所里的穿堂風刮不見了。他又蹲了片刻才出來,這次他沒有上天車駕駛室,而是拐到了爐臺長引橋下面。
他站在橋墩邊,點了支煙。凌晨有凌晨的氣勢,在鋼鐵般堅硬的空曠中,寒風在夜空中撲扇著翅膀,仔細聽能聽見廠房里天車剎車的摩擦聲。在他離開這里之后,一切仍像以前一樣,他的回歸并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他想,在這種壓迫一切的氣勢下,一次就業或退休,一次出生或一次死亡,其實并沒什么區別。
隆冬之后就是早春了,但其實也不過是另一個輪回的開始。深夜的廠區在丁小兵眼里還是那么恐怖,他抬頭看著路燈,路燈像一輪明月,從天上照耀著草叢和矮冬青,在泥土地上留下斑駁的光暈。路燈是沉默的,地面上的一切對它來說都一樣,無論春夏秋冬,無論萬物的生或死,它只是在等待天亮之后按時熄滅。這就是它的日常。
此時的丁小兵既不想回到天車上,也不愿再多想些什么,他就想讓自己這樣站著,直到白天的到來。
可能是太冷,丁小兵豎起工裝衣領往回走,他幾乎感覺不到腳趾的存在,堅硬的泥土很硌腳,但很真實。就像他想做個真實的有感情的人,但似乎先天條件不足,自己做的努力越多,卻越偏離越差勁,反方向得越遠,乃至感覺自己低于一個正常人的標準。當然,他也不清楚正常人的標準到底有哪幾條。
他這樣想著往前走。踏上水泥地后,他發現走著走著自己就偏向了右側,像是有人使勁把他往右邊推。他停下來跺跺腳,又抬抬膝蓋,等身上暖和些再往前走,兩條腿就聽使喚了。
直到凌晨六點,丁小兵才從天車上下來。駕駛室里的那臺窗機制熱效果太差,回到班組休息室好半天,他才暖和。休息室里三個同事都光著膀子在睡覺,充足的暖氣讓人感到燥熱。他仔細看了看他們,想分辨究竟是誰在廁所里嘲笑過他,可他們臉上油膩膩的,遮蓋了所有的表情。
丁小兵扯過兩把椅子,一把用來坐,另一把用來翹腿,很快他就睡著了。下班后洗了個熱水澡,然后騎著電瓶車跟同事去吃面。這是班組的老規矩,下了夜班幾個人分瓶白酒,吃碗牛肉面,再回去倒頭睡到下午,這樣既省了中飯,也緩過來了一夜的疲憊。
白酒四個人平均分,菜是面館免費的幾樣小菜和幾塊鹵干,以及各自面條上的幾塊牛肉。沒人說話,默默喝酒,夾雜著吸溜面條的聲響。
丁小兵暈乎乎騎車往家趕。剛過一個十字路口,就感覺車子往右邊突然一偏,然后眼前一黑。
丁小兵醒來時,醫院消毒水的味道便迫不及待地鉆進鼻腔,他被嗆得咳嗽了幾下。他想坐起來,卻發現右胳膊有點用不上勁。隔壁床的陪護連忙站起來讓他別動,然后按了下丁小兵床頭的呼叫器。
小護士很快就來了,跟她一起來的還有個男醫生。男醫生抓著個病歷夾翻看了幾遍,又啰里啰嗦問了一大通,然后讓他去做核磁共振,并讓他通知家屬來。丁小兵說,有什么需要簽字的我本人親自簽。
小護士出去又進來,手里多了床單和被套,是那種白綠相間的條紋,這顏色比以往一碼白看上去要親切。小護士扶他下床,然后給他換床單,她換床單被套的手法,讓他想到了賓館服務員的熟練。
做完核磁共振沒多久,醫生拿著片子又來了,告訴他診斷結果是輕微腦梗死,幸虧送醫院及時,目前需要住院治療。
那就住院吧。丁小兵很平靜,當天晚上他就把病床卡上腦梗死的“死”字偷偷涂掉了。他想給兒子打個電話,但想想住院也沒啥事,也就是每天吊三瓶藥水,晚上量次血壓、脈搏什么的,自己也能自理,就給單位小領導打了個電話。
醫院西側隔著條小馬路,是大學生公寓。每晚八點半左右,幾個小伙子就在水泥球場上打籃球,不時傳來陣陣叫好聲,而病房里另外三個老頭早已傳來打呼聲和斷斷續續聽不真切的夢話。丁小兵在病房過道里走了兩個來回,腰有點酸。他朝那三個床頭看了看,發現其中一個老頭沒睡著。他看看他,老頭也沖他擠了擠眼。
丁小兵躺在病床上,怎么也睡不著,他感覺病房有點兒像寺廟。有天晚上,走廊外傳來凄慘的哭聲,他突然冒出個念頭,感覺死的人是自己,哭的人是兒子。也許只有生死這樣的事才能把兩代人維系片刻吧?
丁小兵在走廊上抽了支煙,然后站在病房的窗前。又一場冬雨將至,深灰色的天幕下,高聳的樓群與低矮的商鋪都顯得有些沉悶。一片樹葉剛從窗前飄過,雨點就落了下來,先是幾滴,像個前列腺患者,緊接著雨滴變得密集,像是一個兒童對著草叢撒尿,很快把四周洇濕了。從醫院八樓往下看,CT室門前低凹處的雨點,在暗夜閃閃發亮。遠處的馬路上,疾馳的車輛,斑斕的雨傘,凌亂的電線,變幻的紅綠燈以及路邊草坪上的泥巴,所有這些他能看見的東西,很快就被人們匆匆的腳步沖刷得模糊不清。
才九點,正是夜晚剛開始的時候,醫院里卻是漫長冬夜的開始,猶如疾病沒有盡頭。
到了第五天,醫生就趕他出院了。丁小兵覺得自己也沒啥大毛病,是該出院了。在辦出院手續時,他不經意間,聽到一個年輕的醫生與科主任的神秘對話,年輕醫生說,主任,這次的實驗很成功,您放心!
丁小兵渾身一抖,感覺他們說的正是自己。
醫院離自己的住處并不遠,丁小兵并不急著回去,他走得很慢,順路還去吃了碗牛肉面。
老遠他就看見三個老頭在小區大院門口站著,走近一看,他們正圍著一只瘦小的狗。它是土黃色的,孤伶伶站在那里,不時擺著短尾巴。其中一個老頭說個不停,其余的老頭都沒吱聲,只半睜著眼睛,盯著小狗晃動的尾巴,仿佛馬上就要滑入某個夢境。
老頭看見他,問他這幾天怎么沒下樓找他們玩。丁小兵說去外地看上大學的兒子了。
到了傍晚,細碎的雪花悄然落下。丁小兵先是發現小區路燈下有白色的東西飄過,起初他以為是灰塵,沒多久樹杈間有了隱隱約約的白色,草地上很快就有了一層薄薄的積雪。他推開窗戶,伸出手,想奮力抓住點什么。漫天的雪花看上去相當繁華,遠處的山在夜晚的大雪里消失不見,連一星半點的痕跡都沒有。那里原本有一座山,此刻卻成為了一種幻景。
新的一天一定會從那些暗影中顯露出來。丁小兵這樣想著,身體搖晃了兩下。
對面大男孩房間的窗簾沒拉,燈依舊亮著。丁小兵發現屋里已經換了新住戶,一對年輕夫妻正在廚房里忙碌著,陣陣熱氣不斷從窗戶里飄出來。丁小兵在走廊上來回走了幾趟,醫生說康復訓練很重要。樓棟里不時散發出烤串和奶茶的香味,空氣柔軟而又富有彈性,他判斷這棟樓里應該搬進來了更多的年輕人。
這讓丁小兵很舒服。
(轉自《安徽作家》2023年第2期)
作者簡介

程迎兵,男,中短篇小說見于《青年文學》《長江文藝》《福建文學》《湖南文學》《清明》《紅巖》《野草》等期刊。出版有小說集《陌生人》《萬事都如意》《登山道》。有作品被譯介到國外。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安徽作協小說專委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