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6-16 來源:安徽作家網 作者:安徽作家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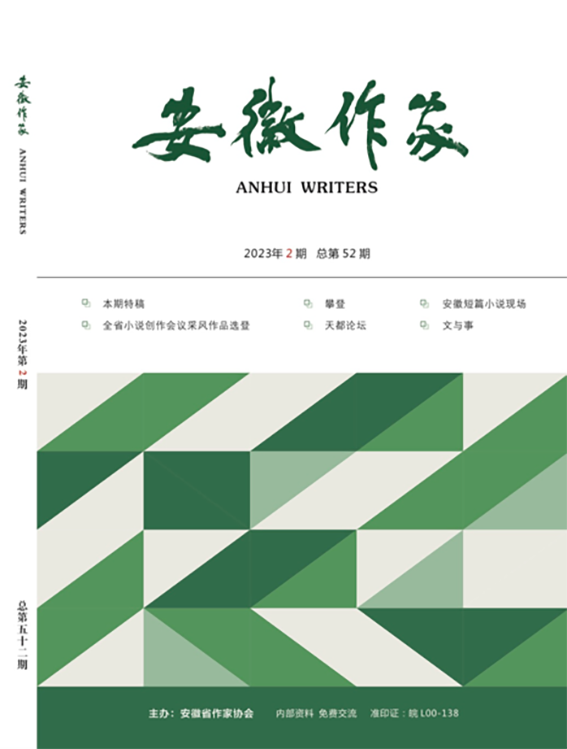
作品欣賞
溫暖的花海
苗秀俠
漸近陵園時,小路兩邊厚密的花海撲面襲來,幾乎將她與車完全淹沒。按指示牌引導,她輕撫方向盤,略帶點力,右轉至一條新水泥路。新路從鮮黃的油菜花地里犁過,逶迤成一個問號形狀,就像一句寫在地上的祝福。
到了陵園大門口,她才發現,原來進出陵園,新增了這樣一個環島,進來的車輛,要從油菜花地里繞行一個半圓;出來的車輛,直行,緩解了祭祀高峰期的擁堵。
泊好車,在停車場站一會兒,調整一下情緒。四年沒來了,一切仍是熟門熟路的樣子。陵園大門東旁的一溜店面,門口擺滿菊花,有盆花,也有抱花,黃菊白菊粉菊紫菊,粲然怒放,宛若一張張真誠的笑臉。她喜歡盆花,花泥能讓花兒綻放得長久一些。中盆三十元大盆五十元,她挑了兩只中盆,插著黃白雛三樣菊花,小小的紫色雛菊,有幾分俏皮,小仙女一定喜歡。
買了花,是否再買黃表紙,她有些躊躇。問店家公共祭燒區還在嗎?四年前她來燒紙時,就是在園內橋南西側的公共祭燒區完成的。很有特點的地方,墻上雕刻著屬相圖案,圖案下是一只只水泥砌的池子,根據逝者屬相,在池內焚紙。店家搖搖頭說,早扒掉了。看到她臉上的無奈樣,店家又說,只要能把紙帶進去,可以在墓前燒。可以嗎?連問了兩句,得到店家肯定后,她決定買兩捆黃表紙,好幾年沒來了,兩捆紙不算多。店家從床底下掏出沾著草屑的紙,拎了拎,有些重。店家說:“你自己帶不動,我幫你吧,你先進去,過會兒我送給你。”
她說了墓園區號,就拎著盆花進去了。
穿過高高的園區門樓,很快走過弓形小橋,進到墓園內。一片耀眼的鮮花世界,撲面而來。這荒郊野外的墓園,因有這些綻放的鮮花而顯出生機。這個被世間人鋪排出來的繁華,仿佛一個詩意的起點,通向每個人設定和以為的神圣的地方。
沿著松柏甬道,走近那個恒久之地。四年未見的小碑,因有周邊鮮花的簇擁,并不顯得荒涼。她用紙巾擦拭著墓穴的碑座和石碑,此時,一陣吱吜吱吜聲傳來,店家的腳踏三輪車到了。瘦削的三輪車廂,蓋著一層看不出原色的舊布,店家跳下車,掀開布,拎出來兩捆黃表紙,又遞了一盒火柴給她。她連忙道謝,居然,她都忘記火柴的事了,看來店家經驗老到得很。店家又把另外半捆紙,送給了甬道東側墓園的一對中年男女,那對夫妻正在給一座雙位墓穴上香。
解開捆紙的塑料繩,兩捆沒有約束的黃表紙,噗地攤了一地。一邊花紙,一邊和小仙女說道起四年未來的因由。花紙的技術至今沒有學會,她把紙對折起來,裝模作樣用指頭搓捻了半天,紙還是原先桀驁的樣子。她只好把紙握成帳篷形狀,在碑前放好,點燃起來。火苗夾著青煙,在風里舞。“小仙女,你知道的,大前年,做了一個小手術,就耽誤了時間,沒來看你了;然后,人間的疫情,三個清明節都沒能來,這次,媽媽終于成行了。今天的太陽真好,到處都是花兒,蠶豆花原來不光有白色的,還有淡紫色的呀;豌豆花開得真熱鬧,媽媽在路上都看到了。小時候媽媽喜歡掐豌豆花戴在耳朵上,當作耳墜,還唱著兒歌。想聽嗎?豌豆花兒朵朵,開在地心窩窩;爸爸搖耬耩地,媽媽撒肥春播。是不是很土啊,小時候唱著可好聽了。那片蘆葦呢,開著的花居然還是去年冬天的白絮花,從冬天走到春天,蘆葦戴著的那頂厚棉帽,你說熱不熱啊。”
她嘴里絮叨著。從未像今天這樣放松地絮叨,或許,疫情放開了的原因,更主要的,她退休了,出來不用再請假了。
她的腔調是開心的,就像來看一個老朋友,和老朋友敘家常一樣。最開始來祭祀時,未進墓園就淚流滿面,到墓碑前已經泣不成聲。那時候,她一年要來三次,一次清明,一次農歷的十月十五,一次春節前的年三十。不知何時,她來的次數少了,先是減成一年二次,后來一年一次,都是在清明節前。二十年來,再忙,一年一次來看小仙女,是一直的堅持,直到有了疫情。疫情前的那個春天,她做了個小手術,沒能成行。最后一次來還是2018年的清明節。往返來去中,年歲一點點堆積,就跨過了五十歲的門檻,流淚的次數少了,更多的是和小仙女說說話。開心的不開心的,都在小仙女面前說,說對了說錯了都不打緊。
小仙女九歲時,那場做夢都沒想到的疾病來襲,小仙女走了。病痛里的最痛,她全部品嘗。沒想到的是,尚未擦干眼淚,傷痛還沒愈合,新的傷害再次來襲。前夫痛心疾首地說,女兒在的時候,他是堅決不會離開家庭的,因為他愛女兒,現在女兒不在了,他重新考慮后,決定告訴她,他們還是分開吧。他早就不愛她了,他愛上了另外一個女人,已經三年了。真的,三年了。他說這些時,口氣是委屈和無辜的。其時,夜晚黑燈瞎火,兩人并頭躺在枕上,被窩顯出空曠。她聽到這些,居然是安靜的。她一動不動地躺著,一動不動,身體漸漸變得冰冷,是一種死亡才有的冰冷。
她第一次體會到活著是可以成死亡狀的。
他早就隨著新的愛人到遠方生活,而她,也離開了那座小城,調到省城工作。獨留下女兒在蒼茫的墓園。當初買墓地時,剛剛開發的陵園,一片荒蕪,在一眼望不到邊的空墓穴群里,女兒的單穴小碑顯得那么卑微。這也是她每每來祭祀時哭泣不止的原因。后來,死去的人越來越多了,陵園里的墓碑就豎滿了,女兒所處的這個世界,變得熱鬧起來。
“小仙女,你一直在天堂看著我們,你是笑著看我們啊。記得你喜歡穿白襪子,很長的白棉襪,可以蓋住膝蓋,那套粉色連衣裙,也是你最喜歡的。你就是穿著粉色連衣裙和白棉襪,參加六一兒童節表演的,那段集體表演的舞蹈非常非常棒,其中你最棒。從三歲起你就在市少年宮學舞蹈了,你的夢想就是當一名舞蹈演員……你還喜歡彈鋼琴,那時候房子小,打算暑假過后分到新房就買鋼琴,那時候學校新建了職工宿舍大樓,你爸爸是有些名氣的老師,完全能分到福利房的……小仙女啊,我說得太多啦,你煩不煩啊。不要煩啊,我能跟誰說呢?”
歡騰的紙灰像蝶兒飛舞,旋起一陣陣滾燙的熱浪,舔著她的臉和頭發。
“哎,你怎么能燒紙呢?你瞧,你還要燒這么多!不能燒!”
一個男聲從身后傳來,切斷了她和小仙女的對話。她有些愣怔地轉過身,一個高大的中年男人筆直地站著,穿一身青灰色保安服,滿目嚴厲,狠狠盯著飛旋的紙火。她想趕緊起身作個解釋,才發現,她的腳蹲麻木了,制約了起立的動作。
“瞧瞧你,居然,買那么多紙。疫情放開了,燒紙沒有放開啊。你不知道嗎?真是的。你以為能躲得過去啊,燒紙不冒煙啊。”他憤憤地說著,仿佛為自己的失職懊惱,聲音越發大起來。
她蹲著仰視著他,有太多的抱歉。她不知道,她怎么就在墓碑前燒紙了。這些年祭祀時禁止燒紙,她明明是知道的,然而,店家一說只要能帶進來就能燒,她一秒鐘沒猶豫就決定買黃表紙了。四年的相隔,她已經顧不得許多,她太迫切進到墓園里,讓紙變成火,讓火成為蝶兒,在蝶兒的飛舞里,她跟女兒說說話。那么多要說的話,沒有紙蝶的飛舞,怎么說得出來呢?
終于站起了身,有些趔趄。她本想說些什么,發現說什么都有狡辯的嫌疑。她萬般羞愧地小聲說:“以為可以燒呢,這也不是山林,周圍都是莊稼地……”
“無論啥地方,早就規定都不能燒紙啊。禁燒你不知道嗎?你說,我是罰你款呢,還是不罰你款呢?”男人走動了幾步,掃視著地上攤成一溜的黃表紙。她以為男人會一腳踩過來,把火滅掉,把紙踢飛。這是有可能的,因為她犯規了,要被制止,就得這樣,這也是男人的職責。但男人話鋒一轉:“你買多少刀紙?”
“買了兩捆。多少刀沒問。”雖然擔心會按購買紙的多少罰款,她仍然誠實地回答。
“那就是四十刀。你瞧你買這么多有啥用?買兩三刀意思意思不就行了。”男人的聲音更大了,一邊說著,一邊彎下腰,把地上攤的紙全部收攏起來,抱在懷里:“這紙,按規定要全部沒收了。”滿滿的一大懷,像抱著一懷的黃菊花。地上正在燃燒的紙,不知趣地旋成幾朵灰蝶,躍躍欲飛。正如男人說的,地上的紙,也就兩三刀的樣子,最多不超過五刀,因為,剛點著沒多久,而且,沒有花好的紙,不蓬松,燒起來慢很多。男人抱著紙站著,并沒有立即走開,反而指著地上著火的紙:“你紙不花就燒,有啥用。”
“我不會花紙,試了,捻不開,還是原樣子……”她覺得自己陷入了不知所措之境地,忐忑而羞愧。
突然,男子蹲下身,把懷里的黃表紙全部放到地上,兩手搓了搓,抓過一刀紙,恨鐵不成鋼地說:“紙要這樣花,對折起來,十個指頭要一起動,大拇指最關鍵,朝上推,下面的指頭朝下扒拉……”
他飛快地花開三刀紙,花得真漂亮,扇形,層層疊疊,像盛開的菊花瓣。她也連忙抓過一刀紙,跟著學,然而,她仍然沒能花開,那刀紙在她的手指間仿佛凝聚的時光,動也不動。
“其實光這樣花開了也不頂用,得先把一張一百元的真錢鋪在上面,挨著鋪,鋪一次,用手拍打一次,錢才能印上去;要一張一張地鋪,一張一張地拍打,鋪完了,拍打完了,再花紙,燒了才管用……”男人邊說,邊示范著鋪錢和拍錢印錢的動作。他張開粗糙的大手,像個魔術師那樣,先做出鋪錢的動作,然后,拍打著黃表紙上根本沒有的“錢”。然后,再換一個地方,再鋪錢,再拍打。她想到旁邊的包里應當有百元大鈔,決定去拿過來,讓他鋪錢印錢。她這個念頭剛起,男人猛地站起身,聲音又加大了幾分:“你說,我是罰你款呢,還是不罰你款呢。你燒這么多紙干啥,你真是的,真是的。”絮叨著,猛地彎腰抱起地上的黃表紙,頭也不回地大踏步走開了。
男人只抱走了十來刀紙,余下的,都還原封不動地攤在那里。
她盯著男人遠走的背影,一臉的淚就沒來由地潑出來。她閉上眼睛,任由淚水奔涌。明艷的陽光,摟頭蓋腦罩住她。“小仙女!”她喊了一聲,忍不住哭出聲來。
已是中午時分,來祭奠的人,陸陸續續離開了。安靜的墓園,只有她一個人。她一下放松了,再次蹲下身,學著男人的樣子,攤開一刀紙,鋪“錢”,印“錢”。她努力拍打著黃表紙,那一縷一縷的陽光,也隨著她的掌聲,被拍進紙里。之后,她雙手托住紙,十指有力地捻動,紙們聽話地排隊布陣,成為松軟的層次分明的扇形菊花。
花紙,成功了!
抓起花好的一刀紙,丟進火里,嘭的一聲,重新燃起的紙火,再一次燙灼著她的頭和臉。旋轉著燃燒的黃表紙,漸成灰蝶,在愉快地飛舞。在灰蝶的舞蹈里,她又跟小仙女說道起了被中斷的那些話。
兩只小小的菊花花籃,在碑座上放好,那幾簇懵懂的紫色雛菊,睜著無辜的眼睛,齊刷刷地看著她。伸出手,她輕輕撫摸著刻在碑上的字,就像彈撥一只舊琵琶。碑的顏色舊了,字的凹槽也淺了,曾經蒼天可鑒明月可明的兩人,早已天各一方,唯留下這并排著的兩個名字,驗證著海枯石爛的謊言。
然而,終究是愛過的,那些明亮的青春和遠大的理想,那朝朝暮暮的追隨,那十指交握苦樂與共的相守相依,都不曾在年月里缺席,如此,就算被定格在石碑上,也不枉此生了。
輕嘆一聲,她有了個決定。明年清明節前,她要找陵園管理處的人,給碑出個新,給碑上的字再描一描。她要讓過往的歲月,顯出該有的顏色和樣子。
天空響起明亮的鳥鳴,一陣云雀快速掠過,飛向遠方。墓園外圍的農田,青麥穗舉著細碎的花朵,油菜花織出鋪天蓋地的炫目金黃。那無邊的花海,密密實實地包圍著她,散發出一股股穿透歲月的溫暖醇香。
(選自《安徽作家》2023年第2期)
作者簡介

苗秀俠,中國作協會員,文學創作一級,《藝術界》副主編(主持工作)。在《中國作家》《小說選刊》《北京文學》《隨筆》《作品》《長江文藝》《芳草》等發表中短篇小說多篇,有小說和散文入選年度作品精選集、《中國文學年鑒》等。出版《遍地莊稼》《迷惘的莊稼》《農民的眼睛》《皖北大地》《大澮水》等作品。曾獲老舍散文獎,安徽省政府社科獎,北京文學獎,安徽省五個一工程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