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5-04 來源:安徽作家網 作者:安徽作家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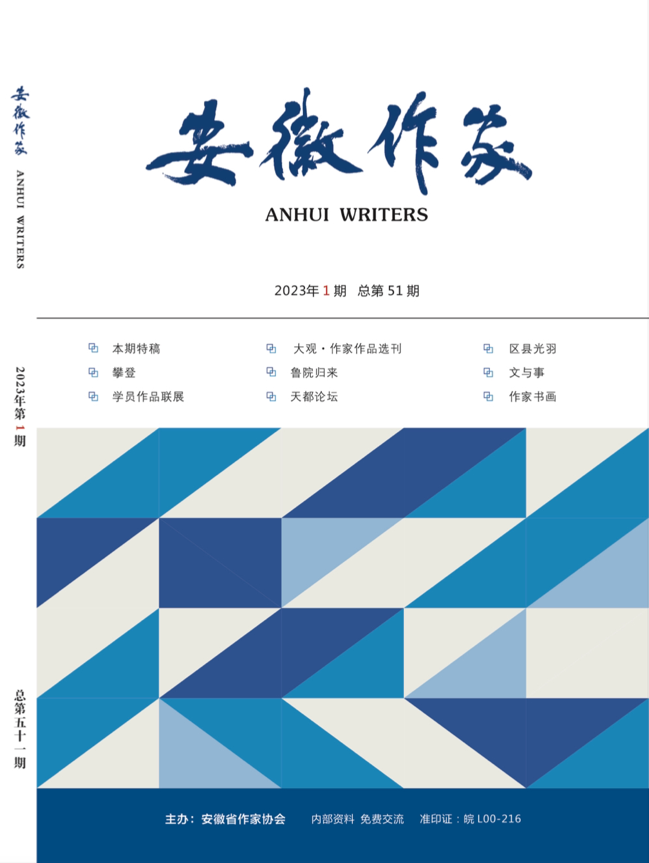
無兄弟不籃球
無文學不姐妹,無兄弟不籃球。我們中的大多數是在現代文學館的籃球場上混熟的。由于當時北京出行政策等原因,我們報到的時間也不同,分為四批(還有幾位同學最終未能成行),我算第二批。在宿舍隔離期間,除本職編務工作外,我都在做一本考古方面圖書的文學潤色事宜。也許是長久地與墓葬、遺址等打交道,我時常夢見逝去的人,經常在夢中驚醒。所以,甫一出關,我就直奔籃球場,與芍藥居的陽光親密接觸。
此時正值北京深秋,銀杏有了黃金的質地,梧桐開始給大地寫信。我穿過魯院門口的樹林,像是走進一幅印象派油畫。繞過一株雪松,先和茅盾打一個招呼;轉到了湖邊,正遇到老舍、曹禺、葉圣陶在聊天。老舍執手杖,隨意地靠在椅子上;葉圣陶著長衫,持一把折扇;曹禺西裝革履地站在背后,留出一個可供合影的位置。后來,這個位置被來自洛陽的王小朋占領,在魯四二的班級紀念冊上,他和三位大師盤踞其中,成為一道靚麗的風景。我們看過照片后有一個大膽的提議——等小朋百年之后,就按照這個造型給他做個雕塑留在這里,三位大師變成四位大師,這一組雕塑的名字就叫“淘寶老王”。小朋連連稱好,只是有兩點意見,一是自己照片中的表情略顯拘謹,二是排名有點靠后了。
但那時,小朋剛投進一個三分,表情相當自信,頗有進NBA名人堂的架勢。隨后,他想來個梅開二度,忽見一人大鵬展翅,直接沒收了籃球,將其玩弄于掌中。這名身長八尺的大漢就是內蒙古詩人梁雙全,本名浩斯寶力高,是籃球隊的隊長。由于他成熟穩重加沉默寡言,一度被當作文學館的安全保衛部部長。梁部長的搭檔是回族作家冶生福,來自青海,會唱“花兒”,他在籃下和“花兒”的歌詞一樣,“撲棱棱”“嘩啦啦”不停,人送雅稱“籃板王”。和生福形成明顯對比的是嘉興小伙蔣話,他在場上游手好閑,屬于散步式打球。
我在場邊觀察著這一群活蹦亂跳的同學,并沒有想到他們會出現在我的小文中。人群中我只認識陜西詩人李東,前幾年我們在山東東營黃河口詩會見過。那個詩會女詩人眾多,李東人帥詩好,一直在指導她們,我們一直沒有機會深入交流。李東這幾年作品屢見大刊,與他在場上屢投不中的表現截然不同。最年輕的得分后衛周于旸既能玩轉籃球,也能玩弄小說,他和李卓并稱“投手”——周于旸后來引以為豪壯的是在魯院學習期間連著投進七個三分球,我卻鄭重地告誡他:“每當你覺得想要炫耀球技的時候,你要記住,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所擁有的狗屎運。”
615宿舍
從窗子到門七步,從門到窗子七步,可惜我不會七步成詩。我只會五音不全,但在魯四二學員中,我最具流浪歌手氣質,因為我有一扇朝北的窗,可以望見星斗。待在這么有詩意的地方,一前一后的隔離生活也沒那么無聊,就是有點冷。
剛來那會兒,每天七點左右,我蜷縮在被窩里,聽到送餐車轟隆隆的聲音,知道有人來投喂了。沒想到成年之后還能過飯來張口的日子,在此特別感謝魯院師長和后勤人員對我們的悉心照料。魯院的面食是一絕,致使我學成歸來時,成功增重十斤,原來前輩們說的在魯院學習得到很大提升,指的是體重。
有人戲稱我們是魯院騰訊會議班,所以我的大部分課程也是在615上的。615既是我的宿舍,也是我的教室。
翻開615的留言冊,看到李榮茂、張二棍、童作焉等人的留言,看來這里盛產詩人。臨別之時,我也在留言冊上寫了一段話,但當時可樂喝得有點多,至于寫了什么,我全忘了。如果寫得好,就算可樂的功效,一瓶可樂詩百篇;如果寫得不好,也不代表我真實水平。
勃朗特三姐妹
梁部長在魯院的得意之作不在于詩歌,他用蒙語創作,就算寫出了《荷馬史詩》,我們一個字也不認識;也不在于他的沉浸式《鴻雁》演唱,盡管他在六樓引吭高歌的時候,魯四二的學員傾巢而出給他加油。他在魯院收了一個高徒,是籃球隊里唯一的一名女隊員——來自保定的兒童文學作家賈為。梁隊竟然教會了賈為三步投籃——奧尼爾曾說過,教女生三步籃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賈為和她的老師一樣,嗓音也好,恍如天籟,一唱起《送別》,“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剛起個頭,蔣話就淚水漣漣,猛灌自己一大杯可樂。魯院是不允許喝酒的,所以我們用可樂代替。其實可樂喝多了也會醉,蔣話可以證明。他記憶力超群,不會不記得他醉可樂后飄逸的狀態,簡直和在球場上散步的他判若兩人。
在賈為加入507茶話會之前,507已有兩位女會員,一位是劉威,湘妹子,以發言犀利而著稱,我們跟著李卓叫她威姐。茶話會大多是作品研討會,其實更準確地說,是文學批斗大會。建會巨業伊始,我和小朋、李卓定下基調,就要刀刀見血,直擊痛點,否則搞成相互吹捧大會,就沒意思了。威姐是專業編輯和成熟作家,讀得認真,評得細致,談得真誠,批得“到衛”——好幾次把作者批得躲到衛生間不敢出來。小朋勸威姐稍微收一收,批評對象老是待在衛生間,雖說到位,但也倒味,這樣文本就成批評的孤島了——小朋對氣味非常敏感,他認為小說要有煙火氣和人情味,從他的《黃梅路魚鋪簡史》就可以聞得出。威姐粉面含春威不露,說,我已經很克制了!
這也是我一直不敢拿出自己小說參與研討的原因。但小朋、于旸、生福、蔣話、李卓文正不怕威姐批,所以他們的收獲就比我大得多。有人唱白臉,就有人唱紅臉。另一位女會員常笑予就經常唱紅臉。她來自哈爾濱,出生于兒童文學世家,腿比院門口的玉蘭樹還要長。她說搞文學的人心理都很脆弱,都有一顆兒童般幼小的心靈,所以要適當鼓勵。等常笑予發言的時候,苦主就會從衛生間跑出來,重拾生活的信心。
她們生機勃發,開朗樂觀,特立獨行,簡稱勃朗特三姐妹;她們是507茶話會的女嘉賓,又稱“茶話女”。
幾十人在院里過集體生活,也不能外出,我們都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干擾。一個月過去,問題來了,除貴州作家冉小江外,男同學顯得人胖毛長,得理發了。
班主任葉老師聯系外面的造型師,讓他來給大家理發。造型師問我們有多少頭?答曰,除去女生和一個不用理發的男生,估計有十幾頭。造型師嫌人頭太少,不愿來。正當大家一籌莫展之際,唐山作家劉云芳站了出來,說她來試試。
云芳手藝不錯,關鍵還不收錢。她的宿舍不僅是教室,而且還成了理發室。我去理發的時候,她大吃一驚,說你也要理發?我說再優秀的詩人也是人,也要理發的。她說,你不是要植發嗎?我沒這技術。
穿越孤島
此時此刻,在長沙賀龍體育館附近,蔣話穿越大半個中國見到了李卓。這幾乎是魯四二畢業后的第一次聚首。
而在去年12月,李卓跟蔣話聊過一次,說魯院其實像一個孤島,我們是一群漂流到島上的人。“因為在孤島上,所以日常不被關注的事物,都可能會成為我們珍視的東西。”不知道他們是否會想起這段聊天。但我可以確定,他們今晚喝的肯定不是可樂。
魯院是孤島,507也是孤島,甚至我們每個人都是孤島。原以為,一個個孤島聚集在一起就會變成群島或新大陸,其實不然,我們在一起,只會造就更大的一座孤島。
終于,我們從一群人的孤島回到一個人的孤島。結業后,我們踏上行程,浩斯寶力高回到草原,常笑予回到冰城,小朋回到十三朝古都。有的回到郵票大小的故鄉,有的回到相愛相殺的他鄉,有的收獲了一個滿意的答案,有的領回了一大堆疑惑。我在結業典禮上說,我們都會回到一張寂寥而廣闊的書桌,重新出發,在一粒粒漢字前找到自我。
這么看來,漢字也是一粒粒孤島。當它們以不同的形態集合到一起,形成一篇文章,里面的喜怒哀樂,確實是個人的而不是群體的。
魯院歸來后,我一直在想我收獲了什么?是參加了中國文學盛典?魯迅文學獎之夜?是聽到了曹文軒、李洱等大咖的講座?是得到了李少君、徐則臣等老師的指導?這讓我想起一個故事,說是古時候,山東某地農民家的母豬生了一個白豬,農民非常驚奇,以為天降祥瑞,要獻給皇上;可他走到濟南府后就回去了。為什么呢?那是因為外面到處都是白豬。
這個農民收獲了什么?他和我一樣,是長了見識。說得洋氣一點,是開闊了視野。我的眼光,一直停留在地球上的匡沖,李卓則把視角放在大地方青田。不過,他現在已經漂流到了遙遠的努阿坦布島。周于旸走得更遠,他在云頂操縱想象的吊車,通過一塊玉米地穿越了地球孤島,抵達象人星,他的志向是“跨越整個星系,去宇宙另一端的陌生星球當一個外星人”。
如果以上真的發生,我可以選擇繼續留在孤島,就像李卓小說《努阿坦布島葬禮》中的老皮特的父親一樣,說,“你們走吧,別恨我。”請大家相信,哪怕是島上最后一個人,他也不會孤獨。當這些遠行者回望故鄉時,他還在那里喝著可樂,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
感謝這一段短暫而美妙的時光,感謝這一群招搖過海的人。他們,有的給我遞來一根杠桿,有的給我一聲棒喝,有的給我忘情水,有的給我布洛芬。有的只是拍一拍我的肩膀,讓我知道,他和我一樣完成了孤島穿越,已經足夠幸運。
(選自《安徽作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