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11-28 來源:安徽作家網 作者:安徽作家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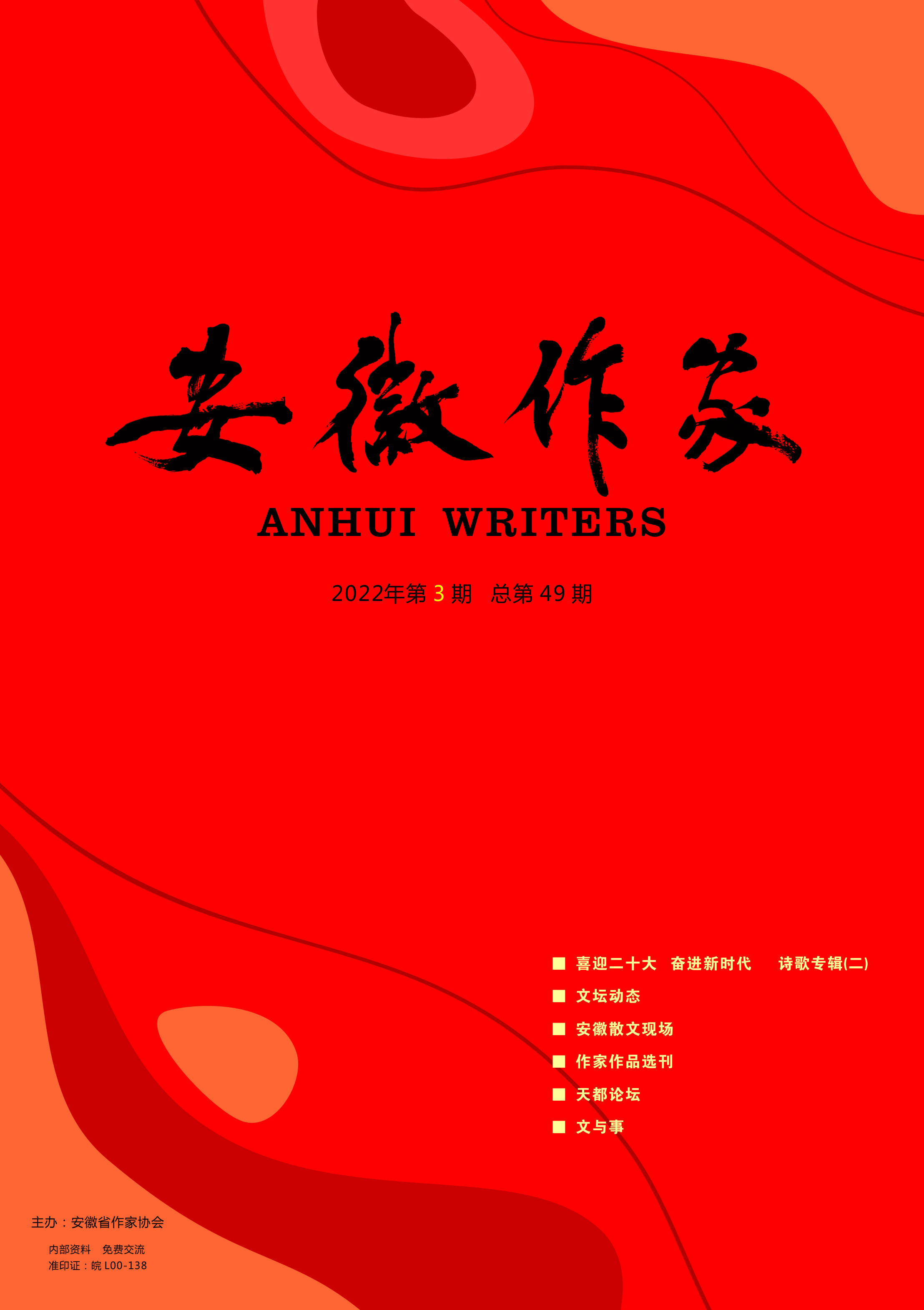
作品欣賞
散文觀:文學作品要給讀者帶去精神上的思考,并體驗到愉悅,這愉悅當然應該是美的。不能給讀者帶來思考以及美的享受的文字,不能稱之為文學作品,散文當然不能例外。
扶貧記
金國泉
我突然感到我去扶貧的村寨,那個地處泊湖邊的團山村民風少見的純樸。在這樣一個泥沙俱下、霧霾里看鮮花的時代,它悄立湖邊,既低頭也仰望,甚至遠不止于純樸,而應該是醇樸,淳厚、醇香間挾帶著質樸,一種能讓我品著甜、含著飴、嘗著香的味道,這味道似乎到現在還在我唇齒間激情地蕩漾著,一種美到心尖的感覺。
我的家鄉望江縣是國家深度貧困縣,在今年脫貧摘帽之列。也就是說幾十年來我生活、工作一直都在本土,像許多人一樣沒有真正離開過家鄉,一直沒斷過奶,靠家鄉的山水滋養著,依家鄉的丘陵山岡起伏著。對,家鄉的確到處是丘陵山岡、湖汊塘堰,有順口溜為證:“黃土岡,丈把高,大水淹來就齊腰。湖里游,溝里滾,日曬三天成火坑。”怕澇、怕旱是家鄉一塊厚厚的胎記,真的摸不得,一摸必生痛,真的經不住敲打,一敲打必傷經痛骨。
我曾在散文《泊湖記》中這樣描述過,泊湖橫跨皖鄂兩省,從安徽望江華陽鎮進入長江,應該是長江在此長期形成的一節“盲腸”。現在看來并非如此,泊湖應該是長江這根臍帶上拴著的一個孩子,由長江滋養著、灌溉著,兩千年仍然未斷。實際上,人類生存的過程就是掙斷臍帶的過程。
春節前夕縣里安排了一系列活動,扶貧隊長老胡告訴我,春節前每位幫扶人必須走訪慰問其幫扶對象戶,了解他們春節期間的生產生活,送去關懷溫暖、祝賀祝愿。收到這條消息時我在外地掛職,但那不是能例外的理由,老胡囑咐了我。實際上,涉及到扶貧的事,幾乎沒有理由例外──我感到,在深度貧困縣里,每個體制內的人都具有這樣一個身份,這樣一分責任,甚至也不僅是體制內,它@所有人所有單位,我等全部被裝進了這個籮筐中。
今天是星期天,我早早就起來了,與我的對象戶通了電話,妻子問我為什么那么高興,我回答不上來,但我知道在這方面我比我的那些對象戶還要容易滿足。因為他們平時都在外務工,一年之中幾乎不回來。連面都見不到怎么幫扶?這個責任實際讓我們這些幫扶人感到莫名的大。
僅僅打個電話是幫扶嗎?雙方經常都在這樣責問與追問。
特別是汪華中,往年要到臘月二十七、八才回到村子,而正月我們還沒正式上班他就奔回到了他的打工地。我常常與他開玩笑,你這幾乎是不給我與你見面的機會呀!
我看了一下日歷,今天是臘月二十二,他居然在家,與我通話的語氣居然不像往時那樣硬邦邦,而是露出了平時少有的綿柔感。我怎能不高興!他常年一個人生活并生存著,父母早年不在了,一個哥哥已成家立業不在一起生活。三十出頭,人相當老實,腰板相當結實,但性格也相當結實,結實到有些剛硬,可能正因為如此,至今他仍然長年在鄉村與城市之間徘徊著,找尋著,既無牽無掛,也有牽有掛。我常常想,三十出頭的小伙子,上不用養老,下不用養小,咋成了貧困戶?有一次我曾壯著膽問過他,他說他就是貧困戶,不行嗎?我沒話說了,他理直氣壯,我當然就理不直、氣不壯。與他類似的我的幫扶對象戶還有一戶,只不過年齡小一些,比我兒子還要小,原來屬五保對象,這樣的情況屬貧困戶就不用壯著膽子問了。他從小父親病重,欠下一筆債走了,母親改嫁他鄉,留下他一人。兩間破敗的瓦房在我還不認識他時就已經坍塌了,屋基上長滿了野草,夏末時,比人還高。在鄉村,特別在貧困的鄉村,沒人的地方總是會長出這樣大片大片的野草,長得讓人心慌意亂,大約是這個原因,古人干脆就叫它荒草。好在他母親改嫁的地方并不遠,他不用去管這些荒草是怎樣強行霸占他的屋基的。他曾告訴我,叔叔待他也很好,每年打工回來都在叔叔家過春節,這也讓我感到他的家仍然在。
在貧困的農村出生并長大,我對貧困當然熟悉到有自己許多不變的標準。有些標準是讓我生痛的,從內心里生出來的痛,就像我的幫扶對象,他們那深一腳淺一腳的身影,總是那么沉重,總是讓我想起羅中立的油畫《父親》,那時時鎖著的愁眉像他們的步子一樣展不開。是承載的太多還是鄉村的水泥路太窄?但鄉村實際是天開地闊的,是能跑大車小車的,每一輛都必須經過鄉村的,在鄉村掉頭在鄉村拐彎,田野里無論是冬季的麥浪,還是夏季的稻禾,都是那樣的籟籟灑灑,每每都是樸素與親和,心會曠遠,耳會清爽,眼會澄明,甚至就像眼前道路兩旁已然枯萎下去的狗尾巴草,在這個冬日的暖陽中仍能讓我感到絲絲白潔的暖流,如果我們將它拔出來,它的根必定是鮮活脆嫩的,誰都會忍不住對著它深深吸一口,那充滿生命的泥香。
記得上次來時,道路兩旁還是滿田野滿山岡的金黃,現在如釋重負了,遠遠望去只剩黑黃的稻茬,一堆一堆的草垛錯落在田埂上,有牛犢緩步,有雞鳴狗歡,有三五棵灌木青綠在薄薄的冰凌中,給人一種舒暢的感覺。老胡把車停在路邊說你一個農村長大的孩子咋那么矯情?我又回答不上來。是矯情嗎?是,也不是。這個村子雖與我老家無本質上的區別,但也有隔河隔岸的不同,“三里不同言,五里不同天”。我雖不與它朝夕相處,但來去之間,鞋幫上免不了粘上了它的泥土,手掌上免不了粘了些它青澀的草香,心自然就有了某種牽掛與期許,人與人,人與村莊……概莫能外,華中、護斌、艷伢……每一個名字都有了歲月的厚重與純凈,即便我們不牽著掛著,他們也仍然在他們自己的那個星座上24小時地奔騰,365日地打磨,唇紅齒白,笑盈盈的。
我先是到了護斌叔家,老兩口都已八十臨近,沒有兒女,他曾告訴我,早年抱養過一個女孩,又乖巧又漂亮,剛滿十八歲那年打農藥,不幸中毒夭折。每談至此,二老臉上短暫的興奮便轉為很沉的漠然,是悲苦二字無法形容的。時間讓他們白發叢生,時間對痛苦的打磨,裂痕雖除,但磨損度非常大,像磨刀石比原來低矮了許多,自此老兩口相依相靠,沒再起任何波瀾。他自己右腿早已經行動不便了,到田間地頭勞作都要靠電瓶車送他一程,妻子肺部、腰部都做過手術。村里為他倆辦了低保,領了慢性病證。就是這樣一對老夫妻,我每次到他家,他都是笑呵呵相迎,那種對生活的坦然與承接的確讓我心生敬重,敬重中有道不明的心酸。
他養了兩頭牛、三十只雞,還種了兩畝玉米,獲補貼3000元,菜園里有菜,銀行里下半年的低保補貼還沒取呢!他像數家珍,我也像聽新聞,但這新聞有鹽有油有柴火,就是一道上好的土菜。就像剛進他家門時看見他提著的籃里的那幾顆白菜,清淡可人。我注意到,他用的仍是上個世紀流行的菜籃子,而非塑料袋,這道風景在我的家鄉仍然普遍著。村民們制造的垃圾,他們自己基本能處理60%,比如廚余的東西可以喂畜禽,比如果皮、果殼直接就是有機肥,那剩下的40%除化肥、農藥,幾乎就是城里人帶過去的,或過度包裝,或尿不濕塑料瓶……
我掰著指頭算垃圾賬,他卻指著籃子里的白菜說,經過霜凍的白菜好吃,又香又脆。這些永遠被我們俯視,匍匐在大地上的白菜,我們實際需要彎下腰去才可采摘。它無論經過多少風霜雨雪,總是一臉青翠地面對,一心白潔地生長。且霜打一次,其味就香脆一分。
我家園里的菜自己吃,不下肥,不打藥。今天中午就在我家吃白菜燒肉吧!沒在我家吃過一餐飯,過年了,也該吃一餐。你放心,肉也稱回來了,雞也順了,鴨也順了,就在那──我的家鄉,過年用的東西都不叫殺,叫順,圖個吉利──他用手指著吊在那里的一大串豬肉,足足有一二十斤。我叫村里干部來陪你,我家也不是那樣臟呀!我知道老人在用激將法,他比那顆白菜還要善良與潔凈。記得有一回,我看見他家茶幾上有因農忙而沒來得及擦去的塵灰,便拿起抹布想幫著擦一擦,老人一下子激動得不行,連連說那不得了,要午雷轟頂了,他把自己壓得那么低,把我們這些所謂城里人看得比什么都貴重。
我說不是那意思,護斌叔,我從小就在地溝里爬,田溝里滾,我們家也是吃泊湖里的水,你家到我家只隔兩個湖汊,很近。說臟,我們一樣臟,說干凈,您老比我們干凈多了。主要我今天必須見一下汪華中,約好了。
那你去吧。見我如此,老人不再堅持。他告訴我華中在家,剛才去園里摘白菜回來時看見了他。華中這孩子有喜事了,你知道不?我說我不知道,什么喜事呀?他要結婚了。這真是天大的喜事,難怪今天早上講話語氣不一樣。
從護斌叔家出來,剛走上村中正路,遠遠就看見華中站在門口喊金哥。一聲金哥樸素而真誠,就像他家剛貼上去的大紅雙喜字,喜洋洋的。沒有了上次見面時胡亂穿著的邋遢,歲月圍困的滄桑此時被他一身嶄新的西服趕走了。
金哥,真的感謝你,幫我拿到了修房子的錢,你看我這房裝得怎么樣?華中說的是危房改造資金,他家符合這個條件。我說是村里鄉里幫你把資金申請到位的,我真的沒幫什么忙。趁著華中為我倒水,我注意了一下他家裝修一新的三間平房。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房子也爽著,那些家具也爽著,那曾經漏過雨水的地方,現在嚴絲合縫,只透喜氣,淚痕一樣的污跡沒有了,媳婦在灶間忙碌著,真是有女人忙碌的地方就有男人安穩的家。他說他與媳婦是去年在一個廠子打工認識的,準備正月初六辦個喜酒,到時你一定來喝一杯,要像幫我扶貧一樣幫我撐個面子。
這頓酒我一定來喝,你不請我也要來。我問他去年掙了多少錢。他笑著說反正我辦喜事不用錯錢,“耍滑頭”中張開著憨厚。他又甜甜地喊著他媳婦,我沒聽清,但我聽到了他叫媳婦把準備好的東西拿給我。
金哥,這是我倆的一點心意,你一定得收下。我一看是兩條中華煙和兩瓶酒,一下站了起來,你這是什么意思?是要打我的臉呀!他倆也激動起來,一個拉,一個拽。我說那個危房改造是你應該得的,就連鄉里村里也不用感謝,更何況我!我邊說邊掙脫邊往外跑,見我跑出了門,華中居然追了出來,我馬上嚴肅起來,華中,我告訴你,你再跟著我,我翻臉了,永遠不理你。見我一臉沒見過的認真,他愣住了。快回去,媳婦在等你燒飯,初六我來喝喜酒。
車子發動后,我看見華中仍然愣在那里,一動不動,不知是前進還是轉身,冬日的陽光下,一臉無助的茫然,憨憨的像做錯了事的孩子,他手中裝著中華煙的紅方便袋,一晃一閃,有暖意,有無邪的深情。
在回來的路上,扶貧隊長老胡說,兩條中華煙和兩瓶酒,可能要他們半年的積攢呀!這些村民仍然奉行的是滴水之恩涌泉相報。我知道我甚至沒給他滴水之恩,是他們自己一步一步艱難地前行,一鍬土一鍬土去培植,一鋤頭一鋤頭去挖掘,他們的溫情善良就如村莊旁的溪流慢慢滲透進了這一鍬一鍬挖著的貧瘠的土地里,這些丘陵山岡因這良善溫厚的灌溉而麥子抽穗,稻花飄香。
(選自《安徽作家》,2022年第三期)
作者簡介

金國泉,男,安徽望江縣屠家田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安慶市評論家協會副主席。詩歌、散文、文藝理論散見于《詩刊》《文藝報》《星星》《天津文學》《散文》《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山東文學》《詩歌月刊》《青海湖》等報刊。曾獲吳伯簫散文獎及安慶市文藝獎一等獎。著有詩集《記憶:撒落的麥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個漏洞》《金國泉詩選》及散文集《大地蒼茫》等多部。
作品欣賞
散文觀:當我翻開一本散文集,就是想進入作者的內心場域,通過閱讀感受作者藉由語言、思想、性情,傳達的生命觀。我面對的不止是一本書,而是一個有靈魂且有溫度的人。閱讀,就是和這個人隔著時空相見、交談。希望自己的書寫也有這樣的品質。
在河邊相遇
項麗敏
蟬歌人間
立秋后的第二天,臺風降臨。
臺風攜來風和暴雨,一場交戰之后,盛夏在滿地落葉里離開季節的門檻。
這是我生命中第四十七個夏天。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長是短。相比只能擁有一個夏天的蟬,這當然是長的,而相比山中能活上幾百年的樹,這又是短的。
我的祖母和外婆在人間活了五十九個夏天。小時候覺得這個數字太短了,讓我隱隱恐懼,仿佛一道陰影橫亙在那里。現在看來,其實也不算短。以她們早已破敗的肉身和沉船樣的生活衡量,五十九已是極限的數字,無法再承載更多了。
我的母親也曾經恐懼過,在五十九歲之前。她焦慮,沮喪,脆弱不堪,覺得自己很難突破這個數字。而這之后,母親漸漸放松了對時間的警惕。不知道母親是否有這樣的感覺:在跨過了五十九這道魔咒般的門檻后,每一天的到來都是余生,是上天加贈給生命的假期。
如果母親能有這樣的感覺,她就會比較容易獲得幸福。至于我,很早就有這樣的感覺和認知了,早到已不能準確說出究竟是哪一年。
三十歲,我在日記上寫下加繆的一句話,“在隆冬,我終于知道,在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
隆冬就是死亡的威脅,而夏天就是復活的力量。
人的一生應當不止一次出生,也不止一次死亡。第一次的死亡來得越早,再生就會來的早一點。這再生的生命將屬于你自己,你將像蟬的若蟲一樣,在蛻變后,擁有與之前完全不同的生命。
不是每一種死亡都能順利的擺脫舊軀殼,復活,再生。再生需要能量,也需要運氣。
曾在記錄片中看到蟬蛹蛻變的過程——若蟲從泥土下爬出,緩慢地爬上一棵樹,抓緊樹皮,背部的殼漸漸裂開一道縫隙,腦袋從縫隙中掙出,接著是三對細足。幼蟬的上半身懸空著,奮力將軀體向后仰、仰,仰成倒掛的角度,讓尾部從殼中掙脫出來。
一些蟬的若蟲羽化成功了,掙脫了殼的束縛,吸收陽光的熱能,讓翅膀迅速生長,變得堅實有力,可以帶它飛翔。而有些若蟲,剛從泥土下爬出就被螞蟻圍攻,成為蟻群的食物。
看到螞群排著隊,涌向蟬的若蟲,我的身體也有一種被咬噬的痛感。我無法憎恨螞蟻,這是自然法則的安排。我只是為若蟲悲哀,在泥土下幽閉了那么久,從沒見過陽光,沒有發出過聲音,就永遠失去了原本可以擁有的、能夠熱烈鳴唱的夏季。
整理《山中歲時》的書稿時,發現自己多次書寫到蟬。詩歌里也是——偶爾翻開新出版的詩集,隱居其間的蟬歌就溢出來。
為什么會這么頻繁的寫到蟬,難道在我的生活里就沒有別的聲音?只有蟬歌,這單一又不知疲倦的聲音貫穿始終?
是我的聽覺對蟬歌比較敏感吧,總是能在漂浮空氣的聲音里捕捉到。當你敏感于什么的時候,你就能在紛紜的事物中感知到它,看見和聽見它。而當你失去這種敏感時,即便身在其間也惘然無知。
對蟬歌比較敏感的原因在于,我一直就居住在大自然的事物之中。蟬是我無法忽視的近鄰,看不見它,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在我已經歷的四十多個夏天,多數時候,只有蟬唱陪伴著我,從清晨到黃昏,用它銀亮、寬闊又寂靜的歌聲充滿著我。
夏天離開了,但夏天并沒有走遠。它還會回來,在臺風退下之后。
沒有一種離別是那么輕易的,斬釘截鐵的。每一種離別都要經歷再三的猶豫,牽扯和徘徊。
而秋天的到來也不是在夏天離去之后。秋天早就來了。在夏天的宴席最熱烈時,秋天就裝扮成一叢百日菊,一只紅蜻蜓,一樹馬褂木的黃葉子,還有蟋蟀彈奏的小夜曲,悄然到來。
秋天潛伏在盛夏眾多的事物之中,也潛伏在一個看起來很強壯的人的身體里,在他不在意的時候,襲擊他,讓他在一夜之間疼痛,衰老。
秋天是盛夏的密探,也是盛夏的叛徒。但秋天也眷戀著夏天,模仿著夏天。
蟬的吟唱就是秋天眷戀夏天的證據。無處不在的蟬歌,并沒有因為夏天的離去而消失,它的韻律更為婉轉、豐富、從容,從單聲部變成多聲部,反復循環的安魂曲。
一個人走在林蔭小道,聽著蟬歌,覺得這就是永恒了。
雖然有點孤寂,我還是喜歡這樣的夏天——除了蟬歌,聽不見別的聲音,也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然而我似乎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本領,能在蟬歌里聽到萬物之聲。
這萬物也包括我。
有蟬歌就夠了,不需要更多了。如果余生還有很多個夏天,我希望仍舊這樣度過,仿佛永遠過不完暑假的學生。我會繼續將聽見的蟬歌錄下來,以散文和詩去保留,以人間的文字去收藏。
在河邊相遇
有好多天沒聽到蟬鳴了。進入九月后接連落雨,蟲聲稀疏起來,蟬鳴也像被一只手抽走,消失于四野。
蟬鳴就是漫長夏日的煙花,當煙花燃盡時,安靜下來的世界似乎也失去了一種光芒。
耗盡燃料的蟬從樹枝紛紛落下。不過仍有一種蟬——剛羽化不久的寒蟬留在樹上,等待著天氣變晴。天一晴,屬于它們的世界就會在長吟短唱里重新返回。
我也在等待天晴。這幾天一直惦記著那群斑嘴鴨,想再看到它們鳧游河面的樣子,用鏡頭捕捉下它們悠閑的姿態。
是八月末的早晨與斑嘴鴨不期而遇的,地點在浦溪大橋,這里河域寬闊,有深水區,也有芳草淺灘,河面云影流動,兩岸少有行人,是涉禽和游禽鐘愛的棲息地。
最常見的是白鷺,每次來都能見到,當我站定,舉起相機,其中一只就會拍翅飛起,另幾只緊隨其后,向上游飛去。
舉起的相機總是落空,倒并不覺得遺憾,只要能看見白鷺在這里就好。這條河流原本就是它們的家園,我的到來是一種入侵,是對它們寧靜生活的打擾。
來的次數多了,發現了一個秘訣——只要我遠遠地站著,不舉起相機,就不會驚擾白鷺,它們自顧自地在淺水區捕食,在河邊慢步、靜立,神態安閑,有著天然的隱士氣度。
白鷺捕食的時候很有意思,一改平常慢悠悠的樣子,變得活潑,甚至有些滑稽,翅膀展開,在水里跳躍,拍打得水花四濺,看起來像一種歡快的田間舞。任何動物,包括人,在面對美食的時候,都會露出本真又可愛的一面吧。
在這里也見到過池鷺、黑水雞、褐河烏、小鸊鷉。小鸊鷉善于潛水,看到有人過來就一個猛子扎下去,半分鐘后,才見它重新浮出水面。
入秋后的黃昏,在這里會聽到一種潛鳥的叫聲——很可能就是小??的鳴叫,“嚯嚯嚯……嚯嚯嚯……”似一位少年歌者在重復練習顫音的發聲法。這聲音拉長了黃昏的時光,靜立河邊,看暮色潛入河面如同溫柔的鄉愁。
遇見斑嘴鴨完全是意外,或者說是上天賜予的驚喜。當它們——大概有七八只的樣子,靜靜地泊于河面,我以為是附近村落游來的家鴨。
以前在河里看見的家鴨大多是白色,像這樣麻褐色的也有,似乎又有些不同,羽色沒有這么鮮亮。我打開相機,從長焦鏡頭里觀看它們——墨色的鼻子,鼻尖嫩黃,翅膀上有一抹綠,翅尖又是白色的……忽然,安靜的河面晃動起來,其中一只拍動翅膀,凌空而起,身邊的伙伴也迅速跟隨,拍翅離開河面,向高處飛去。
懊悔剛才那么好的時機沒有把握,沒來得及拍攝下它們飛離河面那富有動感的瞬間。
當斑嘴鴨從河面飛起的一刻,我腦子里浮出《遷徙的鳥》中主題曲的旋律。雅克·貝漢拍攝于本世紀初的這部紀錄片我看過無數遍,主題曲爛熟于心,每個鏡頭也都深深地刻在腦子里。真幸運啊,能在自己生活的河邊見到紀錄片中的場景,仿佛實現了一個久遠又念念不忘的夢。
這群斑嘴鴨很可能是浦溪河的過客,遷徙時路過這里,做短暫的休憩。
不知道它們會在這里停留多久,也不知道它們要去往哪里。秋天才剛開始,它們也是剛剛踏上遷徙的路途吧。
第二天,冒著細雨再次走到浦溪大橋,懷著忐忑的希望,把目光投向河面——河面空空,連之前常見的白鷺也不見了。
也許是下雨的緣故,下雨天,野外的小動物、小昆蟲都會躲起來,就連隨處可見的麻雀也沒有影子了。誰會那么傻呀,下雨天又冷又濕,誰還在外面游蕩。
下雨天也不是上路的日子,那些斑嘴鴨應該還沒有離開這里。
雨斷斷續續下了一周,總算是停了。多日不見的陽光撕開云層,從裂隙里涌下,世界又恢復了生氣。
拿起相機,起身離開居所。我要走進光里,走到田間與河邊,走到那亮晃晃的地方去,讓照著稻穗的陽光也照著我,讓平凡與奇跡的野花鋪滿我生命的河流。
河流帶來世界
連著幾天沒在浦溪河看見斑嘴鴨就會不安,擔心它們被捕獵。這種擔心使我對放網捕魚的人警惕起來,眼睛盯著他,將手里的相機對準他,似乎這樣就能把他唬走。
捕魚人對我的目光渾不在意,穿著連身防水服,提著網,在河里跨步走著,把河水踩得嘩嘩響,嘴里還大聲唱著歌。置身河流讓捕魚人忘記自己的年齡,肢體也變得靈活起來。快樂是有感染性的,尤其是孩子氣的快樂,如果不是擔心斑嘴鴨,捕魚人這么快樂的樣子應該也會感染到我。但是此刻,我對他的旁若無人很氣惱,覺得他分明就是在挑釁。
河水已經齊腰深了,暮色里的捕魚人低頭弓背,身影酷似水怪。他通常是在天黑前放網,天亮時收網。誰知道那網里除了魚還有些什么。或許捕魚只是個幌子吧。
這疑竇讓心里涌進一團團云翳,沒有辦法消除,就只有拉長相機鏡頭,在河面搜索,希望能看見斑嘴鴨的一家。
我沒有看見斑嘴鴨,倒是看到另一種涉禽——黑水雞。
對黑水雞我并不陌生,以前住在太平湖邊就看到過它們,池塘里貼著水面追逐,翻身撲騰,很激烈的樣子,不知道是打斗還是在熱戀。春天在秧田里也看到過,從碧青的秧田里鉆出,田埂上叫兩聲,東張西望,很快又鉆進秧田。黑水雞周身羽毛青黑,只在兩肋露出一線白,醒目的是額甲和嘴喙,鮮紅欲滴,喙尖又是明黃色,像戴著一種特制的口罩。黑水雞的腳很長,一看就知道它善于在沼地行走。當它進入水中浮游時,長腳就不見了,尾部上翹,頸部呈S型,完全是游禽的模樣。
黑水雞的體型比斑嘴鴨小一半,多數時候隱身在草汀里,如果不是拿相機當望遠鏡在河面搜索,很難看見它們。
是在一道河壩上游看見黑水雞的,那里水域寬闊,水流平緩,幾叢蒲葦草如綠色小洲錯落河間。兩只黑水雞——應該是一對夫婦,正在營巢,游向一叢蒲葦,用尖長的嘴喙將葦葉扯斷,銜著,再游回屬于自己的營地——相距不遠的另一叢蒲葦。
黑水雞銜來的葦葉已經枯黃,這樣不用費多大力氣就能扯斷。水面漂來的浮草當然也不能錯過,趕緊銜起,送回營地。整個早晨,兩口子就這么來回穿梭地運送著草葉,將蒲葦叢中間的巢高高壘起,河水淹不上來,它們就可以安然地在巢里生蛋孵蛋了。
將鏡頭對準那些蒲葦叢,仔細看,發現每一叢蒲葦中間都有壘起的草巢,吊腳樓一樣。這個發現讓我心里一陣歡喜,仿佛無意間窺見了了不起的秘密。
蒲葦叢間三三兩兩游著十幾只雛鳥,其中一只見我把相機鏡頭對準它,咚地一下,潛入水下,水面隨之蕩開漣漪。雛鳥的警覺會相互傳遞,另幾只也跟著紛紛潛入水下,很快又從另一邊浮出來,見我還在,又潛下去,又浮出,像一群調皮的孩子玩躲貓貓的游戲。
這些雛鳥就是黑水雞的孩子。黑水雞是天生的潛水員,出殼后就能下水潛泳,這也是它們自我保護的本能,用來躲避從天空俯沖下來的猛禽利爪。
對黑水雞秘密生活的發現,使我那被云翳籠罩的心又明亮起來。
早晨的時間過得很快,河面已有日光的倒影,該去上班了,收起相機準備離開時,空中傳來熟悉的鳴叫,抬頭看,一群大雁正在河流上空盤旋,站定,等它們落下,相繼落入河中,才明白過來——它們正是我尋找數日的斑嘴鴨。
斑嘴鴨的數量沒有像我擔心的那樣變少,而是更多了(有二十多只)。不知道之前看見的那一家子是否在其中。我愿意相信它們就在這支壯大起來的隊伍里,等待著更多的伙伴從四面飛來,集結,等待著秋天最后一聲號角吹響,沿著祖先遷徙的路線,向著更溫暖的地方啟程。
端起相機,對著河里的斑嘴鴨按下快門。在離斑嘴鴨不遠的地方,捕魚人穿著連身防水裝,提著濕漉漉的漁網,正從河里走上岸。不知道他是否有收獲——應該是有的,就算沒有收獲到魚,也收獲了快樂,或許他每日最快樂的時光,就是這一早一晚下河放網的時光吧。
居住的地方有一條河流是多么奢侈的事,如果這條河寬闊又清澈,那么一生守著這條河也不會覺得單調匱乏。河流會帶來整個世界的訊息,季風流動,云起云散,還有“飛鳥相與還”的晨昏,每一天的遇見都不可預期,每一個平凡的瞬間都隱藏著奇跡,如同生命本身,不能復制,不可重來。
(選自《安徽作家》,2022年第三期)
作者簡介

項麗敏,中國作協會員。居于安徽黃山,自然寫作者,已出版《閑坐觀花落》《山中歲時》《浦溪河的一年》等十余部散文集,多次獲安徽省政府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