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shí)間:2020-10-09 來(lái)源:《湖北社會(huì)科學(xué)》 作者:陳先發(fā)
作者簡(jiǎn)介:
陳先發(fā)(1967—),男,安徽省文聯(lián)主席,新華社安徽分社總編輯。
高健(1990—),女,揚(yáng)州大學(xué)文學(xué)院講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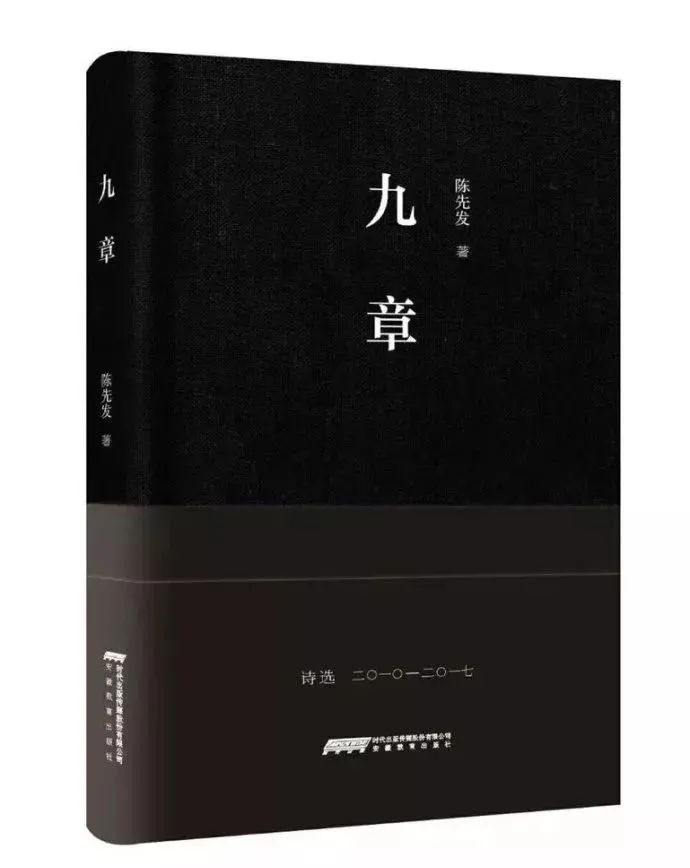
《九章》,陳先發(fā)著
高健:祝賀您的詩(shī)集《九章》榮獲第七屆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我注意到在授獎(jiǎng)詞中,特意提到了《九章》的結(jié)構(gòu)。在詩(shī)集《九章》中,您集中使用了以9首單詩(shī)為一組詩(shī)歌的獨(dú)特體例,這一體例可以說(shuō)是您在長(zhǎng)期的詩(shī)學(xué)創(chuàng)作和思索之后的自覺(jué)選擇,我們想知道您為什么決定用“九章”這樣的體例進(jìn)行創(chuàng)作?
陳先發(fā):在寫(xiě)作上,我一直要求自己保持對(duì)形式感、結(jié)構(gòu)意識(shí)方面的警覺(jué)。這跟漢字、漢語(yǔ)言的某種特質(zhì)有關(guān)。漢字在形體、音韻、多義性等方面的微妙應(yīng)用,對(duì)其在一首詩(shī)中的表現(xiàn)力有不可估量的影響。九章這種個(gè)人體例,應(yīng)該說(shuō)是這種自我要求的產(chǎn)物。最初的狀態(tài),其實(shí)是無(wú)心的。2010年前后,我寫(xiě)了《箜篌頌》、《垮掉頌》等一批詩(shī)題中含有“頌”字的短詩(shī),詩(shī)的內(nèi)在氣息相近,審美指向和語(yǔ)言質(zhì)地上有共性,當(dāng)時(shí)我想,何妨為這組詩(shī)來(lái)個(gè)二次命名呢?數(shù)一數(shù),正巧九首,未經(jīng)深思就直接冠名為“頌九章”了。后來(lái)在游歷中,覺(jué)得許多地方歷史的、現(xiàn)象的、社會(huì)的豐富性,不是單一維度的一首詩(shī)可以盡括,就著意以九章體去寫(xiě)它。比如到安徽宣城,因?yàn)橛欣畎自鴮?xiě)過(guò)的敬亭山、有謝眺遺跡、有大量保存完善的明清古村落等眾多的資源可以挖掘,就寫(xiě)了“敬亭假托兼懷謝眺九章”。在持續(xù)的寫(xiě)作中,九章作為個(gè)人體例的詩(shī)學(xué)特征不斷得以強(qiáng)化,我也開(kāi)始在整體建構(gòu)上想得更多一些,以期達(dá)到我所謂的“九首詩(shī)作為一個(gè)共同呼吸的整體,同根而活、各自搖曳”的審美效果。表面上看,九章是一種自我設(shè)限,其實(shí)我一直覺(jué)得,個(gè)人寫(xiě)作應(yīng)在一種嚴(yán)厲的自體約束中達(dá)到心靈的自由,就像在四壁封閉的斗室中去實(shí)現(xiàn)一顆心的無(wú)限漫游一樣,以此完成對(duì)自我的深刻塑造。幾年來(lái),先后寫(xiě)了近三十組九章,在許多讀者那里,這也漸漸成了某種識(shí)別的個(gè)性符號(hào)。這種體例的自覺(jué)性,就是在這持續(xù)的寫(xiě)作實(shí)踐中一點(diǎn)點(diǎn)深化的。
高健:通過(guò)閱讀,不難發(fā)現(xiàn),每組“九章”的內(nèi)部排序并不是遵循創(chuàng)作時(shí)間的簡(jiǎn)單處理,目前的排列順序很顯然是您有意安排的結(jié)果,您能具體談?wù)勀陌才乓罁?jù)嗎?這一安排順序是否不可更改,它對(duì)于詩(shī)歌的理解有影響嗎?
陳先發(fā):每組九章的內(nèi)部,次一級(jí)章節(jié)的順序當(dāng)然是有意安置的。正如砌墻一樣,不同形態(tài)的磚,該在什么位置上,必須服從整體受力的需要。一首詩(shī)的內(nèi)部空間建設(shè),要考慮的元素很多,情緒的、情感的、思想的、想象力的,等等。語(yǔ)言的光和影的部分,時(shí)而要交織,時(shí)而也要分離——當(dāng)然閱讀者有權(quán)力將這九節(jié)打亂了重新排列,那它在審美上體現(xiàn)的就不再是我的意志。詩(shī)和其他形態(tài)的藝術(shù),妙處或許正在于此:即每個(gè)人在一首詩(shī)的語(yǔ)境中,有他自己體驗(yàn)的各自斷面和不一樣的觸發(fā)點(diǎn)。這些斷面如此不同,也正如每口池塘都能映出自己的月亮一樣。而對(duì)作者來(lái)說(shuō),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九章在整體上既是一首詩(shī),也是獨(dú)立的九首詩(shī),將二者貫通的,是說(shuō)上去有點(diǎn)玄妙、時(shí)而難以向讀者有效傳遞的“氣息”二字。《文心雕龍》中說(shuō),“文者,氣也”,氣息的流轉(zhuǎn)把這九節(jié)連接起來(lái)。有的連接是明顯的,有的則是潛在的。我覺(jué)得閱讀能感受到這一點(diǎn)。而影響這九個(gè)章節(jié)排列的,也有很多臨時(shí)性的因素,寫(xiě)作時(shí)的心境和情緒的起伏等等。從詩(shī)藝的角度來(lái)看,每組九章都較長(zhǎng),每個(gè)章節(jié)要按時(shí)疏時(shí)密、時(shí)急時(shí)緩的力量布局去安排,“重的東西”會(huì)放在較后的位置。這順序本身,就是一種審美力。這順序也是寫(xiě)作本身,而不是外在的東西。
高健:每位詩(shī)人都希望自己的詩(shī)歌具有獨(dú)特性,具有獨(dú)樹(shù)一幟的意義,您也提出了“寫(xiě)作即是區(qū)分”的創(chuàng)作觀念,對(duì)于當(dāng)代詩(shī)人來(lái)說(shuō),“影響的焦慮”更是無(wú)處不在,既要面對(duì)同時(shí)代的詩(shī)人,也要面對(duì)古今中外頗為豐富和厚重的詩(shī)歌傳統(tǒng),您認(rèn)為詩(shī)人在創(chuàng)作中如何才能賦予自己的詩(shī)歌以獨(dú)特的意義呢?
陳先發(fā):寫(xiě)作即是區(qū)分,是將自己與無(wú)限的他者隔離開(kāi)來(lái)的力量。寫(xiě)作者也只有有效地完成了這種區(qū)分,他的形象才能明晰起來(lái)。如何去完成呢?我覺(jué)得最根本的一條,是始終保持對(duì)個(gè)人生存體驗(yàn)的忠實(shí)。每個(gè)人的生存及其體驗(yàn)都是唯一性的,也都貯存著極大的豐富性,對(duì)它保持忠實(shí),既是一種立場(chǎng),也是一種基本的方法。當(dāng)代的寫(xiě)作者有時(shí)很煩惱,因?yàn)樗鎸?duì)著龐雜的文學(xué)史和數(shù)不清的流派,面對(duì)時(shí)代或語(yǔ)言的命題要破解,你所做的努力,可能早有別人做過(guò)了,正如當(dāng)年李白欲詠黃鶴樓時(shí)的苦惱一樣:“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shī)在上頭”。如何祛除這種影響的焦慮呢?其實(shí)唯有一條道,就是忘掉文學(xué)史、忘掉什么古典什么后現(xiàn)代這些僵硬的概念、忘掉亂花繚眼的各類流派而一心精研自我的存在。一己之生存既是卑微的,也是博大而滾燙的。一己之中,不可能有時(shí)代全部的現(xiàn)實(shí),但卻存有時(shí)代全部的真實(shí)。深入一己,把傳統(tǒng)當(dāng)作自己的一個(gè)資源庫(kù),才不會(huì)被所謂傳統(tǒng)壓垮。當(dāng)然如何在寫(xiě)作實(shí)踐中有力地去表現(xiàn)出一己之豐富之獨(dú)特,那要靠永不止息地寫(xiě)作實(shí)踐。寫(xiě)作是一種持續(xù)的行動(dòng),靈感與智慧會(huì)在不斷加壓的實(shí)踐過(guò)程中到來(lái)——沒(méi)有確定的時(shí)辰、沒(méi)有確定的路徑——那種“妙手偶得”的現(xiàn)象,如果不是在持續(xù)而緊張的語(yǔ)言實(shí)踐的間隙中到來(lái),那么它就是一種虛妄的期待,或說(shuō)是一種投機(jī)意識(shí)。我以前的寫(xiě)作是懶散而隨機(jī)的,到了這個(gè)年紀(jì),我會(huì)趨向更規(guī)律而持續(xù)的行動(dòng)。但有時(shí)候會(huì)覺(jué)得離內(nèi)心的暗許遙遠(yuǎn)得很,現(xiàn)在更需要的是,持續(xù)行動(dòng),不問(wèn)收成,不設(shè)目標(biāo)。個(gè)體意義的人,需要誠(chéng)實(shí)面對(duì)世界之浩瀚、一己之微茫,在此基礎(chǔ)上自會(huì)形成對(duì)世界的洞見(jiàn)。一個(gè)詩(shī)人不是通儒大哲,無(wú)須以所謂精神的厚度來(lái)面對(duì)世界——當(dāng)詩(shī)人看見(jiàn)并忠實(shí)、精準(zhǔn)地書(shū)寫(xiě)一己的弱小時(shí),這弱小也是通神的,是一種無(wú)限延續(xù)之力,就像在被無(wú)窮地踐踏中再生的野草,當(dāng)它被出神地表達(dá),它就是生命的強(qiáng)大與厚度本身。這是詩(shī)性的厚度與格局,與俗世的強(qiáng)弱不是同一維度的東西。當(dāng)然,所有的詩(shī)性書(shū)寫(xiě),有強(qiáng)大的共同基礎(chǔ),我在早年一首小詩(shī)《北風(fēng)起》中有這么兩句:“谷物運(yùn)往遠(yuǎn)方,養(yǎng)活一些人;谷物中的戰(zhàn)栗,養(yǎng)活另一些人”,詩(shī)人,就是被戰(zhàn)栗、顫栗養(yǎng)活著的同一類人。
高健:中國(guó)自古就有“詩(shī)言志”、“詩(shī)緣情”的說(shuō)法。新時(shí)期朦朧詩(shī)之后有很多詩(shī)人開(kāi)始嘗試一種“以詩(shī)歌為詩(shī)歌”也被稱為“元詩(shī)結(jié)構(gòu)”的創(chuàng)作方式,您對(duì)這一詩(shī)歌思維方式有什么看法?
陳先發(fā):我從不為任何寫(xiě)作的教條所累,無(wú)論它是眾人仰面的,還是眾口唾之的,如果它限制了我、固化了我,那么它們就是同一種東西。比如你講的“元詩(shī)”,或者當(dāng)年布勒東倡導(dǎo)的所謂“純?cè)姟备拍睿挠白釉谖疑砩峡隙ㄓ校词菍?duì)語(yǔ)言本身的、對(duì)寫(xiě)作自由的一種極端性要求,我或多或少地也有這種寫(xiě)作沖動(dòng),但我覺(jué)得我從未被它所統(tǒng)攝。我也從不反感走在那條路上的寫(xiě)作者。當(dāng)代漢詩(shī)一個(gè)良性的局面,就是形成了審美方向上充足的多樣性,只有多樣性的文學(xué)生態(tài),才會(huì)蓬勃淵深。從根本上講,我覺(jué)得寫(xiě)作的愉悅在于形成真正的“私人語(yǔ)境”。區(qū)分一種好的寫(xiě)作與壞的寫(xiě)作,并不在于你要走漢詩(shī)傳統(tǒng)中一以貫之的文以載道,還是要走維特根斯坦所謂的語(yǔ)言游戲之途——世上的路其實(shí)皆無(wú)本質(zhì)的新意可言——而在于你在此路上能否達(dá)成真正的“私人語(yǔ)境”。克制住復(fù)制的沖動(dòng),去創(chuàng)造,才可觸碰到那愉悅的本質(zhì):真正個(gè)性化的語(yǔ)言風(fēng)格和真正的思之洞見(jiàn)的形成。
高健:不知道我的這個(gè)觀察是否正確,從您的詩(shī)論包括詩(shī)歌中,能夠很明顯地感覺(jué)到您對(duì)于詩(shī)歌語(yǔ)言的重視,您似乎一直在追求和鍛造獨(dú)屬于您自己的“詞語(yǔ)”,您能具體談?wù)勀脑?shī)學(xué)語(yǔ)言觀嗎?
陳先發(fā):寫(xiě)作的本質(zhì)要求,當(dāng)然是去觸碰世道人心、去洞悉人的生命本身,這個(gè)過(guò)程,既是在喚醒自己,也是在觸及無(wú)窮的他者之心。語(yǔ)言既是寫(xiě)作的工具,也是寫(xiě)作要?jiǎng)?chuàng)新的對(duì)象之一。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日常語(yǔ)言,許多美好的表達(dá)、許多習(xí)慣用語(yǔ),大量來(lái)源于詩(shī)歌。這個(gè)例子不勝枚舉。詩(shī)歌的語(yǔ)言學(xué)成果,是整個(gè)種族、整個(gè)文明史最重要的積累之一。一個(gè)好詩(shī)人的語(yǔ)言觀,事實(shí)上包括的遠(yuǎn)不止他如何使用文字、如何處理修辭,更包含他對(duì)世界的根本認(rèn)知。我更傾向于一種直接、樸素、但有況味、余響不絕的語(yǔ)言風(fēng)格。好的詩(shī)人筆下,語(yǔ)言的彈性很大,詩(shī)句中有迂回和開(kāi)闊的空間,它是多解的、多義的。如果一首詩(shī)的語(yǔ)言,被某種固定而明晰的意義固定住了,就意味著我們的心在此處有了僵硬的邊界。
高健:從目前的讀者反饋來(lái)說(shuō),包括很多專業(yè)的讀者,在嘗試解讀您的詩(shī)歌時(shí)都難免遭遇挫敗,您怎么看待詩(shī)歌寫(xiě)作與詩(shī)歌接受的問(wèn)題,包括詩(shī)歌誤讀的問(wèn)題?在未來(lái)的創(chuàng)作中是否會(huì)將詩(shī)歌與大眾接受納入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
陳先發(fā):什么樣的詩(shī)算是好詩(shī)?這句話的含義本質(zhì)上是晦暗不明的。它的一半被隱藏了起來(lái),其實(shí)是:它面臨著怎么樣的閱讀?大概我們都會(huì)有一致的體會(huì),過(guò)去的學(xué)校教育,要求學(xué)生們?nèi)デ蠼狻皹?biāo)準(zhǔn)答案”、“中心思想”,久而久之,給真正的閱讀造成了莫大的障礙。一首詩(shī),一個(gè)曲子,一幅抽象畫(huà),如果你去求它的標(biāo)準(zhǔn)答案,這種閱讀就是一種沒(méi)有靈性的、僵死的閱讀。一首好詩(shī),它要?jiǎng)?chuàng)造的,正是可以指向無(wú)盡的答案、更豐富的闡釋空間,不能用“懂或不懂”去界定它。當(dāng)代詩(shī)歌的閱讀接受有限,病根大致在此。
我曾寫(xiě)了這么一段話:“詩(shī)是從觀看到達(dá)凝視。好詩(shī)中往往都包含一種長(zhǎng)久的凝視。觀看中并沒(méi)有與這個(gè)世界本質(zhì)意義的相遇。只有凝視在將自己交出、又從對(duì)象物的掘取中完成了這種相遇。凝視,須將分散甚至是渙散狀態(tài)的身心功能聚攏于一點(diǎn),與其說(shuō)是一種方法,不如說(shuō)是一種能力。凝視是艱難的,也是神秘的。觀看是散文的,凝視才是詩(shī)的。那些聲稱讀不懂當(dāng)代詩(shī)的人或許應(yīng)該明白,至少有過(guò)一次凝視體驗(yàn)的人,才有可能是詩(shī)的讀者”。許多讀者的閱讀,還停滯在“觀看”的階段,沒(méi)有進(jìn)入“凝視”的狀態(tài)。當(dāng)然我這不是在苛責(zé)閱讀,我是在等待,等待整個(gè)社會(huì)平均審美能力的提升,為詩(shī)歌閱讀創(chuàng)造新的空間。
一首詩(shī)、一首樂(lè)曲的豐富性,正是由創(chuàng)作和閱讀兩者在交互中共同創(chuàng)造。使一首詩(shī)內(nèi)在的東西增加的,是閱讀的介入。哪怕是誤讀,只要你用一顆心去感受,藝術(shù)就會(huì)產(chǎn)生效果,所以我曾說(shuō)一首好詩(shī)有無(wú)數(shù)的入口,講的就是這個(gè)道理。一個(gè)讀者,就是一個(gè)新的入口。任何一首詩(shī)都是一個(gè)敞開(kāi)的容器,它誘使讀者進(jìn)入并不自覺(jué)地在其中創(chuàng)造出另一首詩(shī)。所以一首詩(shī)并不存在本來(lái)面目,也不存在完成狀態(tài)。用這種方式去理解詩(shī)歌,詩(shī)歌就會(huì)去激活你的內(nèi)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