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11-21 來源:文藝報 作者:林培源 陳潤庭

林培源,1987年生,青年作家,廣東省汕頭澄海人,現為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美國杜克大學訪問學者。曾獲得兩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以及第四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小說佳作獎等。小說作品發表于《花城》《山花》《大家》《作品》《青年文學》《小說界》《江南》《長江文藝》等文學期刊,已出版長篇小說《以父之名》、小說集《鉆石與灰燼》等,2019年出版小說集《神童與錄音機》。
陳潤庭:在當下,文學越來越面臨來自各方面的擠壓和沖擊。一方面是網絡文學已經成為大眾文字閱讀的主要內容與方式;另一方面,嚴肅文學有淪為邊緣的“圈子游戲”的危險,大家自說自話,自我滿足。誠然,上世紀80年代建立起來的文學期刊之間松散的“等級制度”還在暫時發揮作用。作為今天的寫作者,依舊選擇在紙質文學期刊上發表作品的意義是什么,已經成為了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林培源:在文學生產體制中,文學期刊是不可繞過的一部分,不管是現代文學還是當代文學史上,文學期刊雜志以及編輯、發表、出版和流通的過程,形成了一個巨大繁復的文學場,作家的創作和讀者的接受很大程度依賴于這樣的體制。你說的嚴肅文學的危機,前提是文學流通和接受或者說閱讀方式的轉變之。新媒體(微博、微信等)和網絡文學相輔相成,一方面改變了我們傳統的“紙媒發表—讀者購閱”的流通方式;另一方面,也為傳統的文學期刊帶來新的面貌。以前很多報刊亭會銷售文學雜志(當然也包括其他娛樂雜志、科普雜志等),讀者會在報刊亭購買閱讀,但是現在報刊亭越來越少,一些文學期刊漸漸縮到了圖書館、機關單位或者研究機構,淪為“專業讀者”閱讀和批評的對象。當然,現在網絡很方便,我們也可以通過訂閱文學雜志的微信公眾號獲取相關信息,這其實也形成一個新的“朋友圈”文學生態。在我看來,文學發展到今天確實遇到很多挑戰,期刊的發行量在減少,網絡文學、新媒體在膨脹……尤其在這個全球化時代,中國讀者也可以實時通過網絡讀到西方報刊發表的文學作品,及時了解世界文學動態——這是信息時代的便利。不過我想從另一個角度回應你說的“嚴肅文學的危機”。
結構主義批評家托多羅夫有本書叫《瀕危的文學》,作為一個經歷過前蘇聯和東歐體制的過來人,托多羅夫所謂的“文學的瀕危”也可以理解成是某種文學的危機,只不過這個危機是在特定的歷史形態和時期出現的,托多羅夫當然更看重的是文學本身的復雜性、豐富性。這是托多羅夫的現身說法,值得我們借鑒。文學在一個后革命的時代,在一個消費主義、物質主義大肆滲透進日常生活的時代,如何保持其獨立性和尊嚴,恐怕是每個真誠的寫作者必須面對和思考的。文學期刊當然很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載體。在這樣一個時代,只要你想寫,隨時都可以找到平臺發表,我們當下也有許多契機可提供給年輕的寫作者,比如連續舉辦了20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賽、《收獲》雜志推出的“青年作家專輯”、《鯉》雜志的“匿名作家”寫作計劃、“寶珀”理想國文學獎等等。
陳潤庭:可能因為“出名要趁早”,我們很急于“收割”青年作家。現在有很多提供給青年寫作者的賽事,幫助優秀的青年寫作者冒出頭,這當然是好事。但是不是每個寫作者都會在青年時期展露才氣呢?我覺得不一定。很多中年的寫作者,或許名氣不大,但讀他們的作品時,我總是肅然起敬。他們作品中的氣息與漫長的自我精神成長是分不開的。但我們的現實卻是,如果一個寫作者錯過了年少成名的班車,又不在高校、雜志社等機構任職,那么他的寫作似乎就注定了不為人知的命運。張定浩在早前的訪談中,曾說我們“現在對所謂的年輕一代寫作者越來越寬容”。歌壇有個說法叫“歌紅人不紅”,但很多年輕的寫作者或許已經獲得了文學獎的嘉許、文學界的關注,卻陷入了“人紅文不紅”的窘境。
談談文學吧,如你所說,在這個時代,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寫作者,作品也不存在發表不了的問題。由于網絡平臺的影響力,很多嚴肅文學的作者將自己的作品放到豆瓣、微信公號等平臺發布,有的閱讀量可觀,但大部分都只有可憐的閱讀量,或許這正說明嚴肅文學的危機看似始于網絡,但并不因為媒介的跟進而消失。某種狹義上的文學正在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退場,而看似與文學沒有密切關聯的領域,比如電影、二次元等,也漸漸進入寫作者的視野。可喜的是,文學因為走出了純文學的藩籬,借力打力,重新獲得了某種生命力。但事實上,在各股力量爭斗的角逐場中,以筆為生的寫作者是“資本”最薄弱的一員。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文學作品改編電影,原著往往成了一個空殼子。文學在當代文化生產中,成了初級的原料提供商,生產故事,生產戲劇沖突,但并不產生價值,更不具備社會批判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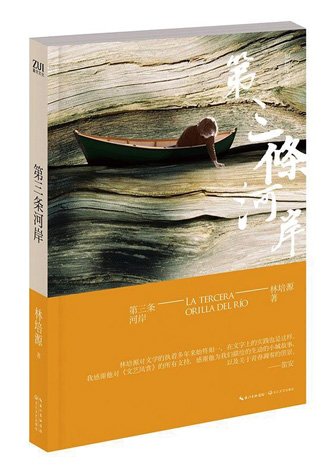
林培源:你觀察到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拿豆瓣來說吧,有的寫作者一開始默默無聞,習慣了在“無名”狀態下寫作,但寫作某種程度就是在暗中尋找讀者,所以他們會把寫好的文字貼到豆瓣上(不管是小說、評論還是其他體裁的文字),漸漸就引起了一些讀者的關注。有一類豆瓣“網紅”作家就是這么走進讀者視野的。這也是一種野蠻生長、最終進入主流文學視野的現象。他們當然也會在純文學期刊發作品,同時在網絡上凝聚了大量的擁躉,這樣就反過來引起了主流文學界(這里指的是上個問題談到的傳統文學生產體制)的注意,再被收至“麾下”。我當然也認可文學變得越來越小眾和專業化的說法。這個問題之所以不可忽視,是因為在當今社會每個人面臨的誘惑越來越多了,金錢、名聲、權力……2007年我參加第九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當時認識了不少寫作的同行,但是12年過去,堅持寫小說的人寥寥無幾,大部分都奔向其他行業了,有的或多或少還干著和文字相關的工作,比如編劇和影視行業;再者,面臨大眾文化(電影、動漫等)對文學空間的擠壓,寫作者會試著從這些領域里汲取一些營養,試圖去拓寬創作的邊界,比如有的人會借鑒賽博朋克電影(《銀翼殺手》等)的元素寫科幻小說,甚至將科幻電影中的一些世界觀和元素引入小說。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現象,關鍵還是不能顛倒了其中的邊界,小說最終還是要寫出小說本身該有的東西,也就是所謂的“文學性”,不能淪落為對其他文類蹩腳的模仿。
陳潤庭:你說“小說最終還是要寫出小說本身該有的東西”。米蘭·昆德拉也有相似的說法,他說“小說唯一的存在理由是說出唯有小說才能說出的東西”。但說出唯有小說才能說出的東西并不簡單。當代的各個藝術門類面對著同一個時代,當代的藝術創作者也面臨著某種“最大公約數”的存在境況。在這種情況下,小說要保住自身言說的活力,不淪為其他藝術門類的原料提供商,可能必須重視先鋒的作用。先鋒已死是老掉牙的議題,就連“80年代式的先鋒文學不會再有,但寫作永遠需要先鋒精神”,也只是老掉牙的空論。皮埃爾·布爾迪厄在分析文學場域時,說過先鋒派其實也分被承認的與不被承認的。當先鋒派被承認時,恰恰說明其先鋒性已經成為歷史。先鋒既是恒在的,又是面目不斷變化的。短篇小說集《神童與錄音機》“先鋒性”的體現,依靠的不是骨架嶙峋的敘事形式,而有賴于城與鄉兩種經驗的對壘與互滲。有時候我很懷疑,當下文學正在發生的先鋒派,是否還在嚴肅文學批評家和作者的視野之中。
林培源:你講得很好,不同時代的文學總有一個參照和反駁、對抗的對象,比如上世紀80年代的先鋒文學。先鋒文學的產生,一方面是從縱向的歷史上對此前文學觀念的反撥,另一方面從橫向上又是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互相交融的產物,莫言、余華、蘇童、格非,他們都是在世界文學尤其是拉美“爆炸”一代文學的滋養下成長起來的,你說的“承認的過程”實際上從文學史來看,也就是一個被逐步經典化的過程,被寫進了文學史,好了,你就被定性了,被供上了神龕供讀者瞻仰、研究者研究。順著這么一個文學史的邏輯和脈絡看下來,我們這個時代的“80后”“90后”寫作者和上世紀80年代的先鋒文學相比較,似乎變得越來越沒有先鋒精神,稍微瀏覽一下文學期刊,會看到太多庸俗、無趣的小說。怎么無趣呢?就是講一個圓滑的、自圓其說的故事,但是小說內在的精神含量淺薄得可憐;當然也存在另外的“野生作家”,他們蔑視陳規陋習,實踐著文本形式上的新穎,甚至踐行著一些跨文本和文類的實驗,以此顯示他們的叛逆精神。這當然是好事。但我在寫小說的時候,更多希望能在文本結構、形式和故事之間做一個調和,不完全拒絕講故事,但也不是奔著花里胡哨的形式而去,就像2016年我們做過的一個訪談,題目我至今仍很喜歡——《我想避免“平庸”的現實主義》,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陳潤庭:每次讀到這種“平庸”的現實主義小說,我都要花點時間平復心情,尤其是看到作者還是年輕人的時候。最后我想聊聊文學代際的問題。作為文學制度的一部分,文學代際的劃分有利于創作群體的推陳出新,以迭代的形式,保持文學的活力。“80后”作家在一開始便以爆炸式的姿態出現,引起諸多爭議。而“90后”作家則在“期待叛逆”的目光下登場,反而顯得乖巧溫馴。你怎么看待與你同代的寫作者,以及他們的寫作?
林培源:近幾年不少文學期刊推出了“90后作家專輯”,一些新鮮的面孔悉數登場,文學生態看起來比從前更繁榮了,可實際情況真是如此嗎?很多年輕寫作者確實在“期待叛逆”的目光下登場,但總體的姿態卻是乖巧溫馴的:他們很懂得批評家需要什么,讀者需要什么,他們很精明,知道怎么迅速地登上舞臺,那里有聚光燈打下來。這樣的情況也不惟“90后”,我們看到其他代際的作者寫到一定程度就疲乏了,作品中那種早年就該有的氣力褪去了,小說語言越來越油滑、松散,沒有生氣,寫小說變成了一個熟練的手藝活。這也是我自己要警惕的。和我同代的作家中有不少佼佼者,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東西。我有一個不成熟的看法是:小說最終構建和體現的是寫作者的文學觀。因此要進步,除了保持對日常生活的興趣和持續的觀察、思考之外,恐怕閱讀還是一個秘密武器,在閱讀中加深對世界的理解,重塑新的經驗,或許才能越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