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4-01 來源:安徽作家網 作者:安徽作家網
近期,我省作家江飛散文《水上的傳奇》發表于《人民文學》2023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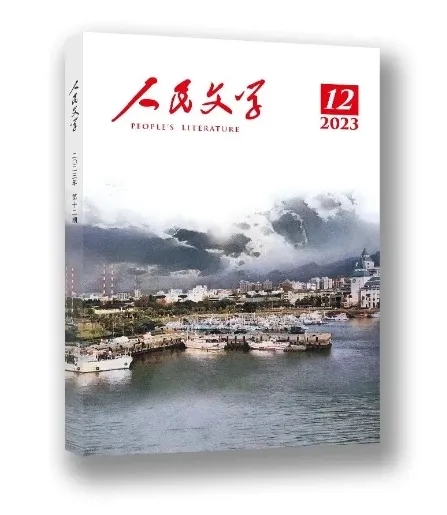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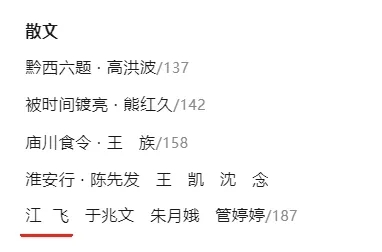
作品欣賞
水上的傳奇
江飛
“這個古鎮繁華了兩千年,吳王夫差開鑿邗溝時它就有了。如今是朝廷鹽運史的駐地,官衙森然,店鋪林立。大漢朝淮陰侯韓信和《西游記》的作者吳承恩都出生在這里。小波羅上岸溜達了一圈,在船上他就聞到了茶馓的香味。茶馓是當地的特產,手工把面拉扯成細細的一線,一圈圈繞成巴掌大的一塊,下鍋油炸,金黃酥脆地出鍋,舌頭用點力,入口即化。”二〇二三年九月十七日,當我坐在淮安古城河下古鎮的“文樓”里把一塊茶馓放進嘴中的時候,不禁想起小說《北上》里寫的這段話來——全長一千七百九十七公里、貫穿兩千五百年歷史的大運河則是他的文學原鄉。一路北上的意大利人小波羅是幸運的,因為他見識到漕運時代最后的繁華,而我卻只能面對歷史的遺跡和亦真亦幻的歷史,或許最繁華的歷史也終究敵不過一塊最日常的入口即化的茶馓。
歷史是一條長長的大運河,千帆競發,百舸爭流;大運河是一條長長的歷史,古往今來,綿延不絕。而淮安,正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北有古淮河,西南有洪澤湖,東南有白馬湖,它因運河而生,因運河而興,它創造了歷史的豐碑,水上的傳奇。
傳奇始于漕運,漕運是中華民族行走水上的智慧與故事。在春秋戰國、秦漢、南北朝的刀光劍影中,漕運成為軍事的后勤保障,成就了秦皇漢武的偉大功業。歷史的意味深長在于,驕奢淫逸的隋煬帝卻是大運河時代的開創者,他開鑿的大運河,縱向溝通海河、淮河、黃河、長江與錢塘江五大水系,為盛唐文宋的清明上河、西湖歌舞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三千里京杭大運河,推動和刺激了中國傳統的商業經濟,擔負起一個國家的生命線,更成就了長安、洛陽、開封、蘇州、杭州、揚州、淮安等運河都市的繁榮。明清之際,地處運河中段的淮安更是因為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而成為漕運之咽喉,作為中央政府的河道治理中心、漕運指揮中心、漕糧轉輸中心和稅收中心駐節有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得“天下九督,淮居其二”之名。“南船北馬,九省通衢”,無論是南糧北調、北鹽南運,還是絲、帛、茶、瓷、藥材、手工業品等商品南北交流,作為南北分界的淮安,成為南北水運樞紐、漕運鹽運集散地,成為“天下糧倉”。“襟吳帶楚客多游,壯麗東南第一州”,這是何等的壯麗,這又是何等的榮耀!
萬歷七年移建在此的“總督漕運部院”的門樓依舊巍峨聳立,兩旁的石獅依舊靜默不語——它們是見過大世面的:漕督曾掌七省漕政,節萬余漕船,數十萬漕軍,門庭若市的景象,猶如運河之上千萬艘糧船“銜尾而至山陽”。盡管“帆檣銜尾,綿延數里”的盛況已難得再見,但如今在淮陰船閘等候的貨船依舊絡繹不絕,也依舊像往昔那樣首尾相銜,有序通行。不同的是,曾經通閘需要等待幾天幾夜甚至十天半月,而現在只需幾個小時,甚至更短。相較于快捷的陸運,水運的特點也顯而易見,比如運量大、能耗小、污染輕、占地少、成本低、投資省。立于“京杭運河”號的船首,迎著烈日和微煦風,從淮安大橋下穿過,大大小小裝滿木材、沙石、鋼材等貨物的船舶,承載著千家萬戶的生活和希望,在兩側徐徐前行。“一閘不通,萬船難行”,我遙望著淮陰船閘入閘口的閘門緩緩閉合,水位緩緩抬升,緊接著出閘口的閘門緩緩打開,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自然而然。在淮安港務中心的調度室,“船閘集中控制系統”正進行著實時監控,原來這“井然有序、自然而然”靠的不是聽天由命,而是現代化的科學調度。
夕陽如金,水波不興。我根本無法想象曾經的清江閘,如何“斷纜沉舟”,又如何九死一生。那些幸存的人們,必須得感謝被譽為“中國大運河河工歷史博物館”的清口樞紐水利工程。歷史上的清口樞紐是黃河、淮河、大運河三條河流的交匯之處,因為黃河奪淮、淮河水系被破壞,明代著名水利工程專家潘季馴采取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蓄清刷黃、濟運保漕等方法,在清口樞紐建筑了水流利制導、調節、分水、平水、水文觀測、防洪排澇等大型工程,充分體現了人類農業文明時期東方水利水運工程技術的最高水平,代表了中國古代治河思想和科技精神的巔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從大禹治水到都江堰到清口樞紐,中國人的水上智慧和傳奇技藝怎能不讓我驚嘆?
水波蕩漾,夜色迷離。泛舟清江浦上,岸上人來人往,水上一座橋又一座橋。“夜火連淮水,春風滿客船”,這風景,王侯將相、顯宦世家曾見過,巨商富賈、文人墨客亦曾見過。遙望九層高聳的國師塔,莊嚴肅穆,燈光璀璨,如航標,映照浦上;御碼頭、石碼頭,如面孔,如燈火,如繁花,一閃而過。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清廷正式頒布停漕改折的令。“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白居易《長相思》)相思一曲終了,漕運一令終結。大運河依然流淌,從不停歇,淮安卻漸漸隱入歷史的煙塵。
清江浦畔,花街煙塵未絕。花街上并沒有花,只有高大的梧桐,在暗夜里默默守望。花街明清時就有了,很繁華,以前很長,現在只有這一小段。“虛窗暗透風如剪,深院絮飛霧似簾”,花一般的邱心如,二百年前也曾在這花街筆下生花,寫就長篇彈詞《筆生花》。此刻,這短短的、窄窄的花街上,只有三三兩兩的行人,和自由流動的手鼓與吉他輕柔的樂音。那是“花街微書局”門前,一支三五人的樂隊,抱著吉他的女歌手正在淺吟低唱。高懸的“淮安清江浦”紅燈籠下,是大大的“淮安”和“趁著青春年少,抓緊時間拍照”的黑底白字,顯出一派時髦又本土的文藝范。忍不住駐足傾聽,莫名就有些感動,為這群年輕的音樂人和自己一去不復返的青春。書局的老板是個面貌憨厚的“九〇后”,姓于,帶我們去街頭的一家“璞園糖水”。一碗色香味恰到好處的“木瓜桃膠”下肚,瞬間酒氣盡散,甜上心頭。當年“南船北馬舍舟登陸”的人們也大抵如此吧,一路北上,風塵仆仆,到這里停下匆匆的腳步,拐進花香四溢的花街,走進熱氣騰騰的人間煙火里。“南船北馬”,我細細咀嚼著的這四個字,正是那支樂隊的名字,或許也是未來某部文學作品的名字,但首先是一代又一代為生活而奔忙的中國人的代名詞吧。
身膺民社寄,民以食為天。南船北馬的人們,總會在運河河畔的酒肆茶樓交換各路消息,又總會在淮揚菜的滋味里相遇或重逢。“清淮八十里,臨流半酒家”,全鱔席、全羊席、全魚席,和精清新的淮揚菜系,伴隨著漕運的興衰,走過豪奢化、貴族化,最終回歸鄉土化、文人化。歷史也好,個人也好,菜系也好,終究要走一條返璞歸真、守常樂道之路。”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飰,摶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芍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飰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七發》)。作為淮陰人的漢代辭賦家枚乘,恐怕也難以抵擋筍蒲的魅惑,當然,他意不在此,而是以音樂、飲食等六件至樂之事,來勸誡貴族子弟不要過分沉溺于安逸享樂,而要學習探討“要言妙道”,用道德調理自身。
我埋頭吃著筍蒲,心里不由自主地想著“要言妙道”,想著想著,莫名就想起“中國淮揚菜文化博物館”入口處的海報上是明日即將上演的京劇《安國夫人》。哦,原來除了堯帝、韓信、吳承恩、周恩來,抗金巾幗英雄梁紅玉也生于此地!水上的傳奇,不僅滋養了人們的口腹肉身,更孕育了一個又一個個傳奇人物,并通過他們構建了中國的歷史文化、道德倫理和“要言妙道”。一部波瀾壯闊的運河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傳奇秘史啊!
杉青水秀,水流無聲。游弋在高大筆直的兩排池杉之間,猶如行進在歷史和現實的夾縫之間,竹筏顯得渺小,竹筏之上的人就更顯得渺小了。撐筏的老船工是個異常健談的人,姓崔,原是這片林場的員工,只聽他一路妙語連珠,高聲夸贊著“水上魚米之鄉”金湖。而我顯得有點心不在焉,因為我更在意的是那水中不停晃動的光影,那天空與池杉的夾角,以及那小巧如菩薩、氣度似萬佛朝宗的氣根。置身于金湖水上森林,仿佛來到一個世外王國,沒有車水馬龍,沒有狗茍蠅營,今夕何夕,似乎已不重要。可惜,筏到橋頭,又不得不匆匆離去,不經意轉身瞥見一片開放的睡蓮,在陽光下熠熠生輝——它們多么自在,多么幸福!
“水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這種角色,你不寫作會忽略它。而一旦你把它視作一個審美對象,就會發現一條河可以帶起你整個的生活。生活好像以一條河為中心,抓住了這條河就抓住了其他細枝末節的東西,或者說是綱舉目張”。還是作家深諳“水”的意義。或許,所有偉大的時代都有一條與之相關的大江大河,所有平凡的生活和生命也都有一條與之相關的大江大河。時間順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奔騰不息的歷史與河流,一定會創造新的時代,新的生活,新的傳奇……
作者簡介

江飛,男,1981年生,安徽桐城人,安慶師范大學美學與文藝評論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學院教授,碩士導師。北京師范大學博士,復旦大學訪問學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安徽省寫作學會副會長,“江淮文化名家”領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