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5-03 來源:安徽作家網 作者:安徽作家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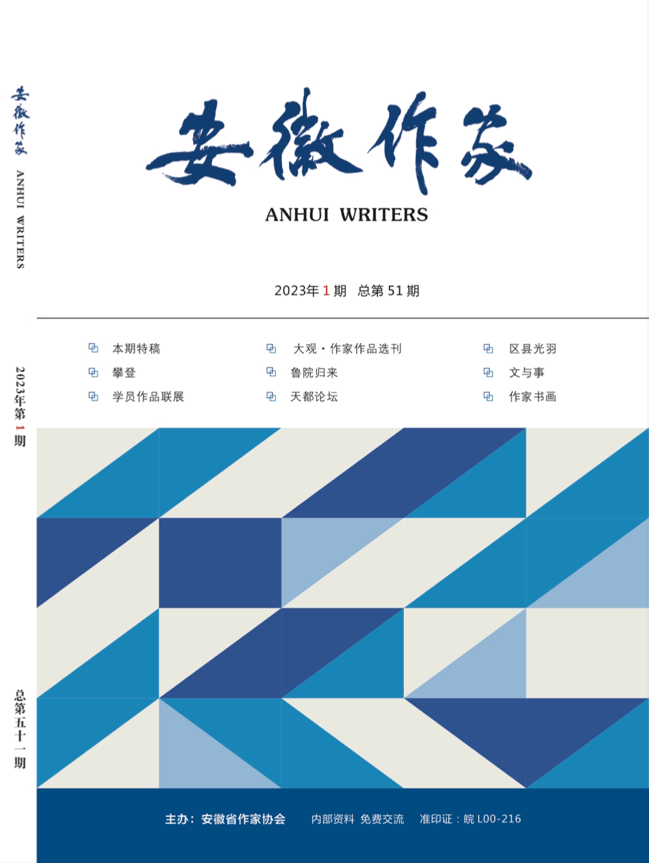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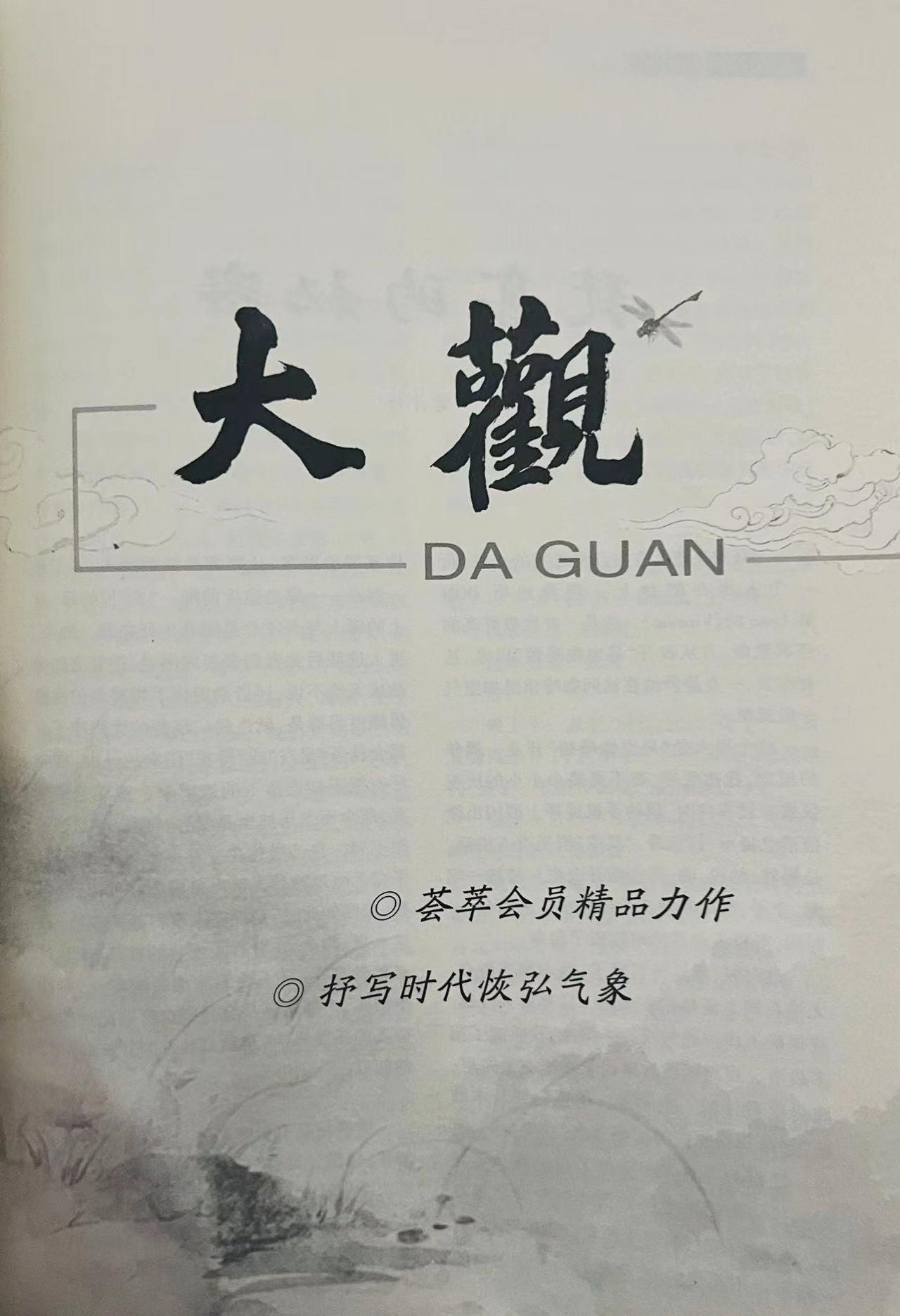
老病有孤舟
——讀杜散記
陳 墨
大歷四年冬。
一場鋪天蓋地的大雪,落在西京長安,落在城東的灞橋上,落在這座銷魂橋兩岸昔日依依楊柳上。灞橋風雪中,沒有了驢子背上的詩思,單剩下徹骨的凜冽與銘心的傷感。
大雪落在長安的街衢巷陌,落在城墻上,落在甕城中,也落進大明宮的宮墻內。
宮墻內,宰相元載裹著風雪,疾疾奔向紫宸殿。元載從內侍董秀那里私下得知,代宗對內侍魚朝恩負恃權寵不滿已久,為承圣意,冒雪晉見代宗,密奏朝恩專權不軌,驕橫跋扈,天下咸怒,并奏請代宗除之。代宗并無言語,嘴角露出會心一笑。只是,這一笑中包藏著不易覺察的詭異,這種詭異,也許只有紫宸殿外漫天飛舞的雪花懂得其深意,而元載此時僅僅從中仿佛看到魚朝恩的下場,那曉得這詭異一笑的注腳,遠在八年后自己的伏罪。
大雪飄在長安的天空,敗鱗殘甲差可擬。大雪掩覆了枯草,掩覆了萎苕,掩覆了長安城昔日的繁華與今日的凋敝。
這場大雪飄過終南山,飄過巴山,飄過漢水,飄過長江,落到潭州,直落得岳麓失翠,湘江凍浦,落得家家灶冷,戶戶衣單。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一葉扁舟停泊在白雪皚皚的湘江岸邊,一陣瀟瀟寒風,將一蓬雪花送進船艙,落到一位滿頭白發的老者面前。瘦骨嶙峋的他,支撐著偏枯的右臂,兩眼昏花地對著艙外的飄絮。他一直就這樣端坐艙內對雪,默默地目送一片片雪花悄無聲息地落進江水。他看見一片枯葉與雪花同飄,仿佛自己飄蓬異鄉,孤寂與茫然油然而生。他也想借綠蟻來排遣內心的寂寥,他也想生紅爐來溫慰身心的饑寒,可室如懸磬的他,哪里買得起酒?即使能夠賒來,也是有酒無友,借酒消愁愁更愁。他只好在無人盡歡的孤獨寂寞中,一直對著凄冷森寒的飄雪,到黃昏,無人至,等來的卻是倦歸的寒鴉。
這位落魄的對雪者,不是別人,正是曾經“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詩人杜甫。是的,正是曾經寫下“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詩人杜甫;正是曾經信心滿滿,“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立志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詩人杜甫。
杜甫的一生,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一生。
胸羅萬卷,突破、磨破、識破之,得以左右逢源而下筆有神。此乃其成為詩圣的根柢。
吳越與齊趙的漫游、長安十年的求索、國破后的流亡、隴右的奔命、成都草堂暫憩后的再次流亡、夔府孤城、湘水孤舟,他的身心一輩子都行走在充滿坎坷、困頓、沉郁與抗爭的路上。惟其如此,方成就其詩作詩史、圖經之美名。
當漁陽鼙鼓驚破霓裳羽衣曲后,唐玄宗失去了長安和寵愛的美人。杜甫“致君堯舜上”的幻想,在其為之苦苦求索十年后,也開始動搖。當他懷著一線期望,冒著生命危險,投奔鳳翔,一路上看到的是輾轉于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而朝堂上下,盡是些亂綱壞紀的關中小兒與見不得太陽的于腐草中飛出的螢火蟲,以及為了權位利害一家骨肉自相搏斗的君王。這等情勢,給予他以痛心徹骨而外,便是徹底的絕望。
他如一只失群的孤雁,不飲不啄,只是翕張雙翅,一路哀鳴,一路回首依戀不舍的長安和洛陽。
他于川原即將昏暗之時,落腳秦州。他獨步薄暮中,聽到的,時而是四面邊聲連角起,時而是胡琴琵琶與羌笛,時而是從戍樓上傳來的嘹亮的胡笳;他孤行平明里,看到的,是降虜千帳,胡人跳著白題斜舞,在黃云白水間羌婦笑語,胡兒行歌。他還望見出使吐蕃的驛使和抵抗吐蕃的行軍,以及在“隴草蕭蕭白,洮云片片黃”的天地間搖動著慘淡的烽火。他想在太平寺泉水下游,開辟一片藥鋪,引清泉以澆灌。可他“囊空恐羞澀”,且“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開園拓圃只能是一種美好的夢想。饑寒交迫中他,身體開始轉向衰弱,瘧疾又發作了,每隔一日,便發高度的寒熱,身上的脂肪與骨髓仿佛將在病中耗盡。這年,杜甫年方四十八,尚未半百,已顯垂垂老矣端倪。
他用“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的詩句與秦州作別,一如西風中的一匹瘦骨嶙峋的班馬,開始新的流離轉徙。落日里兒童號饑,寒水中馬骨欲折,峽谷上碎石搖搖欲墜,老林間熊羆咆哮、虎豹哀號、山鬼長哭、狐狨低嚎。在泥濘不堪的泥功山上,他的“白馬為鐵驪,小兒成老翁”,差一點就把自己交代在那里。可是,當他掙扎著翻過泥功山,結草堂于飛龍峽西岸,遙望對岸的鳳凰山上鳳凰臺時,他在感嘆鳳聲之不聞之余,設想上有無母鳳雛,在饑寒中亟待照料,而他寧愿將自己的心當作“竹實”,把自己的血當作“醴泉”,來飼養這只鳳雛,以期長大后銜來瑞圖,飛回人間,“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
可是,鳳凰臺上并沒有鳳雛,饑凍交湊的正是杜甫自己。他終日在山林里拾取橡栗、尋找黃精。冬日,林海變成雪原,兒女們常常餓得眼冒金花。他只得剖雪求食,冰天雪地中,悲風從天吹來,撩動他的衣襟,撩動他眉宇間的惆悵,把他的心吹得徹骨地寒。
是年冬末,杜甫這匹瘦馬,更是“毛暗蕭條連雪霜”。但他沒有停止前進的步伐,蜀道上,踢踏踢踏之聲,雖緩慢,卻不失堅實。這天,他終于來到雄壯的劍門前,關下溪壑間的潺潺流水,仿佛為他透露出些許春的消息;俯望關內原野,險阻從此終止,心胸豁然亮堂。
是的,揚一益二,長安洛陽以外,除去揚州就要數成都最繁榮了。秦滅巴蜀以后,以四川盆地為基地滅齊伐楚建立秦朝。西漢時,繼續開發巴蜀,巴蜀大地繁榮興盛富甲一方,盛唐時期,人稱天府之國。四年前,唐玄宗從長安延秋門出逃,就是直奔成都而來的,兩年后,安祿山被殺后,才由成都返回長安。也就是從天寶之亂起,這塊曾經的王道樂土,覆巢之下,內被徭役與稅賦重壓,外受吐蕃侵擾,此時也陷入了互相斫殺的局面。
不過,在經歷長達四年顛沛流徙的杜甫看來,較之隴右,成都尚算安寧,起碼氣候比長安要溫暖一些,吃食比隴右要易得一些。
成都城西七里,有一座浣花溪寺,這年歲末,剛踏進成都的杜甫寄身于此。由冬及春,寺外不遠處的一棵高大的楠樹下,一座略可棲身的茅屋落成了。從此,這座樸素谫陋的茅屋,便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塊圣地,后人盡可以忽略杜甫的生地與死地,卻總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草堂是開敞的——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身處其間的杜甫,沐浴在春風里,看白鷺頡頏,鴛鴦沉浮,尖荷小葉,細麥輕花;聽柳間黃鸝,雨中燕語,春宵甘霖,田園交響。他似乎陶醉在自然里了。
其實,陶醉于斯的杜甫,并沒有沉湎于“嫩蕊商量細細看”的細微,并沒有耽溺于“自在嬌鶯恰恰啼”的輕盈,而且可以說是一刻也沒有停止過他的沉郁與思念。
那顆有著兩百年樹齡的楠樹,為風雨所拔,“虎倒龍顛”,英雄失路;“淚痕血點”,人樹兼悲。嘆楠兼自嘆: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茅屋為秋風所破,他不以草堂飄飖為憂,卻以己度人,生出大庇天下寒士之意,其迂闊如此,比之“心以當竹實”、“血以當醴泉”的犧牲自我的精神,何曾有二致!
盡管他處在疏疏落落的亭臺里,看著浣花溪畔天地疏朗,病體也感到輕快了許多;盡管他常常“仰面貪看鳥,回頭應錯人”;盡管他閑散到“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的程度;盡管高適和嚴武,一個是他梁宋漫游時的舊友,一個是他昔日仕途上的同黨,他們經常親自攜帶酒饌,竹里行廚,花邊立馬,真摯的友情使他忘卻笑語供人的辛酸。可是他對于他的故鄉和流落在他鄉的弟妹親人還是念念不忘,他著手營造草堂的時候,也不曾放棄過順江東下的念頭。東京沒有收復,鄉關胡騎恣虐,親朋的消息長期隔絕,他只能悵望云山以外的長安與洛陽,在風色蕭蕭的夜晚感發“萬里正含情”,憂思悲恐像脫韁的野馬,在心頭上奔騰起來。
他送嚴武入朝至綿州,在奉濟驛分手時說他自己:“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
當他剛送走嚴武,還未來得及返回他的成都草堂,就聽聞得成都已淪入“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的慘境,這回,他非但歸不了秦,就連草堂也回不去了。他不得不再次流亡。
“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的杜甫,暫別成都,暫別草堂,流寓梓州。廣德元年春天,五十二歲的杜甫聽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消息,以飽含激情的筆墨,寫下了他“生平第一首快詩”。他自己于這首詩下自注:“余田園在東京”,詩的主題是抒寫欣聞叛亂已平的捷報,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悅與雀躍。這種喜悅之情,如萬斛泉源,出自胸臆,奔涌直瀉;這種雀躍之意,一氣流注,曲折盡情,不是杜甫這樣的命途多舛而又百折不回的人絕不能道。
白首、放歌、縱酒,胸中郁結為之頓消,青春、作伴、還鄉,從此可以不再流浪。
四年前,李白于白帝城忽聞赦書,驚喜交加,旋即放舟東下,“千里江陵一日還”的喜悅暢快之情,今時杜甫之心情與其何其相似?!
遺憾的是,杜甫的喜悅暢快和狂歡,只是曇花一現,大唐的天下,不過是驅走了虎,卻又引來了一群豺狼——回紇更為驕橫,吐蕃欲豁難填,甚至再次兵不血刃地占領了長安。他回家的路正所謂“道阻且躋”,他魂牽夢縈的長安八年內兩度陷落,“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他為回不了東京田園而傷感,更為回不了盛世長安而痛心疾首。
天下動蕩,人世混亂,杜甫不得不攜妻挈子暫別草堂,往來于梓州、閬州、射洪、綿州、漢洲之間,“三年奔走空皮骨”。衣食無著而又身無長物的他,為了生計,不得不鬻詩陪座,自覺老丑的他,又怕因性格坦率而出言傷人,陪居末座的他只好連酒杯子也不去碰它,所賣詩文,也只好低頭折節,附炎趨勢。他滿腹辛酸地自嘲道:“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
在離開草堂一年零九個月里,他就這樣身不由己地游走于劍南東道與山南西道之間。這里的山川遺跡,使得他于自嘲以外獲得些許的慰藉,“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當年,吳生曾在長安大同殿的墻壁上畫過嘉陵江邊三百里的巴山蜀水,而今,杜甫也用他的雙腳和詩行勾勒出一幅壯闊的北川百里圖:這上面有“碧瓦朱甍”的越王樓,樓下長江萬丈清;有“丹楓萬木稠”的積香寺宮閣;有惠義寺、牛頭寺、率兜寺、滕王修建的玉觀臺;還有南池子漢高祖祠前的儺舞。他不失時機地去憑吊陳子昂、郭振元和薛稷的遺跡,感念這幾位蜀中人杰的卓爾不群,與他們進行穿越時空的對話,排遣自己內心的孤獨。
這年秋天,杜甫的蜀中舊游一如經霜烏桕一般日漸零落,他終于下定決心,要“長嘯下荊門”了。他懷揣章彝為其籌措的路費,手執章彝贈送的桃竹杖,想象著即將入西漢水至渝州東下。與知交辭行時,臉上露出欣喜之情——盡管路途上充滿艱險,盡管他還沒有最終決定是去洛陽,還是去江南,無論如何他可以離開這片交游冷落之地了。
他真的要離開蜀中東游了,就連朝廷召他為京兆功曹,他都拒絕了。
一個意外再次改變了他的主意。他正欲啟程時,嚴武回到成都做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殊方又喜故人來”,成都草堂在他的心中又占了上風。他在閬州去到房琯的墓前,與九泉之下的舊友作了最后的訣別。暮春三月,回到成都草堂。
孟春時節,浣花溪畔,是“黃四娘家花滿蹊”,是芳樹無人花自落。草堂前,鷗鳥戲水,燕子呢喃,戲蝶翩翩,嬌鶯恰恰。杜甫踏進草堂,舊犬咬曳著他的衣裾,嗚嗚低徊;昔日芳鄰,或落魄文人,或村夫野老,爭相攜壺沽酒;嚴武親自前來探望,并不時派人送來日用所須。杜甫攜著春天一齊歸來,草堂便又有了生氣。
他本想就這樣在桃樹、松樹猶存的草堂里,開圃種蔬,也種一點草藥,躬耕之余,或對花樹發幽思,或引壺觴以解乏,或撫琴書以消憂,或倚西窗以寄懷。可嚴武卻不肯讓他在浣花溪上過清閑的生活,為他謀得節度使署中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的職務,賜緋魚袋。一方面迫于生計,另一方面,嚴武的知遇之恩盛情難卻,杜甫只得離開草堂,遷入成都節度使署中。滿頭白發的杜甫,穿著狹長的軍衣,遵循幕府的規矩,過著呆板的生活,在幕府里與那些互相猜疑、互相攻擊、爾虞訛詐的幕僚周旋,偶爾還會被同僚們嫉妒,受他們的攻擊,心中充滿難言的憂郁。十分壓抑的幕府生活,使得本有肺病與瘧疾的杜甫再添新疾:風痹。寂靜的深夜,青燈如豆,他緩慢活動著麻痹的四肢,將眼光投向窗外高深莫測的黑夜,憂思感憤涌上心頭:“瘧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他于憂思感憤之際想到陶淵明與謝靈運:“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于是堅辭幕府職務,回到草堂。孰料,他回到草堂月余,嚴武忽然辭世。萬分悲痛加的他,只好“殘生隨白鷗”,“轉作瀟湘游”,依依不舍地與草堂決絕,一葉孤舟,向東飄去,單把草堂連同錦里、石筍街、果園坊、石鏡、琴臺、先主廟、武侯祠……留在成都,留給千秋后世。
凄孤無依的杜甫帶著家人,在岷江、長江上漂泊。這天傍晚,舟泊渝州或者忠州江畔,微風吹拂著江岸上的細草,搖曳著泊在岸邊的孤舟,明星低垂,平野廣闊,月隨波涌,大江東流。對此景象,杜甫不覺百端交集:那江岸細草柔弱與渺小、江中孤舟的漂泊與寂寞,不正是自己的寫照?遼闊的平野、浩蕩的大江、燦爛的星月,不正反襯出自己的孤苦伶仃與顛連無告?遠大的政治抱負,長期被壓抑而不能施展,聲名竟因文章而著,哪里是自己的心愿?既老且病,哪里是自己休官的根本原因?于是,他一字一淚地寫下:“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轉徙江湖,水天空闊,這只孤零零的沙鷗,倦了,累了,更因一路上濕氣侵犯,肺病和風痹再次發作。他在云安,擇一臨江水閣,將病軀寄寓其中,整整一個冬天,像蟄伏的蒼鷹,等待著云開日朗。
春天來了,杜甫的病情略有好轉,可他在江上或江邊看到的仍是“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山居的村莊則是“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杜鵑晝夜不斷的凄苦啼鳴,聲聲入耳,一病經年的他,不能夠再像草堂居住時起身崇拜,只能“淚下如迸泉”了。
不知是因為七年前李白于此留下那篇驚風雨而泣鬼神的快意詩章,還是因為這里的山川雄壯險峻,船到夔州,杜甫按下行程的暫停鍵,似乎有點流連忘返了。雖然抱病無力,他仍多次上白帝城,憑吊古跡,懷古傷今,登臨之余,每每生發出“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的喟嘆。他拖著病軀,在滟滪堆、在瞿塘峽、在魚腹浦、在八陣圖、在瀼東、在瀼西、在赤甲白鹽二山,以及武侯祠、高堂觀,暫得觀形勝,悠然慰轉蓬。所到之處,皆留下了神接古人情出乎己的詩篇,這些詩篇最可貴之處,不僅在于對山川秀麗的狀寫,而且蘊含著深切的憂國憂民情思,可謂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
他在《八陣圖》寫道:“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遺恨二字,與其說是他在為諸葛亮惋惜,倒不如解讀為他自己“傷己垂暮無成”的抑郁情懷。他在《宿江邊閣》中寫道:“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早年就有“常懷契與稷”的政治抱負,如今漂泊羈旅,無力去實現整頓乾坤的夙愿,社會的動亂使他憂心如焚,徹夜無眠。此一聯正是他憂心國事的情懷和潦倒艱難的處境之真實寫照。
杜甫老了,真的老了。他一邊說:“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身體時好時壞,瘧疾、肺病、風痹、糖尿病都不斷地纏繞著他,牙齒脫落過半,耳朵失聰,已然是一枚風前殘燭。另一邊開始回憶他的青年時代。他回憶年輕時與李白、高適梁宋之游以及當時的社會狀況,回憶早年登泰山時的情景,追憶長安往事,倦鳥整翮般地梳理安史之亂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他用一篇《壯游》為自己作傳:自生而穎異,豪邁不羈起,到飽覽吳門古跡、越中勝境;到歸帆洛陽,放蕩齊趙;到再歸長安,意氣風發,獻賦不拜;到天寶之亂,公疏救房,拾遺始末;直至流徙隴右,滯留巴蜀。后世人說:“李白從未老去,杜甫未曾年輕”,倘若沒有《壯游》,杜甫的年輕時代還真是霧里看花,至少他那裘馬輕狂的一面很難讓后人所清楚明朗。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杜甫在夔州抱病獨登臺,作客思鄉、久客孤獨、悲秋苦病、人在暮年、壯志難酬,萬千感愴縈繞胸懷,筆端生出無限悲涼之意。于是,有了《登高》這首曠世之作,一曲響遏行云的悲歌。
這只老病交加、孤單困苦的孤雁,再也不能夠鴻飛冥冥了,但他卻還要不斷地呼號、追求,他那憂己憂民憂國之情在心中熾熱地燃燒,雖然不能夠鵬程萬里,但絕不裹足于暮雨寒塘。
然而,造化弄人,風雨如晦的政局帶給杜甫的結局并不如他所預期。
一個綠柳才黃半未勻的清晨,杜甫從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過三峽,去投他在江陵的弟弟杜觀。他在船上把他的命途又溫習了一遍,同時盤算著到江陵后一定要去拜謁天皇寺,看看寺里陳列的王羲之的書法和張僧繇畫的孔子及弟子的畫像,然后停留時日,或是北歸,或是沿江東下。
可當他到達江陵時,杜觀卻淡出了視線。是年,北方戰事又起,吐蕃進攻鳳翔,長安受到威脅,他只好放棄北歸。而江東的姑母和弟弟杜豐又久無消息,東下不成,他只得留在江陵。所幸,他的堂弟杜位與好友鄭虔的弟弟鄭審,一個在荊南節度使署任行軍司馬,一個為江陵少尹,為他暫留江陵略有幫助。可當他拖著瘦骨嶙峋的病軀去拜訪他們時,門人不肯通報,幕僚極盡冷淡與譏諷,“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鰓”。嘗盡殘羹冷炙的辛酸的他,對為什么會淪落到這般地步,百思不得其解,他高昂倔強的頭顱,用混沌不清的目光傲視蒼穹,向蒼天發出詰問:“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
深秋的江陵南浦,雨洗平沙,天銜闊岸,杜甫沒有向任何人辭行,登船離開江陵,開始新的漂泊。他給鄭審寄去一首詩,詩中說,雖然飄然離開江陵,實際上自己也很茫然,不知所往,只好將行將就木的病軀,連同那葉孤舟,寄托江湖之上。社稷罹難,晚年的自己如同棄物,到哪里都是窮途末路。陳蕃之榻,避難桴槎,這輩子都與之無緣了。
日暮窮途的杜甫,真的是走投無路了。
漂泊江漢之上的杜甫,思歸不能歸,成了天涯淪落之人。但他不屑于窮途當哭,仍心憂社稷,“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暮齒之年,壯心不已,世人多謂秋興悲,獨有他這位“腐儒”面對颯颯秋風,反而覺得病體都開始好轉了。他甚至想到,古人存養老馬,并不是取它長途跋涉的健力,而是用它識途的智慧,難道自己連一匹老馬都不如嗎?乾坤之內,腐儒如杜甫者能有幾人?他的一片忠心,比天上那輪孤月還要皎潔!
歲暮,寒云四合,北風呼嘯,杜甫的一葉孤舟,在洞庭白雪中茫然獨行。天寒地凍的洞庭湖上,漁父的漁網上結著冰凍,獵人的強弓在寒風中空鳴,洞庭湖邊,隨處可見賣兒賣女的人家,他們被迫忍痛割愛以繳納租稅和代役的絹匹。舟中,杜甫用他麻痹的被凍得瑟瑟發抖的手,顫巍巍地寫下“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的詩行。
年初,春風料峭,岸柳舒眉,浩瀚無邊的洞庭湖水波瀾不興。杜甫登上岳陽樓,極目吳天楚云,俯瞰萬頃煙波,仿佛覺得日月星辰都漂浮在湖水之中。對于一般初登岳陽樓的人而言,目睹這樣的勝景,應當是心曠神怡、喜不自勝的,而對于已經是“漂泊西南天地間”,沒有一處定居之所,只好以舟為家的杜甫來說,自然無法歡喜,只有遲暮之年的沉郁了。更兼親戚朋友音信杳然,老病加身,“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凄涼落寞,油然而生。杜甫倚靠闌干,遙望萬里山河,不見絲毫春色生機,看見的卻是關山萬里狼煙遍地,不禁涕泗滂沱,聲淚俱下。
既然北方關山迢迢,戎馬蕭蕭,那就繼續南飛吧。
杜甫入湘,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便是韋之晉。是時,韋之晉任湖南觀察使、衡州刺史。當年,韋之晉赴任湖南觀察使,途徑夔州,與寓居夔州的杜甫談詩論文,杜甫以詩相贈,勉勵他說:“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對韋之晉寄予厚望。只是杜甫那時的計劃是或北歸,或東下,沒想到要南投。
杜甫投韋之晉與在成都投嚴武,雖然同樣有世交的緣故,又不啻世交。杜氏與韋氏同為京兆望族,且世代聯姻,關系過從甚密。杜甫與官僚士大夫韋濟、左相韋見素、畫家韋偃以及詩人韋迢、吏隱文人韋諷等韋氏彥士,交誼頗深。此外,韋之晉不僅是方鎮首領,亦是一位擅作詩文的文人,在當時的文壇上有一定的地位。他的境遇雖優于杜甫,但二人性格志趣頗多相似,尤其是當時杜甫詩名并非顯赫,但韋之晉對杜詩卻傾慕有加。
春水引行舟,桃花夾岸流。有了目的與方向的杜甫,心境一如這春水和桃花,漸次明亮起來。他率領家人,在春風春雨春色里沿湘江溯流而上。云帆一片,征途千里,目之所及,山青水碧。他在途中,仍是走走停停,觀景、會友、感懷身世,仍是那么憂國憂民,仍是用他那并不利索的手抒寫雖不失明亮卻依然寂寞孤苦的心:“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后世范希文所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不是由杜詩化得,實不得而知,但二人的忠君憂國的襟懷一脈相承,則是不容置辯的。
宋之問詩云:“近鄉情更怯”,是謂游子歸鄉心情復雜,而杜甫船行至潭州北界喬口時則說:“凄惻近長沙”。凄惻者,情景凄涼而感觸悲傷也,亦是行子斷腸之謂。歸路愈行愈遠,歸期遙遙無期,眼前雖然是蜂飛蝶舞,燕呢鶯語,怎奈何落日春華,殘年暮景,想到自己走進的正是同鄉賈誼的謫居地,叫他如何不凄惻。
《湘中記》載:“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舟行湘江,過屈原曾經在《九歌》中吟唱過的湘夫人祠,杜甫詠罷那里的江色斜暉、春竹暮花后,對此清川仍不住回眸贊嘆:“湖南清絕地”!如此清絕之地,徒為遷客羈人之所歷,此萬古所以同嗟也。清絕,該是杜甫繼凄惻爾后,對湘江的第二印象了吧?
一日午后,孤舟行至銅官渚,但見房舍鱗次櫛比,人煙輻輳。銅官渚,原是楚國鑄錢之所,現設有燒磁的官窯,燒得上等瓷器。杜甫讓船夫落帆系纜,棄舟登岸,獨步山野。當時正值春耕,田野山地,但見農夫們“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農人勞作,讓他憶起草堂藥鋪,憶起他的東京田園,不禁黯然傷懷。
惠風相從,孤舟似乎輕快了不少,不日,即至潭州。杜甫囑咐船夫將船繞過橘子洲,泊在河西古渡,他徑直來游岳麓山。在麓山寺前,他見到闊別二十余年的故友李邕書寫的巨碑,如今天人暌隔,覽碑思人,唏噓不已。他又在寺內讀到五十年前宋之問流貶欽州道經潭州于殿堂壁上的題詩,題詩字跡可辨,詩中的憂憤清晰可感,引起他意外的驚喜與感慨。和暢的春風,攙扶著他,像一只忘機的山羊,漫步在岳麓山間。他從不奢求功名富貴,可潭州古樸淳厚的民風、岳麓山清幽凈靜的勝境,十分難得地使他連百般憂患也暫時忘懷。他說他要誅茅筑屋在這里傍煙霞,把一重一掩的山林當作肺腑,把山鳥山花當成自己的兄弟朋友,還要就教于老禪師依止終身,不為韜光養晦,只為休養多病的身軀。其意與李白的“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如出一轍,只不過,李白說的是醉后酒話。
這種忘懷只是曇花一現,以天下為己任的濟世情懷才是杜甫的本真。
清明時節,天氣晴朗,春風和煦,柳絮飛揚,飛鳥在天上自在飛翔,湘江兩岸家家戶戶的廚房里冉冉升起了新火的輕煙。杜甫走在潭州的街衢上,女孩腰肢纖細,惹人憐惜,身著明艷衣裳的活潑少年三五成群,嬉戲打鬧。看到這般天真無慮孩童,杜甫不禁想起他在洛陽七歲吟鳳凰的美好時光。杜甫走進太平街,走進湖湘文化的濫觴之處太傅里。昔日的定王府已然霧廓云除,冰消瓦解,好在賈誼當年所鑿的那口古井猶存。他于井旁石床坐下,睹物思人,緬想起這位主張“與民以福,與民以財”的長沙王太傅,少年得志,胸懷雄才大略,屢遭嫉妒誹謗而被謫遷,最終英年早逝。賈誼是洛陽人,九百年后,同是來自洛陽的杜甫,貧病交加,窮苦潦倒,但他已近耳順之年,于賈誼于己,似乎不再有什么感傷。他走出太傅里,走出太平街,舉頭忽見衡陽雁。他的心便隨雁飛往北國家園,他想,故園里也當是一片清明風光,家家戶戶也正在紛紛鉆青楓取新火,長安城樓也掩映在一片輕煙花語中,那萬里山河也是一片錦繡吧。只可惱“春去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可杜甫卻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他要繼續向南,他將離長安越來越遠。“性豪業嗜酒”的杜甫,其時也不勝酒力,但他昨夜還是借酒消愁,痛飲沉醉而眠。平明時分,湘江兩岸一派春色,他懷著黯然傷情的心緒,作別潭州。春晨古渡,只有飛舞的落花為他送行,檣桅春燕作語,似乎在親切地挽留他。春風撩動著他帶有酒香的衣襟,時斷時續的雎鳩關關之聲,唱得人心煩意亂,落魄斷魂。他再次想起被貶長沙的賈誼和褚遂良,兩位古人的命運,與自己因疏救房琯離開朝廷而沉淪不偶是何等相似?不覺悲從中來,一腔愁緒恰似清絕悠長的湘江之水。
舟行衡州,回雁峰在望。
回雁峰并不高,然而“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歸”,卻是為何?原來衡州以北有洞庭湖,沼澤港汊縱橫,冬季極少封凍,北雁到此,晝間可覓食水中魚蝦、田野遺谷,夜間可棲蘆葦蕩,或飲或啄,或嬉或棲,實在相宜。況北飛到此的大雁,幾經長途跋涉,體力大耗,再渡南嶺,途中食宿難支。故而王勃說:“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杜甫這只孤雁,南投衡州,本來想在刺史韋之晉門下,斂翮閑止,覓些“魚蝦、遺谷”,與這位蒼生倚靠的“盛才冠巖廊”的大臣,共襄扶顛盛舉。孰料他尚在逆水途中,這位衡州刺史就已改任潭州刺史,往潭州赴任去了,命運再次與他開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玩笑。
蒸水蒼茫,耒水蒼茫,湘水蒼茫。一群北歸的大雁,在蒼茫的暮色里排成一字陣,翕張羽翼,云天中時而傳來它們歡快的唱和聲。杜甫發現,一只受過弓箭傷害的大雁,流落湘江水湄沙邊,引項向天,目送那群北歸的大雁,過洞庭,過終南,過渭水。其行斷影孤,聲聲哀鳴,不忍卒聽。
杜甫剛下船,聞得韋之晉改任的消息,便不得不和衡州告別。他調轉船頭,順湘江北下潭州,一路上,無非是“.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當杜甫到達潭州,得到的消息是,韋之晉在到達潭州不久不幸暴卒。一霎時,杜甫仿佛冷水澆背,七情昧盡,整個人都僵了。他悲慟至極,長歌當哭:遙想當年與你在郇瑕結交,至今雖已四十來年,當日歡娛卻在眼前;在京師你不忝尊榮,端莊文雅、自在超然,閑暇里還常常屈尊與我詩文往來;后來我雖如那易老馮唐且疾病纏身,但每每聽到你升遷的消息都由衷地感到喜悅;你還記得夔州臨別時,我送你以天下蒼生為重、廣開賢路的贈言嗎?你怎么就這么倉卒而去,你怎么放得下朝廷之命、朋友之托、元元之期?“誰寄方隅理,朝難將帥權”!
往衡州投韋之晉不遇,轉潭州再投而韋之晉已然“飛旐泛堂前”,使得在失望中不斷尋找希望的杜甫徹底絕望了。從此,他在陸地上再沒有安身處所,直至他終老,一年多的時光都是在孤舟上度過的——他徹底變成了一朵浮萍。
時維夏末,橘子洲上綠橘滿枝,湘江水中魚逐細浪。湘江東岸一隅,一艘烏篷便是杜甫的家。天氣適宜時,杜甫也會上岸散散心。岸上不遠處的州府“綺樓關樹頂”,可對他來說,為賢者諱,那里是不便去的,去了只會更傷心。他喜歡往太平街太傅里轉轉,喜歡在太傅里的那口井旁石床上坐下來,一邊閉目養神,一邊情馳古賢,生出無限的喟嘆來。他有時會走得更遠一些,去到鄉村郊野,他在那里看見的是田園荒蕪,柴扉洞開,農具閑置,農民逃之夭夭十之八九。可這一帶并無兵燹,卻為何如此荒涼蕭條?杜甫因詢之老媼,答曰:不堪苛捐雜稅的重負才背井離鄉的。他悵望北方,一聲長吁:“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
其實,他自家雖無苛捐雜稅之虞,但處境也是不堪的。他的夫人常常眉頭雙蹙,凝視著滾滾不息的湘江水,瞅著沒米下鍋。他那十六歲的兒子宗武,由于饑餓,面帶菜色,一副皮包骨的模樣,還要用很多的時間讀什么《文選》。
湘江岸邊的柳絲與杜甫的憂思共生同長。夏日炎炎,柳絲間蟬鳴喧闐,杜甫的病復發了,他抱病江閣下的舟中,仔細梳理他在湖南的一些親朋故舊,猶疑數日,給他內弟崔潩和他祖母的同族盧岳寫了首詩,詩中非常委婉表達了他客居潭州、貧病交加的近況,希望得到他們的接濟。他還在詩中透露出“莼鱸之思”,他對二位說,他回憶起香味醇厚、鄉情悠悠的錦帶羹,還回憶起長安昆明池中的菰米,漂浮在湖面上,像一匹黑色的錦緞,而用它做出的雕胡飯,柔滑香糯,那可是真正的玉食啊。詩書既出,崔、盧兩位侍御到底有無接濟杜甫,不得而知,或有三杯兩盞淡酒,或有一升半斗菰米,抑或什么也沒有。這無關世風,也不是世態涼薄,是世道自顧不暇。
為了生計,杜甫不得不常常拖著殘疾多病的身體,去到魚市上擺攤賣藥。大雪初霽,魚市中那座廟臺朝陽處,杜甫像一條可憐的“窮轍之鮒”蹲踞其間,面前大大小小一二十個紙包里裝的是蜀蒼耳、決明子、杜仲、川貝母、黃獨、黃精、半夏、夏枯草……這些藥,是他近十幾年自己種植或從山野中采擷、自己備用的,有長安的,有隴西的,有成都的,有夔州的,像黃獨,那還是他在同谷縣深山里挖掘的。不久,他的這些陳貨賣得差不多了,便由宗武陪著他,到稍遠的藥市上采購一些新的藥材回來,拿到魚市售賣。有時候,他的身體實在支撐不住了,就由兒子宗武歇了《文選》,代為稻粱謀。
冬日的陽光無精打采地灑在湘江上,江面的水波閃金爍銀。杜甫靠在那只岌岌可危的烏皮幾上,斑駁的陽光在眼前跳躍著,牽動著他的思緒。民間的疾苦、時代的艱虞、山川的秀麗以及自己“到處潛悲辛”的人生遭際,一幕幕、一遍遍在他的腦海了重復放映。他苦苦地思索著,莽莽乾坤,為何沒有自己的立錐之地?沉沉大地,為何自己無家可歸?老去功名草草,徒有詩文飛揚。一陣寒風襲來,老杜淚眼婆娑。
正當老杜老淚縱橫之際,一位不速之客來到他的船上,徑直來到他的烏皮幾旁。老杜悄悄抹去老淚,長眼望去,但見來者乃一位四十開外的男子,中等身材,矯健精悍,眉宇間有英氣。來客操山南巴州口音向老杜問候過,自道姓蘇名渙,乃潭州刺史幕府里的從事。
蘇渙這個名字和他先為俠盜后取功名的傳奇,杜甫多次聽人提到過,今日活脫脫出現在自己的面前,還是令他感到有些出人意表。他正要開口,卻被蘇渙搶過話頭:我仰慕工部大名已久,但在巴州卻是難以讀到您的詩作,直到最近在崔刺史幕府里才能夠如愿以償。“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雄心壯志;“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悲憫情懷;“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的真情呼喚,直擊我心,這是陶潛爾后三百年來難以聽到的聲音。今日得見工部,真叫人不敢相信,這些詩句就出自您的手筆。說完,拱手躬身,向杜甫深深拜揖。
聽著蘇渙的獨白,杜甫心里掠過一絲凄涼。然而,轉瞬就被蘇渙的一見如故、直白真誠所融化。寂寞無助之際,能遇見這樣一位奇人,也算是他鄉遇故知,幸甚至哉!貧病交加、垂垂老矣的杜甫,忽然感覺他與蘇渙的邂逅有點像司馬相如遇見了一百年以后的揚雄。送走蘇渙,他于暮色蒼茫中,情不自禁地提筆寫下這樣的詩句:“今晨清鏡中,白間生黑絲。余發喜卻變,勝食齋房芝”。
蘇渙的出現,猶如一道電光石火,在寒冷的冬夜,為杜甫帶來些許的明亮與溫暖,雖很短暫,卻讓杜甫心生力量與希望。日落西山之際,雙目昏花的杜甫,還仿佛能夠從岳麓山那邊的天空中,望見辰象粲然,而心生美好。
這天,惠風和暢,布谷聲聲,空氣里流淌著橘子花和忍冬花的香氣。杜甫從蘇渙的茅齋出來,腦子還沉浸在兩人無話不談的歡悅情境之中,臉上猶帶喜色,心里反復吟味著蘇渙讀給他聽的那些詩句。
剛到太平街口,一陣沙啞的歌聲從街口的人群中傳來,杜甫傾耳側聽,但聞:“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再細聽這歌聲,似曾相識,便不由自主地朝歌聲的人圈走過來。難道是他?老杜心里揣摩著,趕緊扒開人群擠了進去。但見: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坐在街心,手里拿著篳篥,身邊一架山桑木的羯鼓,一副黃檀鼓杖,鼓身斑駁,鼓杖光潤。篳篥之聲響起,渾厚蒼涼遼遠,白發老人渾濁空洞地望向北方。一曲終了,白發老人眼光落在老杜身上,他緩緩起身,走向老杜,兩雙筋骨暴露的老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歌圣與詩圣在漂流顛沛中重逢了!重逢在江南,重逢在落花時節。一個是“當時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一個是“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一個是“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饑寒趨路旁”的老歌手,一個是“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的老詩人。不盡的興亡夢幻,不盡的悲傷感嘆,直教四只老眼凄涼對江山。
杜甫和李龜年都曾生活在鼎盛的開元時代。那時的杜甫尚寄養在洛陽姑母的家中,身受洛陽文化的熏陶,盡管他還處在上樹摘梨打棗的年齡,詩文已然在洛陽嶄露頭角了。洛陽名士崔尚、魏啟心等都非常稱賞杜甫的詩作,常常說他的出現無異于班固、揚雄的再生。由于他們的援引,杜甫得以時常出入于精通音律的岐王李范與玄宗寵臣崔滌(人稱崔九)的邸宅。李、崔二人都是盛世大唐的文藝迷,王維、孟浩然、李白,還有王昌齡、高適都是他們的座上嘉賓,當然,年少的杜甫也是這里的常客。而作為唐玄宗的藝術知音、大唐歌王的李龜年,只要你能到岐王府、崔九堂,聽賞他的歌聲便是再尋常不過的事了。
一別四十年,杜甫與李龜年在湘江之濱不期而會,這場凄美的邂逅,絕不是偶然,是上蒼的著意安排。王維、李白、王昌齡、孟浩然、高適都死了,李范、崔滌也死了,是他們帶走了開元全盛的氣象嗎?未必。落花流水的風光中,兀然佇立的兩位形容憔悴的老人,以及他們滄海桑田般的歌聲與詩句,留給后人的解讀,正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后人還說:世運之治亂,年華之盛衰,彼此之凄涼流落,俱在其中。
杜甫寫下這篇《江南逢李龜年》后,再沒有寫七絕。他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寫出這般最富情韻、最富蘊含的絕句了。當然,他還知道,如果要寫一部由盛及衰的大唐回憶錄的話,是不妨用它來題卷的。確然,似這般言簡義豐而又營造出舉重若輕、渾然無跡的藝術境界,能與之比肩的絕句,少之又少。
一個荼蘼花香四溢的明月之夜,潭州城內忽然火光沖天,原來是兵馬使臧玠殺死潭州刺史崔瓘。杜甫不得不與潭州作別,在蘇渙的護持下,攜妻挈子南下衡州。其實,他這種顛沛完全出于下意識,乾坤萬里內,根本就沒有他這位疏布纏枯骨的白頭翁的容身之畔。放眼四海,生靈涂炭,“喪亂死多門”,悶熱的船篷里,老杜與妻子兒女空自悲嘆。夜晚,老杜仰望北斗,喟然長嘆:“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其實,老杜的北歸之心,不曾半刻迷糊。洪水阻止了他南下的行程,他仿佛覺得這是天意,是上蒼呼喚他北歸。于是,他與蘇渙別過,調棹北上。這次的北歸計劃似乎有點毅然決然,甚至有點不容置疑,因為老杜心里除了“故國莽丘墟”的牽懷以外,更多了一層落葉歸根的迫切——他的根在北方、在長安、在洛陽。然而,不知是湘江的有情還是無情,老杜自夏,經秋,至冬,他的那只破敗不堪的小舟,始終在湘江上漂浮著,直到天長地久。
正值隆冬時節,孤舟行到洞庭。兩年前,老杜在此留下“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的詩句。那時的他,登岳陽樓,望見的是“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的氣象,而今,他從船上看洞庭湖濱的景色,是空中的寒云、陰暗的白屋、濃霧般的瘴氣、蒙蒙的淫雨以及祭鬼的鼓聲、貓頭鷹被擊落的哀鳴,莫不帶著濃厚的愁慘的色彩,使得命懸一線的老杜病苦之情倍增其苦。他的手顫抖著,他的心也在顫抖著,他時而恍惚,時而清醒。清醒時,他對宗武說:軒轅黃帝制出的律管且把它收起來,虞舜彈過的五弦也撤下去吧!我已不再能演奏,變了調的琴聲將會傷透我半死的心。恍惚間,他最后一次回憶起那段短暫的左拾遺諫官生涯,因為盡職盡責疏救房琯而引起肅宗的不滿,從此與長安永別,漂泊西南天地間。巴蜀十年、湘楚三年的頻繁流浪中,雖然不時得陪錦帳之側,但多是貌合神離,因而不得不劬勞謀稻粱,結果是“哀傷同庾信,述作異陳琳”。他吃的是野菜羹,用的那張烏皮幾搖搖欲散,穿的衣服補丁疊補丁,但他與妻兒平心靜氣地說:“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他還曾對他的朋友說:“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
老杜似乎知道留給自己的時日已經不多,他伏身枕上,要對湖湘的親友作最后的道別。
他對親友們說,大歷三年春天出峽至江陵,本想從陸路北上,回京兆老家,但因種種原因而未能成行,只得南下,來尋覓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棲身之地,卻始終不得。在“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瘞夭追潘岳”的極端困苦的情況下,只好“持危覓鄧林”,投親靠友,仰仗親友們的幫助了。你們都具有慧眼能賞識像我這樣既愚且直的人,惟愿皇天后土能照臨我感激諸公的赤誠。
老杜深邃無光的眼眶里已經不再有淚水,他在枕上反側身體,拼盡最后的氣力,椎心泣血地哀鳴道,我衰病如此,定將像葛洪尸解那樣,必死無疑,現在已經無力像許靖那樣拖家帶口遠走安全之地;家事將像空有丹砂訣而煉不成金那樣難以維持,希望親友在我死后,能夠伸出援助之手,給家小以照顧。慈祥悲切之狀,催人潸然。不僅如此,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依然念念不忘國事,不忘生民。他不無抱憾地喟嘆道:“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藩鎮作亂,天下戰事不息,生靈涂炭,哀鴻遍野,宇宙何時能夠澄澈?這不禁讓人想起他曾立下的那句終身誓詞——“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他的關心朝政、關心生民的“傾太陽”的“物性”,可謂是至死不渝。范曾說,老杜的臨終絕筆,“是金劍沉埋、壯氣蒿萊的烈士歌”,“是大千慈悲、慕道沉痛的哀生賦”。斯言灼灼!
老杜伏枕寫就書懷三十六韻,渾身汗水涔涔,氣息若斷若續。他最后一次張望著船艙外的湘江,清絕的湘江籠在漫天大雪里,乾坤一派白茫茫。
(選自《安徽作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