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shí)間:2022-08-22 來源:安徽作家網(wǎng) 作者:安徽作家網(wǎng)
作家季宇的中篇小說《甲申疑案》原發(fā)《作家》2022年第7期,《長江文藝·好小說》2022年第8期頭條轉(zhuǎn)載,并刊發(fā)苑博先生的評論《打撈歷史碎片中“隱秘的經(jīng)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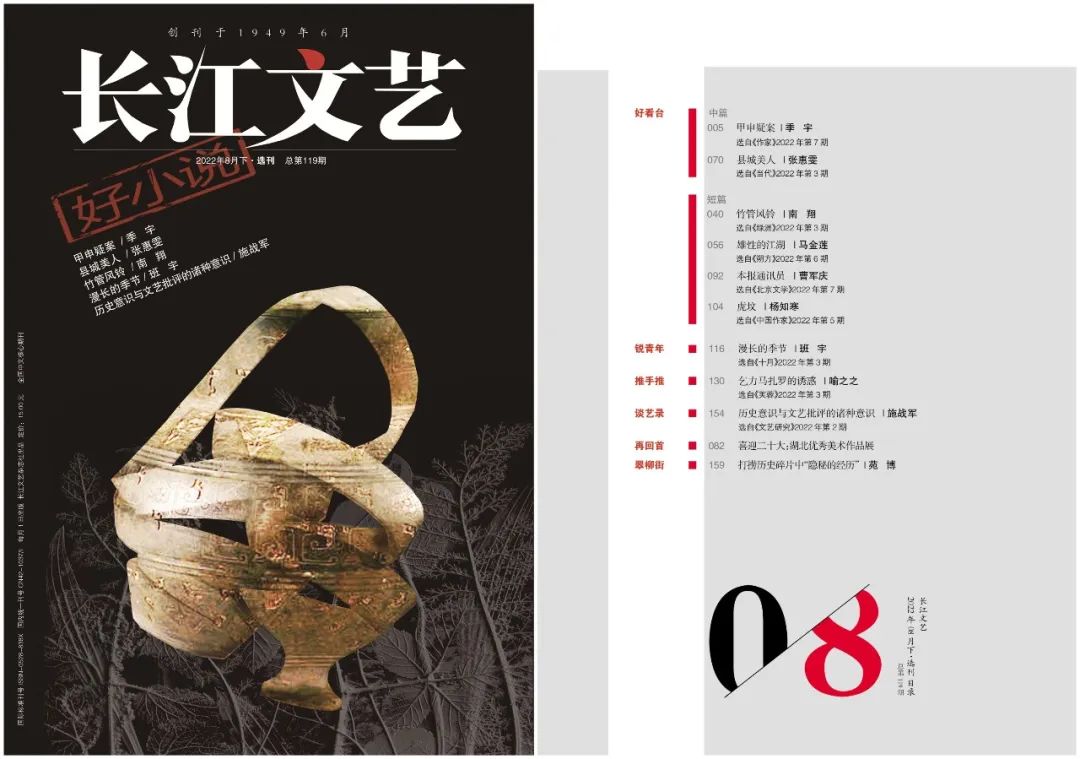
#
作品評論
打撈歷史碎片中“隱秘的經(jīng)歷”
苑 博
季宇是一個(gè)會講故事的作家,他的小說好看、耐讀。無論是寫歷史、諜戰(zhàn),還是寫軍旅、官場,他都能將情節(jié)設(shè)計(jì)得波瀾起伏、扣人心弦。然而,故事的傳奇性并非季宇小說的全部追求。正如他在一次訪談中所說,“傳奇的背后仍然是寫人性、寫人物的命運(yùn)以及他們在時(shí)代洪流中的浮沉”,季宇的小說同樣善于營造人物峰回路轉(zhuǎn)的命運(yùn),并借他們在困局中的遭遇與抉擇,燭照人性的浩瀚與幽微。
如果說在以《當(dāng)鋪》《盟友》為代表的早期中短篇小說里,季宇試圖呈現(xiàn)的人性之復(fù)雜更多地側(cè)重于其中惡的一面:父子相殘、兄弟相殺、人欲望的無限擴(kuò)張,那么,他最近一個(gè)時(shí)期創(chuàng)作的歷史小說,則更多地展現(xiàn)人物在“危機(jī)時(shí)刻”靈魂深處的震蕩、掙扎,以及此后的自贖、復(fù)生,從而顯露出愈發(fā)溫暖的底色。《最后的電波》里李安本因失誤暴露自己的身份,家人面臨日軍屠戮的危機(jī),新四軍派人通知李安本家人轉(zhuǎn)移,一名隊(duì)員在通知的過程中不慎遇難。在此之后,李安本一改先前“應(yīng)卯”的心態(tài),積極參與到新四軍的電報(bào)工作中。直到他彌留神志不清時(shí),仍能敲出熟悉的電報(bào):“東進(jìn),東進(jìn),我們是鐵的新四軍……”《救贖》里朱寶臣因自己的放蕩導(dǎo)致大哥被害,隨后開始漫長的救贖之旅,最后甚至不惜放棄自己的名節(jié)以保全大哥的孩子。《甲申疑案》里法方暗探綁架馮日升的孩子,以此要挾他向法方提供情報(bào),馮日升沒有屈從,而是以提供假情報(bào)的方式,為臺灣布防爭取了寶貴的時(shí)間……“義”是這些小說中最重要的精神內(nèi)核,它是季宇筆下人物行動的潛在動力,甚至成為了他們內(nèi)在的價(jià)值訴求與人生信念。這些小說所標(biāo)舉的,是以“義”為核心的傳統(tǒng)倫理價(jià)值,其中包括家本位的家庭倫理與家國天下的愛國情懷。正是這種以“義”為核心的傳統(tǒng)倫理價(jià)值,讓季宇的小說充滿著人情與人性之美,同時(shí)也構(gòu)成了季宇小說中最耐人尋味的內(nèi)涵。
歷史是一種敘述。并非所有發(fā)生過的事件都能寫進(jìn)歷史中,只有符合敘述者史觀的歷史事件,才能被寫進(jìn)特定的歷史敘述中。反過來說,總體性的歷史敘述,無法也無力呈現(xiàn)全部的歷史細(xì)節(jié),“被書寫的歷史”與“歷史真實(shí)”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距離。季宇的歷史小說揭示的正是這一點(diǎn)。在這些作品里,季宇沒有書寫帝王將相的豐功偉績,而是聚焦宏大歷史中隱而不彰的“失蹤者”,試圖發(fā)掘在語焉不詳?shù)臍v史敘述下那些“隱秘的經(jīng)歷”。《最后的電波》里李安本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幫助新四軍傳遞電報(bào),立下汗馬功勞,新中國成立后卻發(fā)現(xiàn)自己失去了曾幫助過新四軍的證據(jù)。直到李安本的暮年,他才與曾經(jīng)的戰(zhàn)友取得聯(lián)系,他在戰(zhàn)爭中的功績最終才得以“浮出歷史地表”。同樣,如果沒有那個(gè)不懈追尋的敘述者,《救贖》里朱寶臣佯裝附逆、卻暗中向新四軍傳送情報(bào)的經(jīng)歷,還有《甲申疑案》中馮日升與法方“暗通款曲”“事發(fā)下獄”的真實(shí)情況,恐怕都會永遠(yuǎn)埋藏在歷史中,他們將永遠(yuǎn)以一個(gè)模糊不清的可疑身影出現(xiàn)在歷史中。無論是李安本,還是朱寶臣、馮日升,他們的共同點(diǎn)是“信而見疑”:他們對國家、民族一片赤誠之心,但是由于歷史的誤會,他們又被看作敵人、叛徒、失節(jié)者。還好,在他們身后,終會有人撥開歷史的重重迷霧,向人們宣告他們的清白。在這里,我們似乎看到季宇用悲憫的目光,穿過文字與塵封的歷史,注視著我們并且作出承諾:是的,正義總會到來,沒有一份不凡的努力會被遺忘,沒有一種艱苦的生活會最終消逝在歷史中。
除了呈現(xiàn)歷史變局中人性幽微的精神主題,以及打撈歷史敘述中“隱匿者”的情節(jié)模式,《甲申疑案》首先進(jìn)入讀者閱讀視野、同時(shí)也是最令人擊節(jié)稱嘆的或許就是其講述故事的方式。小說沒有采用歷史小說通常的結(jié)構(gòu)方式,原原本本地交代故事發(fā)生的時(shí)空,繼而敘寫歷史經(jīng)緯中人物的行動、選擇與歸宿,而是選擇了碎片化的敘述模式。小說每節(jié)的標(biāo)題都對應(yīng)一個(gè)人物,每節(jié)都從某個(gè)側(cè)面講述完整故事的不同部分,敘述視角與敘述時(shí)空也不盡相同,小說從而呈現(xiàn)出“眾聲喧嘩”的狀貌。那么,作者為何采用這種方式講述故事?碎片化的敘述又給小說帶來了什么?事實(shí)上,在季宇的中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里,《甲申疑案》并不是第一篇采用如此結(jié)構(gòu)方式的作品。《金斗街八號》同樣圍繞人物結(jié)構(gòu)小說,在萬余言的篇幅內(nèi),閃轉(zhuǎn)騰挪出一場精彩的諜戰(zhàn)劇。關(guān)于《金斗街八號》在小說結(jié)構(gòu)上的探索,作者自己如此解釋:“這樣的結(jié)構(gòu)擠壓了情節(jié)的敘事空間,把更多的筆墨留給了人物,與此同時(shí),也節(jié)省了許多必要的交代情節(jié)的篇幅,使故事變得更加精煉。”碎片化的敘述策略在《甲申疑案》中所起到的效果亦可作如是觀。不過,《甲申疑案》的特殊之處在于,小說以打撈馮日升在1884年的生活作為敘述的動力,無形中呼應(yīng)了“尋找”這一古老的小說母題。由此,碎片化敘述給故事帶來的這種駁雜、繁復(fù)之感,實(shí)際上豐富了小說中敘述者尋找的過程,同時(shí)也增加了讀者的閱讀趣味,亦提升了小說理解的難度。小說敘述的碎片化還體現(xiàn)在對于歷史材料的直接呈現(xiàn)。好的歷史小說離不開扎實(shí)的史料與考據(jù)功夫,但大概很少有小說像《甲申疑案》一樣不厭其煩地饾饤那些冷僻的歷史知識。在《甲申疑案》中,光是引用到的史書典籍就有四種:《甲申紀(jì)事》《明清傳教士考略》《中法戰(zhàn)紀(jì)》《1884:我的回憶》。除此之外,小說里還出現(xiàn)了奏章、通信、報(bào)告、口述史料、回憶文章等不同形式的歷史材料。當(dāng)然,這些史料大多出自作者的虛構(gòu),但在小說自身的邏輯里,它們卻是確鑿無疑的“一手資料”。這樣一來,小說在虛構(gòu)與非虛構(gòu)、歷史與現(xiàn)實(shí)之間便找到了一條獨(dú)特的敘述路徑。順帶一提,《甲申疑案》里雖然出現(xiàn)了大量史書典籍與歷史材料,但作者并無意講述這些冷僻的歷史知識,歷史材料的出現(xiàn)也沒有帶來小說結(jié)構(gòu)上的松散。如果留心《甲申疑案》中敘述與史料之間的關(guān)系,不難發(fā)現(xiàn)小說里的歷史敘述看似有著一致的視角,但事實(shí)上每段敘述的視角都有輕微的差異,這是因?yàn)槊慷螖⑹龆紘?yán)格而巧妙地對應(yīng)著不同的歷史記載。這是作者匠心獨(dú)運(yùn)之所在。
從書寫人在困局中的心靈“掙扎”與“蝶變”,到打撈歷史中鮮為人知的傳奇經(jīng)歷,再到碎片化的歷史敘述,《甲申疑案》既延續(xù)著季宇一貫的精神主題與情節(jié)模式,同時(shí)也體現(xiàn)出他對中短篇小說寫作新的探索。其在敘述方式上的嘗試,或可為當(dāng)下的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提供鏡鑒與參考。
(原載《長江文藝.好小說》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