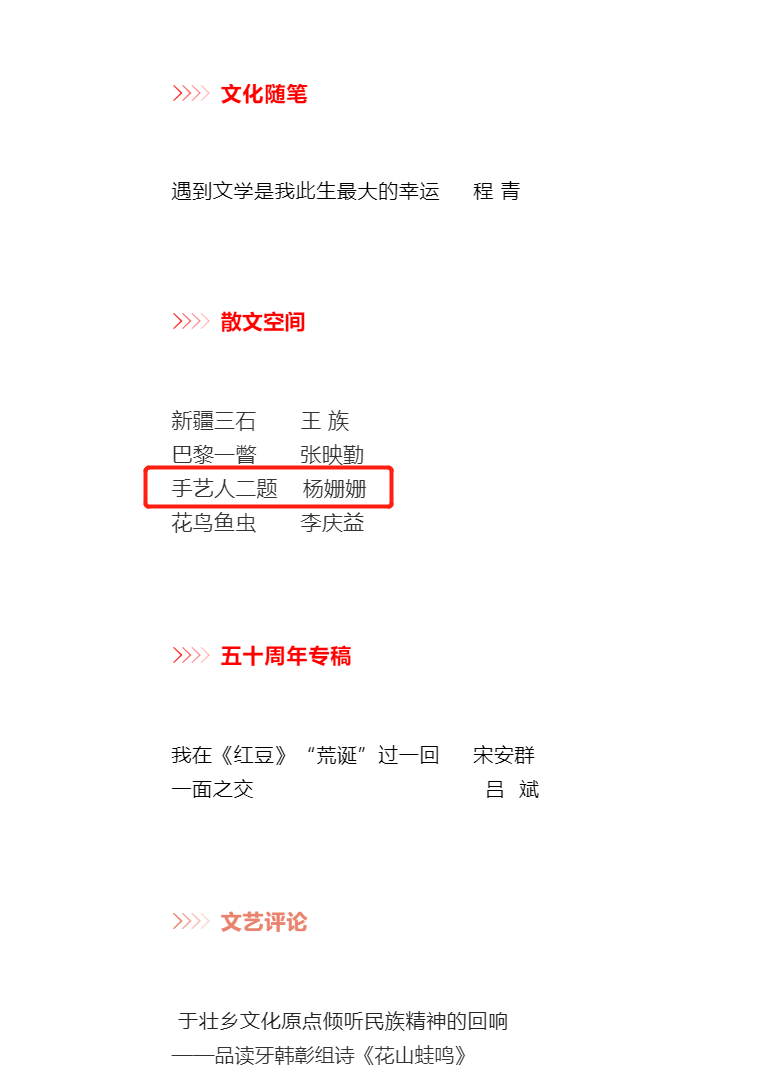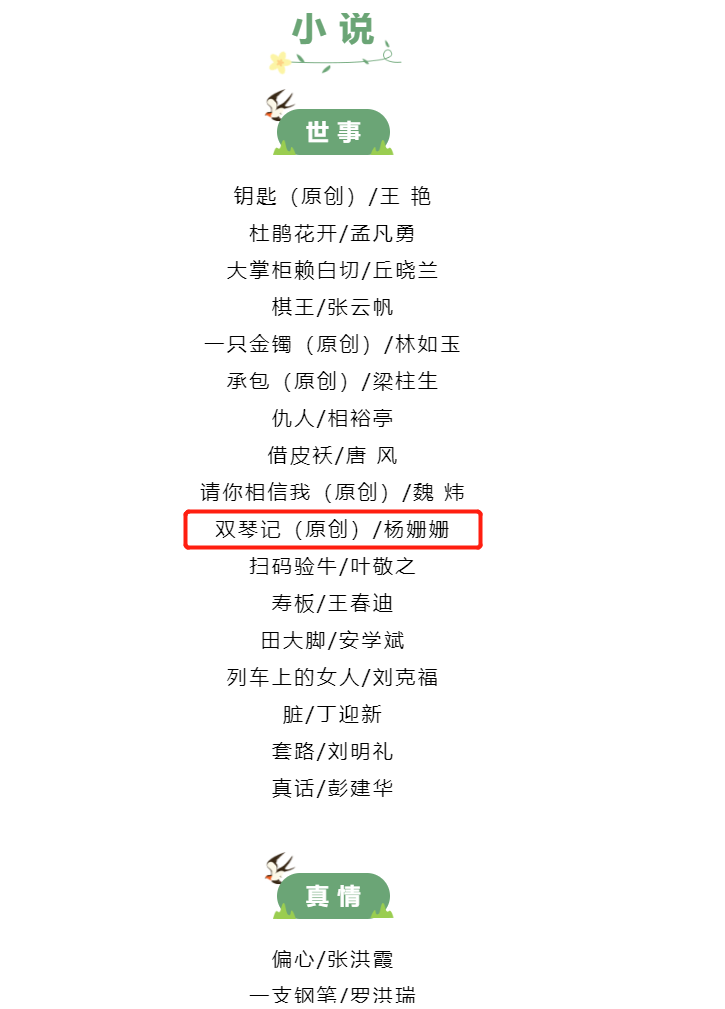日前,作家楊姍姍散文《手藝人二題》刊發《紅豆》2022年第6期;小說《雙琴記》刊發《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22年第3期。
作品欣賞
雙琴記(節選)
楊姍姍
赴揚州之前,舒巖收到了“春天邀約——天音、地韻九華合璧雅集”的請柬。無巧不巧,他還沒來得及把消息告知金友友,他已然向舒巖發出了揚州之約。
舒巖和金友友既是發小,又是揚州大學的同窗。他倆學的古琴專業,畢業后金友友留在揚州發展,舒巖則回到家鄉,在k鎮開了一家音樂作坊。
K鎮坐落于風景秀麗的九華山地區,在這一帶的古琴音樂界,舒巖早已小有名聲。這一趟揚州之行,金友友約他參加一場“天音琴”的賞聽音樂會。兩人匯合后,便一起前往位于剪刀巷的梅曰強先生故居。梅先生生前是古琴界的泰斗級人物,傳承了三百多年古琴廣陵派的第十一代宗師,富有傳奇色彩的“天音”琴即是出自于他的手。
在古琴賞聽會上,大師們的古琴技藝令人大開眼界嘆為觀止,而讓舒巖更為意外的驚喜,卻是讓他曾有一面之緣且讓他記憶深刻的不速之客——姚淼淼。
那是在三年前的隆冬,金友友回鄉過春節。因為各種忙碌,金友友直到陰歷二十九的傍晚,才一腳跨入家門。但凡小城鄉鎮村落,傳統鄉土文化的規矩比大城市里反而更講究,按照老家的習俗,大年三十和初一必須在家待著,家人一起守歲辭舊迎新,吃年夜飯包餃子,燃放開門炮,諸此種種。憋到年初二下午,舒巖和金友友才終于見了面。
舒巖的音樂作坊在K鎮中心的商業街上,因為春節期間做生意的人都紛紛回家了,本地人也囿于傳統基本上在家關門團聚,平時熱鬧的街上冷冷清清。從臘月里的最后幾日開始,繁華的市面漸漸人去樓空,空曠的商業大街上只有舒巖的音樂作坊敞著卷閘門,廊檐下一對紅燈籠在寂寥的夜晚透著一縷溫馨的暖色,給小鎮增添了一絲生氣。
年初二大清早,天空風輕云薄,陽光燦爛,然而快到中午時氣候突變,北風勁吹,直接把天上的云吹得發皺,一層疊著一層,厚厚的黑云扣在天上像濃得化不開的墨斗。舒巖的工作室氣氛昂然,他在廚房里一頓手忙腳亂地操作,端上一個燒炭火的銅火鍋,滋滋地冒著熱氣,一碟碟羊肉牛肉肥腸鴨血豆腐粉絲齊刷刷擺滿了桌子。金友友樂得笑歪了嘴,因為盤盤碟碟里全是自己愛吃的東西。
這時有零零星星的炮竹聲傳來,想必是哪家的孩子竄到雪地里玩耍吧。雪越下越大,天地連成了一片,白皚皚雪茫茫映襯著一個銀亮的夜晚。
舒巖鉆到書櫥后面,變魔術般的拎出一個棕色禮品袋,神神秘秘從袋子里拿出一瓶酒,故意在金友友面前晃了一下。金友友實在沒想到舒巖這個悶葫蘆居然還私藏有蘭溪老窖!自從這家K鎮最老字號的酒坊多年前經營不善倒閉關門,金友友就再也沒有喝到過比蘭溪老窖更讓他既熱血賁張又愁腸百結的烈性酒了。遠在異鄉的時候,除了最想老媽燒的家鄉菜,就是蘭溪老窖,那真正是連接鄉愁記憶的紐帶啊。金友友每當喝到,不,后來是每當想到蘭溪老窖時,都會產生一種想要狂野彈琴的藝術沖動……好曲要有好酒配,舒巖給金友友和自己都滿了上一杯。
手機叮咚一聲,屏幕彈出一條短信:因突降大雪,唯一經過K鎮的一列高鐵臨時停運,何時恢復運輸,請大家耐心等待上級通知……舒巖扭頭,說你收到短信了嗎,高鐵停了。金友友坐在古琴前,一杯蘭溪老窖使得人目光發亮,他揚揚眉毛有點不懷好意地說,那就讓暴風雪來得更猛烈些吧!對了,你想聽什么曲子?
風雪漫天的寒夜, 舒巖和金友友吃著火鍋,喝著老酒,琴聲在古鎮的雪夜余音裊裊,如縷縷花香拂過人心,點點星光滲入思緒,絲絲蟲鳴飄進腦海。
叮咚叮咚,門鈴響了。
金友友正在撥弦的手順勢停下,輕輕蓋在弦上。舒巖放下酒杯,嘟囔了一句:“這大冷的天,是誰敲門啊?”
那個漫天大雪的年初二夜晚,舒巖音樂作坊的門被一名不速之客敲響。
門外站著一個雪人,渾身上下冒著寒氣。這個陌生人的裝束很奇怪,上衣是一件中式棉袍,下面穿了一條牛仔褲,腳上是雙旅游鞋,他背了雙肩包,一只手扶著一個半人高的長方形紙箱。
舒巖盯著那個紙箱看了看,頭腦里閃過一個問號,這個天居然還有送快遞的?
沒等舒巖開口,陌生人說話了,真不好意思,打擾你們。我從揚州來在K鎮下車,要去離這里幾十公里的書畫藝術研究院找一個朋友,大雪天沒有出租車,我走了好幾條街,酒店飯店也基本都打烊了。陌生人用勁眨了眨眼睛,融化的雪水在睫毛那里形成了一個個小水珠,眼影一樣顯得眼睛很大,也很疲憊。他繼續說,迷茫中,隱隱約約的古琴聲在風中時隱時現,我被琴聲吸引著來到你們這里,我……我想是緣分吧。
金友友打量著他,又朝門外看了一眼,就你自己嗎?
陌生人搓了搓手,是的,就我自己。他有點不好意思笑了一下,朋友,我可以進去尋口熱水喝嗎?
這家伙是個自來熟,爽快人!舒巖素來古道熱腸。金友友這樣評價他:俠客心腸和浪漫情懷兼具,恰比古琴之散音和泛音。實際上,金友友和他每每狼狽為奸,都是一對只恨熱鬧不夠的貨色。更何況,對方提到了古琴!
舒巖不假思索就把陌生人讓進門,別說高鐵停運了,現在大過年的,你到我家來就是我的客人呢!
金友友彎腰拿起陌生人帶來的長紙箱,準備放在墻角立著。陌生人見狀趕緊說,我來、我來,不用麻煩。他將紙箱小心翼翼擺平放在地上,左右端詳,又不放心地往里面推一推。舒巖和金友友疑惑地對瞅一眼,不知道里面藏著什么寶貝。陌生人歉意地歉了歉身,解釋道:這個紙箱子里面是一把來歷不同尋常的古琴。
舒巖一下釋然,心想,怪不得箱子這么長!不得不承認,琴以載道,琴以會友,這把古琴一下子拉近了舒巖、金友友和陌生人——姚淼淼之間的距離。
同時,舒巖的心里也對長紙箱里的古琴,遽然升起了極大的好奇心。
那個夜晚,三個人在音樂作坊對酒當歌,撫琴暢談,其中要數姚淼淼最健談。三個古琴愛好者湊在一起,話題自然繞不開古琴。
我們喜歡古琴的人都知道 ,姚淼淼咂了一口酒,放下酒杯的時候順勢掠了一下頭發才接著說,古琴又稱瑤琴、玉琴、七弦琴——傳說舜定琴為五弦,文王增一弦,武王伐紂又增一弦,是為七弦琴,可見古琴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接著又飲了一杯酒,指著他帶來的那把古琴,很神秘地對舒巖和金友友說,這把古琴身世很有來頭,然后姚淼淼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個當地流傳很廣的一則民間故事。
K鎮地處九華,這里流傳的很多故事都跟地藏王有關。在唐朝開元七年、或者八年間,未來的地藏菩薩金喬覺從韓國航海過來,他修行時住在山洞里,所以大家也管他叫洞僧。據說當時有兩位居士姊妹很照顧他,每天給他送飯,一天一餐,天天如此,從不間斷。
有一次,姊妹倆送飯趕上了雨天。雨下得突然,沒有預兆。上山的時候還是晴天,可是下山時風云突變,雷閃電鳴,暴風驟雨,溪水上漲,兩姐妹不慎被咆哮翻騰著的山洪沖走,萬幸的是又被溪邊一棵紅柳樹給擋住了。洪水退去后,當地老百姓在大紅柳下發現她倆,兩人都已經沒有生命氣息,安詳地臥在樹下。大家驚訝極了,山洪暴發宛若野馬狂奔,人落到水中轉眼就會沖得無影無蹤,而她們姐妹卻被紅柳樹留住了。姊妹倆在當地本來就有人緣,村民開始自發地祭奠她們,那棵紅柳也被附于想象力地奉為了神樹。天長日久故事流傳越來越廣,人們在成為了社樹的紅柳旁建起了土地廟,從四面八方趕來虔誠地祭奠、祈禱。在鄉村,一棵樹演變成了社樹那是可了不得的大事,敬重社神首先就要敬重社樹,社樹上的鳥窩不能掏,枝丫不能砍。就連枯枝也不能撿回家做柴火
在本地長大的舒巖,早就就聽過這個傳說,而且在故事流傳的過程中,還有細節更加豐富的版本。他自己就能把這個故事講下去——很多年后,有一次山上發生地質災害,浩浩蕩蕩的泥石流把這棵社樹和土地廟給沖掉了。紅柳順流而下,住在溪邊老田里的一戶吳姓人家把紅柳樹打撈上來,晾干后修鋸整飭一番,這棵曾經的社樹便化身成為了一塊神木。吳家人將神木放在家里,以后一代一代地供了起來。
舒巖還曉得,現在每年K鎮都舉辦的祭奠舞龍的民俗活動,其實最初就是源于紀念那兩姐妹的傳說。
活在當代,舒巖對許多民間文化具有自己包容性的認識,反正是故事嘛,信與不信倒還是其次。不過今天這個“琴趣”盎然的夜晚,他可不愿意浪費在這老調重彈的傳說上。舒巖又倒滿一杯酒遞過去,準備打斷姚淼淼興致勃勃的敘述,可也就是這時,他聽到后者的嘴里蹦出了三個字:地韻琴。舒巖一驚,在記憶中,這個琴好像曾經在哪里見過、或者聽人說起過。
……
作者簡介
楊姍姍,生于寧波,現居合肥。有長篇小說《花還能這樣開》、中篇小說《心事重重》、短篇小說《跨年》《雙琴記》、非虛構《弦音如許》、散文《秋色斑斕》、《手藝人二題》(另題:散落街頭的匠人)等作品發表于《莽原》《飛天》《湖南文學》《天津文學》《安徽文學》《傳奇·傳記文學選刊》《紅豆》等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