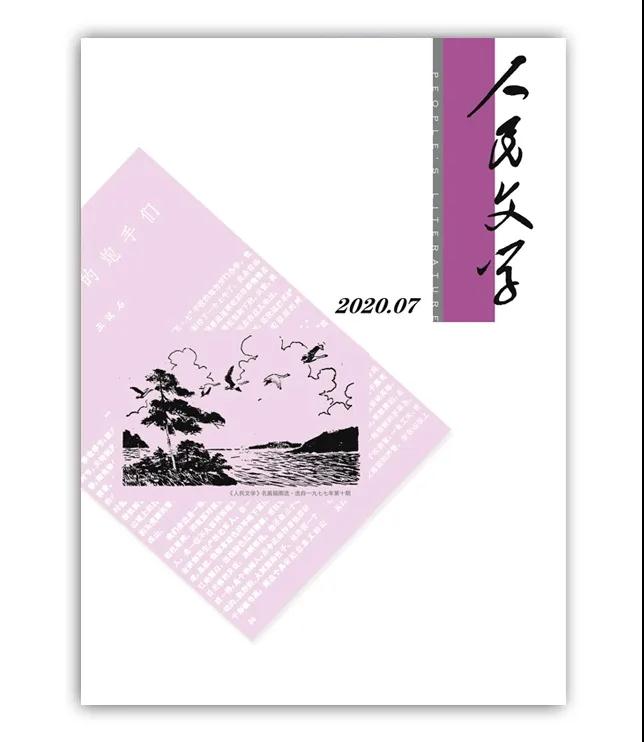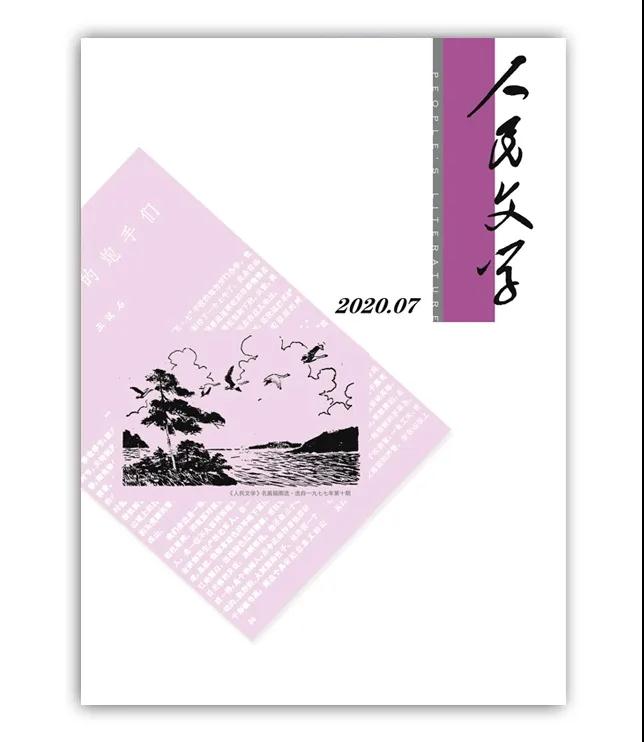
晴朗的夜空為什么滴下露珠
——大別山扶貧散記
(節選)
潘小平
一
1
現在,我就坐在他的對面。
是2019年11月20日上午,9點來鐘,風靜的一刻,大別山冬日的陽光,甚至有些耀眼。
這里是金寨縣雙河鎮河西行政村,小河口村民組。76歲的馮紀耐沉默地坐著,右目深陷。
這只右眼,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失明了,“是因為生病嗎?”我問。
他搖了搖頭,沒有回答,似乎是不想觸及這個話題。他用手指了指對面的山坡,說:喏,就在那面坡上,就在那邊哩。
他指給我看的,是他養父的墳墓,年年清明,他都帶著他的兒孫,去到養父的墳上添土。一年一年添下來,墳頭已經很高了,在林木茂盛的夏季,沒膝的蒿草,完全把碑上的字跡掩蓋。
“我看得見哩,”老人擦了擦深陷的眼窩,有些賭氣地說:“我看得見!”
我瞇起眼睛,看了一眼對面的山坡,冬季的大別山草木凋零,一片衰白。大別山群峰巍峨,雄踞淮甸,綿延數百里,雖座落于鄂豫皖三省交界處,但大部分是在安徽境內。大別山主峰白馬尖海拔1777米,東視南京,西隔武漢,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是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八軍的誕生地,我國著名的革命老區之一,也是一個集老區、山區、庫區于一體的國家級貧困區。
馮紀耐是有“紅色背景”的貧困戶,2016年脫貧。在金寨,我收集并記錄在冊的有“紅色背景”的貧困戶一共是158戶,而實際數字,要遠遠大于這個。
所謂“紅色背景”,是指他們的父兄,在革命戰爭年代,付出了生命。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金寨境內先后爆發了著名的立夏節起義和六霍起義,組建了12支主力紅軍隊伍,曾有10萬子弟參加紅軍。他們有的活到了革命勝利的那一天,有的成為共和國的將軍,而更多的人死在了革命的路上,他們沒有留下后代,他們甚至沒有留下姓名。而他們的后人,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內,都仍然生活在貧困之中。
這個名叫“西山”的小村子,坐落在大別山深處,周遭群山環繞。這是一片紅色的土地,早在1928年春,中共雙河特支就在雙河鎮大廟成立,特支書記馮玉璽,和馮紀耐同屬于當地的馮氏家族。
“馮”是當地的大姓,在“鬧紅”的年月里,有很多馮氏子弟參加了紅軍。馮紀耐的養父馮倫奎,1930年3月參軍,1932年冬隨紅四方面軍進入四川,從此杳無音信。
馮倫奎走的那一年,才十六七歲,還沒有成親。不過婚事是早已訂下來的,女方是雙河西南十多公里南溪鎮人,名叫黃守群。打響大別山土地革命第一槍的“立夏節起義”,就發生在南溪鎮丁家埠大王廟。南溪也是著名“左聯”詩人蔣光慈早年開展革命活動的地方,1924年夏,蔣光慈從蘇聯回國后不久,就從老家白塔畈來到南溪鎮,發展他的小學老師詹谷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馮倫奎走后不久,黃守群就來到了馮家,雖然沒有和男人拜堂成親,但她作為馮家媳婦的名分,是早已定下來的。按照大別山的婚俗,她從娘家出門時,腋下挾了一捆干柴,名為“抱柴”,寓意給夫家帶來“財”氣。“晚拜堂”時,也就她一個人,在靜悄悄的午夜里,由幾位族中的長輩主持。她對著大門一拜天地,二拜祖宗牌位,最后象征性地完成了“夫妻對拜”,成為馮黃氏。
她沒有覺得委屈,很多人家的子弟,都跟著紅軍走了,很多人家娶回來的媳婦,也都和她一樣,是自己和自己拜堂。她才十五六歲,正是花開一樣的年紀,還不知道世事的艱難,也無法預料她一個人的日子,會有多長。
可那時候的黃守群,是多么鮮亮,多么活泛啊,細細的腰肢,黑亮亮的頭發,砍柴,喂豬,一日三餐,伺候公婆,從清晨一直忙到晚上。一個人在山上干活的時候,她會直起腰來,眺望遠處的大山,大山重重迭迭,一直鋪到天際,她想她男人馮倫奎,也不知長什么樣子?現在,又在什么地方?
而家里的日子,是越來越讓人提心吊膽了,白狗子時常闖進村來,抓走紅軍家屬,將他們關進“難民所”。當時僅在雙河方圓不到10里地內,就設了兩個“難民所”,一個是雙河鎮雙河街上的“大廟難民所”,一個是雙河鎮鶴塘村的“白墳子難民所”,專門用來關押紅軍家屬。民團頭子顧敬之,每到一處就大喊大叫,說是要開“人肉寨子”,在湯家匯周圍百十里地范圍內,包括雙河地區,被他用鍘刀鍘死的蘇維埃干部和紅軍家屬,就有一萬多人。
死人的事情天天發生,有些就是馮氏家族的人。共產黨員馮長泰父子倆,被民團抓去了,黃龍附近兩個小莊子,也有13個蘇維埃干部被砍了頭。尸體就扔在河灘上,沒人敢去收尸,公婆一家神色驚慌,膽戰心驚。那時的黃守群,還不懂啥叫“白色恐怖”,也不知道啥叫“革命”,她只知道自打紅軍走了以后,婆家的日子是越來越難了,不僅忍饑挨餓,還要時刻提防著白狗子上門。
1932年紅四方軍戰略轉移以后,蔣介石下令“清剿”留下的紅軍和游擊隊,雙河鎮土豪劣紳馮國梁隨即組織了保安隊,自任民團大隊長。長相俊俏的蘇區婦女干部陸化明,關押期間被馮國梁所看中,馮國梁就將她丈夫史家懷抓去殺害了,強占她做了二房。當時還鄉團提出的口號是:“駐盡山頭,宰盡豬牛,見黑(人影)就打,雞犬不留”。據不完全記載,在紅軍走后的3個月里,衛立煌部、蔣優生第83師等國民黨軍,槍殺和活埋了3500多名蘇區干部與紅軍家屬,為此,他們在金寨挖了一個5里多長的大坑,專門用來掩埋尸體。
機槍掃射、活埋、剜心、挖眼、剝皮、穿鼻子、五馬分尸等等,已經不算什么,更慘絕人寰的還有戴紅帽、穿紅鞋、掛畫等等刑法。“戴紅帽”是將鐵桶燒紅了套在頭上,“穿紅鞋”是將犁鏵燒紅了套在腳上,而“掛畫”是把人殺死以后,將頭領和四肢釘在門板上示眾。
外面發生的一切,黃守群不敢聽,更不敢去看,她常常半夜爬起來,一個人站在門外,對著遠處的大山一遍遍問:大奎子啊大奎子,你到底在哪兒呢?
松濤陣陣,夜色海一樣深。
2
終于得到馮倫奎的消息,已是1980年的秋季。
這一天,有人跑來告訴馮倫奎的大哥馮倫升:你知道嗎?雙河街上的林團長還活著,在江西呢,當了大官了!
林團長指的是林乃清,馮倫奎當年,就是和他一起走的。馮紀耐一聽,猛地站起身來,拔腿就往雙河街的方向跑,他身后緊跟著的,是他顫顫巍巍的嬸娘黃守群。
查百度百科、開國將軍和六安黨史,均有“林乃清”詞條,而在金寨縣當代人物專題中,則有他更為詳細的資料。1916年,林乃清出生于金寨縣雙河鎮雙河街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30 年3 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秋,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后,林乃清隨紅四方面軍向西戰略轉移,西進川陜的途中,參加了棗陽、新集、土橋鋪、子午鎮等一系列重要戰役。
雖然我們無法知道馮倫奎的情況,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時期的馮倫奎,一直和林乃清在一起。但我們無法知道馮倫奎走出大別山后,到過什么地方,打過什么仗,有過什么經歷。1936年4月,林乃清所在的紅四方面軍,第三次走過了草地,這時候的馮倫奎,很可能已經犧牲。
多年以后,我坐在大別山深處,一個名叫“西山”的小山村里,展開一封林乃清從江西寄出的信。薄薄的兩頁紙,字跡已經模糊,使用的是繁體字,信中稱馮紀耐為“紀鼐”,這應該是他在族譜里的名字。
紀鼐:
來信收悉。你好,全家好,今年農業收成還好嗎?
關于馮倫魁同志的事,是這樣的。
一九三二年冬季紅四方面軍進入四川之后,打了德勝山戰役后,部隊整訓之機,我到紅卅十軍軍部開會,碰見了他的。那時倫魁同志在三十軍政治部任組織部長的工作。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五年,四方面軍回合之后,到四方面軍第二次過雪山草地進入甘南地區戰斗,到紅四方面軍又組織一部過黃河西進之后,由軍政治部調到三十軍九十師二五七團任政委時,與敵作戰犧牲的。時間是一九三六年一、二月份,在甘肅倪家銀子戰斗中犧牲的……
內容十分簡短,而且有很多地方語焉不詳。馮紀耐很小心地取走那兩頁紙,很小心地折好,很小心地把它裝進信封。信封也已經很舊很脆了,從1980年秋季,收到它的那一天起,它就被無數次地打開,無數次地折起。在漫長的39年光陰里,它眼看著身邊的這個男人,從青壯走進了暮年,由青絲變成了白發,但每一次取出它時,都是那樣的小心翼翼。
即便是一張紙,它也感到了疼痛。
回到招待所,我立即上網搜索“德勝山戰役”和甘南“倪家銀子”戰斗,沒有任何線索。“倪家銀子”也許是“倪家郢子”的誤記,那一路上紅四方面軍打過很多仗,經歷了大大小小無數次戰役或戰斗,這兩個地名,早已淹沒在了歷史的煙塵里。1936 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以后,遵照中央軍委的命令,林乃清所在的紅四方面軍紅三十軍、紅九軍、紅五軍和直屬騎兵師、特務團、教導團、婦女獨立團等21800多人西渡黃河,改稱西路軍。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孤軍作戰,彈盡糧絕,伏尸盈雪,但林乃清活著走了出來。新中國建立以后,林乃清進入南京軍事學院學習,1955 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授銜時,林乃清被授予大校軍銜,1964年,晉升為少將軍銜。
給馮紀耐寫回信的時候,林乃清剛從江西省軍區副司令員任上退下來,轉任江西省軍區顧問,那一年,他也是一個64歲的老人了!
太陽一點點升高,鋪滿了整個山谷,馮家屋檐下吊著的大南瓜橙亮亮的,像是一個大燈籠。馮家的小院收拾得干干凈凈,屋前的老樹都落盡了葉子,很蒼勁的樣子。是板栗樹,一種高大的落葉喬木。板栗是金寨縣的傳統產業,栽培歷史可追溯到清代同治年間,直到今天,梅山鎮船沖、徐沖、白塔畈一帶的許多村莊里,仍分布有成片的老栗子園。馮家門前的這片板栗,是1988年縣里大力發展山場經濟后種下的, 也是一項重要的家庭收入。據2013年公布的數字,金寨縣現有板栗50萬畝,共1800多萬株,年創產值在億元以上,產量位居全國第一。
陽光照進堂屋,光燦燦暖洋洋一片,我起身進屋。是三間大瓦房,坐北朝南,傳統江淮民居式樣,能看出房子新裝修不久。原來為了迎接新中國建立70周年,縣里為烈軍屬家庭撥了一筆專款,為他們的住房統一做了粉刷和整修。雪白的墻上,貼著國家領導人的畫像,和城市裝修一樣,地上鋪著瓷磚,頂上吊著天花板。有彩電、洗衣機,還有電飯鍋、電磁爐等等家用電器。陳設很簡單,但寬敞整潔,窗明幾凈。
“怎么沒有冰箱啊?”我問。
“咳!冰箱擱咱這兒沒啥用,山里早晚,涼快得很!”老人解釋說,“就是洗衣機,我也不大會用,可家家都有,咱不也得置辦一個嗎?”
2008年以后,中國農村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是家用電器齊全。2008年爆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國沿海大批企業倒閉,大約有2500萬農民工從城市轉回來。西方的經濟學家,重彈“中國經濟崩潰論”的老調,但中國成功地化解了這場危機,而農村家庭家用電器的普及,就和這場大危機有關。
我們都知道,中國以前的出口退稅13%,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中國政府拿出13%的財政補貼,給了海外的消費者。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外貿出不去了,彩電、冰箱、洗衣機、汽車全都壓在了庫里。怎么解決呢?中央拿這13%的出口退稅,鼓勵農民買家用電器,只要是農村戶口,立刻就可享受13%的價格折扣,而且這一優惠政策,只實施到2010年底!這一來,大大刺激了廣大農村的購買力,結果是中國農村每百戶彩電擁有率,高達104臺!也正是依靠農民龐大的購買力,我們成功地化解了這場經濟危機。
馮家的廚房收拾得很干凈,桌是桌,凳是凳,瓢是瓢,鍋是鍋。灶臺上方的橫梁上,吊著一個小飯籃,里面是一碗鍋巴,上面罩著一塊洗得雪白的紗布。
山里人吃飯,喜歡把鍋巴留下來,放到竹籃里晾干,以備不時之需。這是兵荒馬亂的年月,留下的生活痕跡。19世紀以來,中國大地戰爭、饑荒、離亂、瘟疫不斷,人民饑寒交迫,顛沛流離。“跑反”和逃荒的路上,鍋巴是最便于保存和攜帶的食物,汪曾祺在他的小說中,對此曾有過類似的描述。
我小的時候,常聽我奶奶說:出門看你頭和腳,進門看你瓢和鍋!這是說看一戶人家日子過得怎么樣,女人勤快不勤快,有沒有奔日子的心勁,看這幾樣就知道了。馮紀耐雖說死了老伴,孩子們也不在跟前,但里里外外,收拾得很干凈,從這一點上看,他過日子的心勁很足。
馮家是2016年摘掉的貧困戶帽子,老人說現在的日子,雖說不敢和你們城里人比,但吃穿不愁,有酒有肉,身上穿的,頭上戴的,都是兒子們從山外的大商場里買來的,可不便宜呢!
馮紀耐的大兒子在江蘇盛澤工作,小兒子在省城合肥工作,平常日子也不大回來,但每年的清明和春節,是一定要回來的,也不單單是為了團圓,還要帶上他們,到他爺爺的墳上去添土。
對面的山坡上,亮晃晃的一片,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了。隔著十幾里的距離,我無法判斷馮倫奎的墳墓在哪里,我想就是馮紀耐自己,也未必看得到。那座墓立于1980年冬季,接到林乃清來信后不久。原先的一切希望,一切幻想,都破滅了,馮倫奎他死在了外面,死在了甘南一個名叫“倪家銀子”的地方,他再也回不來了!
黃守群把自己關進屋里,不吃不喝,哭了一天一夜,她不知道老天爺為什么要和她過不去,難道她守了48年,等來的就是這個?她想不通,也不甘心,她一個勁地掉眼淚,怎么也止不住。一家人都沉默著,不知道該怎么勸,過了好一會兒,大哥馮倫升才悶聲道:不是還有紀耐呢嗎?讓紀耐給你當兒子,給他二叔頂承香火!
聽了這句話,黃守群的心里,好受多了。
大別山的規矩,一個成年男子,是不能沒有“后”的,不管你活著時過得咋樣,死時都不能沒有人給你“摔老盆”,不能沒有人在你的墳上燒紙添土。現在好了,現在馮倫奎有“后”了,接下來要辦的一件事,是為他滴血立牌,招魂入墓。
3
雙河馮氏的宗族排序,是“仁浦德澤常,倫紀克登文”,按照這個譜序,馮紀耐“寫”給馮倫奎,承繼他的香火。現在,雙河馮氏的宗譜中,在馮倫奎的名字下面,就寫著“馮紀耐”三個字:“也算對得起他了!”
這是大事,由族中有名望的長輩主持,先立過繼文書,然后向著養父死去的方向跪拜,再接下來,是在對面的山坡上選一塊墓地,豎上牌位,寫上“先父馮倫奎之墓”幾個字。沒有骸骨,也沒有衣冠,十六七歲出門,馮倫奎沒有給家里人,留下任何一點念想。好在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刺破繼子馮紀耐的中指,把指上的一滴血,滴在牌位上。這樣,馮倫奎的在天之靈就會知道,他不再是孤魂野鬼,他有了“后”了!
俯在墳前的黃守群,號啕大哭。
一開始,我希望縣“扶貧辦”的同志,為我提供的有“紅色背景”的貧困戶,是“親子”關系而不是“繼子”關系,他們很是為難,說有是有,但很難找到。我感到不好理解,戰爭年代犧牲了那么多的人,難道他們的后代,都找不到了嗎?那時我還不知道,他們根本就沒有后代,他們犧牲的時候,太年輕了!他們死在爬雪山過草地的路上,或是炮火紛飛的戰場,他們只能通過“滴血”的方式,由他們的繼子為他們“招魂入墓”。唐代張籍有《征婦怨》詩:“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在大別山區,有多少農家子弟參加了紅軍?有多少人沒能活著回來?有多少人的死訊,是在他們死去幾十年后,他們的家人才知道?又有多少人是通過“滴血入墓”的“招魂葬”, 最終才魂歸故鄉?
沒有人知道。
為養父馮倫奎“招魂入墓”,是在1980年的冬天,那一年馮紀耐37歲,已經結婚生子,大兒子馮克強,也已經上小學了。雖然山外的人家給孩子起名,已不再按照家族譜序,但金寨雙河的馮姓人家,仍然嚴格按照“仁浦德澤常,倫紀克登文”的排序,給孩子起名字。漫天大雪,下了一天一夜,山山嶺嶺,溝溝壑壑,全都被大雪覆蓋了。馮紀耐拉著兒子馮克強,一步一滑地來到墳前,天地白茫茫一片,肅穆極了。
“跪下,跪下!”
馮紀耐把大兒子馮克強,摁在了墳前的雪地上:“給你爺爺磕頭!”
又21年,2001年,馮紀耐的養母黃守群去世,她走的時候很安詳。她一輩子沒出馮家的門,從青春年少到垂垂老嫗,80多年的時光。
在她去世后的第3年,2004年年初,雙河鎮政府出資修建了雙河烈士紀念園,園區座落在雙河鎮九龍村洪灣村民組,210省道東側。規模不大,占地20畝,但松柏常青,綠水環繞。在這座紀念園里,長眠著為建立新中國英勇獻身的烈士1500多名,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620名,無名無姓的烈士900多名,馮倫奎的墓碑也在里頭。
立碑的時候,鎮里具體負責的干部,希望馮紀耐能提供一張他養父的照片,馮紀耐想了想,把他四叔的照片交了上去。養父馮倫奎生前沒有留下照片,那時候山里窮,窮人家的孩子,有誰照過相?長征的路上腥風血雨,就更不可能有照片留下來了。四叔也是長臉,面容清瘦,和養父馮倫奎長得十分相像。現在他們再掃墓的時候,都是去洪灣村的烈士紀念園,但清明前后,馮紀耐還是一個人到山上去,在養父“招魂入墓”的墳前,坐上半天。
馮紀耐養的一條小狗,名叫“花花”,總在我腳前轉來轉去,一群小土雞嘰嘰喳喳,一會兒跑過來,一會兒又跑過去了。不多,也就20來只,5元錢一只的小雞苗買來,養到這么大。先前還要多,中間鬧了場雞瘟,死了11只,把老漢心疼死了。剩下的這些,也不打算賣了,不是專門有人出高價,上門來收小土雞,賣給城里的大飯店嗎?這幾年土雞的價格一年年往上漲,城里人的嘴,是越吃越刁了!老漢說不賣,留著過年吃,過年的時候人多,兒子媳婦,孫子孫女,女兒女婿,加上老弟兄幾個,孫男弟女的一大堆,都從城里回來了。小兒子說不定,還會帶回他新談的對象!到時候該吃吃,該喝喝,一年累到頭,不就圖個團圓嗎!說著,馮紀耐轉身進屋,拿了一摞小本本出來,有扶貧手冊,烈屬證,烈屬補貼,殘疾證,殘疾補貼,養老保險等等,一下子捧給我。對“扶貧手冊”,他們有一個專門的說法,叫做“錢袋子”。我說不是2016年就已經脫貧了嗎?還留著它干什么?鎮里陪同的工作人員解釋說,脫貧不脫政策,脫貧不脫幫扶,潘作家你翻翻看,這是2019年的新本。
小狗花花不時地跑過來,對著我們作揖,它把我認成了鎮里的扶貧干部了。馮家的情況特殊,不僅是烈屬,本人還有殘疾,鎮里的扶貧工作人員就經常上門來,看看可有什么困難?需不需要幫助?門前的光伏板,一年能有3000塊錢的收入;一季的生姜,也是重要的經濟來源,再加上七七八八,各項政策補貼,一個人夠花了!“我一個老頭子,能吃多少,能喝多少啊?就是小兒子還沒結婚,得給他攢點錢,到時候別管多少,總是我當老人,該盡的一點責任!”
陪同我過去的小儲告訴我,老人家之前還養了好幾頭豬,結果前一陣子鬧豬瘟,死的死了,殺的殺了,一頭也沒剩下。
“啊?”我吃了一驚:“那不是損失很大嗎?”
“不怕,有政府呢,政府給買了保險。保險公司已經受理,就這幾天吧,他們就該上門來了。”
“政府不光給上了豬險,”馮紀耐指了指門前的光伏板,補充說:“還有光伏板,茶葉、毛竹、生姜什么的,政府也都給上了保險了。”
馮紀耐家的光伏板,正沖著堂屋的大門,藍天白云下面,看上去十分顯眼。
4
采訪期間,幾乎在每一個貧困戶的門前,我都看見了這樣的光伏板。
金寨縣的光伏扶貧電站建設,走在全國的前列。光伏發電技術成熟,投資回報率較高,一次性投資,可長期受益,特別適合于因殘、因病致貧的家庭。采訪中,差不多的貧困戶家庭,都把光伏發電算做一筆重要的經濟收入。
“只要是晴天,你就坐在屋里頭,等著收錢好了!”陪我去小儲說,小儲是鎮扶貧辦干部,“90后”。
光伏發電共需要投資24000元,其中政府投資8000元、企業捐贈8000元,貧困戶自己投資8000元。如果貧困戶拿不出錢,可以由保險公司提供信用保險進行貸款,貸款還款從每月光伏發電收入中自動扣除。光伏發電全部上網,每發1度電收益1元錢。
這個扶貧項目的準確表述,叫做“分散式光伏發電”。雖說是操作簡單,可到底也是高科技,這一塊塊發電板,就這么無遮無擋,安裝在屋外頭,一年365天,天天日曬雨淋,要是壞了,錢不是白投了?
“這個不存在,”小儲慌忙解釋:“ 2017年,金寨油坊店鄉面沖村貧困戶詹史成家的發電板,一下子壞了4塊。后來人保財險通過核實后,每塊賠付給他1070元,合計賠付了4280元。”這件理賠案,經媒體報道后,算是給全縣的光伏發電戶,吃了一顆定心丸。
人保財險作為主承保單位,僅在2016年一年,就承保光伏發電8674戶,其中貧困戶7794戶、一般戶880戶、村集體218個,總保額2.0846億元。全縣共建成光伏扶貧電站197.1兆瓦,總投資14.78億元,實現綜合收益4.5億元,助力10.58萬貧困人口脫貧、67個貧困村出列,將全縣的貧困發生率降至2.73%。
有一點我很是困惑,那就是這些分散在一戶戶人家院里屋外的光伏板,發的電怎么并入了大網?最后又是怎么結算?貧困戶留守在家里的,多是一些病殘老人,接連問了幾戶,也沒誰說得清楚。回到鎮里,專門詢問了負責該項目的同志,才知道原來是根據山區電網的特點,戶用光伏電站采取220伏就近并網,村集體光伏電站采取380伏就近并網,聯村光伏電站通過升壓接入10千伏和35千伏線路。一開始,上網收益是按照自發自用、余電上網的模式,現在已經轉變為發用分離、全額上網:“不用你自己操心,每天發多少度電,該有多少錢的收益,有專門的人給你計算!”
金寨縣地處大別山主脈北坡,三省七縣二區結合部,境內多崇山峻嶺,地形地勢多變。因此建站模式也多樣化,因戶因村制宜。概括起來說,金寨的光伏扶貧電站建設大致有三種模式:一是單戶用光伏扶貧電站。對具備光照、承壓、方位等條件的,在貧困戶屋頂或房前屋后空閑地,建設戶用光伏扶貧電站,產權歸貧困戶所有。全縣共建成7803戶、每戶3千瓦獨立戶用光伏扶貧電站,每個電站投資2.4萬元,對自籌資金確有困難的貧困戶,采取互助資金借款或扶貧小額信貸等方式解決;二是村級光伏扶貧電站。從2015年開始,每村投入74萬元,分村建成裝機規模100千瓦的村級光伏扶貧電站。動員社會力量捐建,省、市、縣等32個駐村幫扶單位,為全縣30個貧困村,建成了3141千瓦村級光伏扶貧電站,產權歸村集體所有;三是聯村光伏扶貧電站。2016年,對沒有安裝條件的貧困戶,采取鄉鎮、村協調選址安裝聯村光伏扶貧電站方式,總裝機規模14.5萬千瓦,產權歸縣級所有。資金投入采取各級財政資金注入、光伏企業讓利和貧困戶資金入股等方式籌集。發電收入除去相關費用,凈收入用于貧困戶入股分紅,覆蓋了全縣1.8萬個貧困戶。
作為“精準扶貧”的一項重要舉措,為使光伏扶貧項目的實施規范化,金寨縣首先在選擇扶持對象環節上,就進行了嚴格把控。按照優先照顧有重大疾病、殘疾、喪失勞動能力家庭的原則,通過貧困戶申請、村級評議公示、鄉鎮核查、縣組織抽查等程序,以確保貧困戶優先享受光伏扶貧政策。馮紀耐不僅身有殘疾,而且是烈士后代,所以提出申請后,在各個環節上都順利通過。
光伏扶貧由縣“3115”脫貧計劃指揮部統一組織實施,項目建立了光伏扶貧項目收益分配機制,集中式光伏扶貧電站和分布式(聯戶型)光伏扶貧電站凈收益,全部用于扶持貧困人口。“3115”脫貧計劃是2016年,金寨縣委縣政府出臺的脫貧攻堅實施意見,“3”是指實現“人脫貧、村出列、縣摘帽”這3個脫貧攻堅目標;“11”是指實施精準脫貧10大舉措、推進脫貧攻堅10大工程;“5”是指強化5項保障措施,到2019年底,完成8.34萬人的脫貧銷號任務,實現“兩不愁、三保障、一高于、一接近”目標。在光伏扶貧電站建設工程中,投融資主體的明確最重要。20萬千瓦光伏扶貧電站建設,金寨匯金投資有限公司作為投融資主體;分布式(聯戶型)光伏扶貧電站建設,金寨縣扶貧開發投融資有限公司作為投融資主體;村級光伏電站擴容工程,村集體經濟實體“創福公司”作為投融資主體。為了確保運營維護長效化,全縣投入資金522萬元,搭建了4個服務云平臺,保障光伏扶貧電站持續平穩運行。同時開通運維熱線,建立短信服務平臺,第一時間發現并及時解決電站運行中出現的各類問題。留守在家的老人們,雖然操作不了這些高科技,但他們在外打工的孩子們,在手機上卻可以隨時接收到平臺發布的相關信息。
遠超我的經驗,也遠超我的想象,中國鄉村的變化,翻天覆地。中國鄉村從未像今天這樣,激發出如此巨大的智慧,爆發出如此巨大的創造力。為了綜合利用,延伸光伏產業鏈條,金寨縣還探索出了好幾種互補模式,大力發展“板下經濟”:養光互補是把部分高支架光伏電站免費提供給貧困戶,在光伏板下養殖皖西白鵝、生態土雞、小龍蝦等,戶均年增收3000—5000元;藥光互補是把光伏電站的朝陽與靈芝的喜陰特性結合起來,在光伏電站板下種植靈芝,既增加了靈芝的產量,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實現了土地的集約、節約、高效利用;林光互補是在光伏板下空地套種紅葉石楠苗木,既可以通過光伏發電幫助貧困戶增收,又能夠通過苗木種植增加貧困村集體經濟收入,實現光伏發電和苗木種植兩不誤。
2018年7月30日,全國村級光伏扶貧電站建設管理工作會議在金寨召開;2018年10月,金寨縣因光伏扶貧工程,被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授予“脫貧攻堅獎組織創新獎”。
潘小平,安徽省作家協會原副主席,安徽大學兼職教授安徽省散文隨筆學會會長。1992年之前,在淮北煤炭師范學院(今淮北師范大學)中文系從事寫作教學和當代文學研究,1992年初調入省文聯理論研究室,1995年開始從學術研究轉向文學創作。以散文和紀錄片為主要創作樣式,有《季風來臨》《北方驛站》《城市囈語》《前朝舊事》《長湖一望水如天》《讀書的女人不會老》《無用之用》等散文隨筆和文學評論出版發行。廣泛參與電視策劃與制作,擔任多部近200集紀錄片撰稿,希望通過現代傳媒手段,將精英的理念傳達給大眾。近年來開始嘗試小說創作,有《少男》《扁豆花開》《雪打燈》等中篇小說發表并選載。作品曾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中國電視專題獎,中國優秀紀錄片獎,安徽“五個一”工程獎等。已發表論文、散文、紀實文學、影視文學、小說約980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