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3-27 來源:安徽作家網 作者:安徽作家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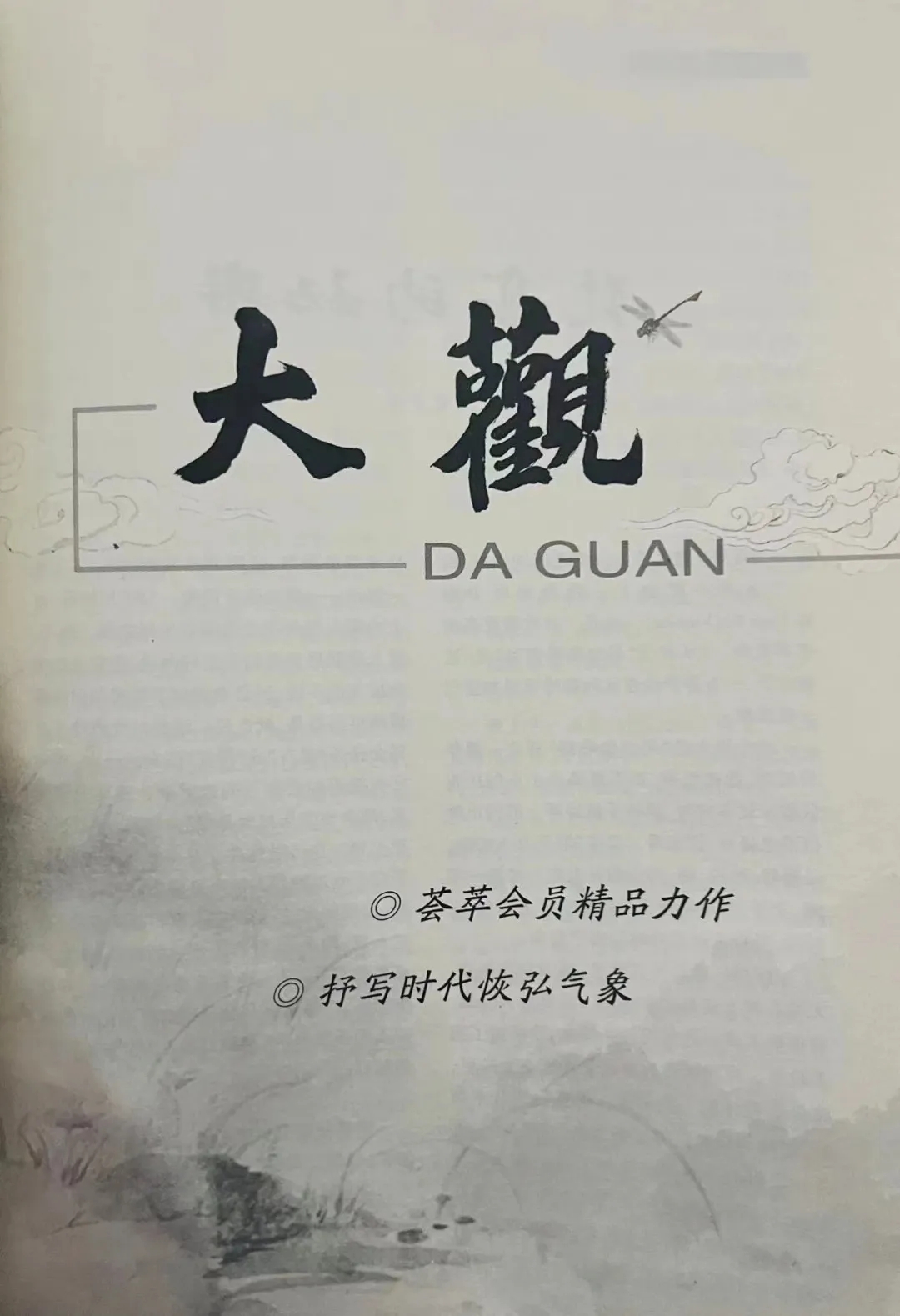
我的叔叔傻柱(節選)
方啟華
1
我的家鄉位于長江邊上。幾千年來,她就像一個慈祥的老太太,靜靜地躺在地上,而那么多的分支干流,像她的頭發絲一樣,滲入兩岸的每一寸土地中。我們村子被長江的兩條支流緊緊地圍住,后來我從衛星云圖上看到了她,她的形狀像我奶奶常用的蒲草扇子。
90年代初,那會交通還不發達,我們去縣城有兩條路可選,一條是水陸,依靠人工撐船,要半天時間才能到達縣城;另一條路是先走十公里的村路,再坐只有鄉村才有的三輪敞篷摩托車,兩塊錢車票,算上走路的時間,也要三個小時。
我第一次去縣城是我五歲的時候,我得了肺炎,爸媽帶著我去縣城看病,因為趕時間,我們是坐車去的,在縣城住了兩天院,吊了十幾瓶藥水,才有好轉。回來時,爺爺和傻柱一早就在馬路旁等著我們,傻柱扛著我回家,媽媽還他扛得低一點,別又吹了風。那會傻柱應該還不到三十歲,傻乎乎地笑著,那張憨厚的臉是我童年最深的記憶。
2
爺爺馬德慶曾是村子里唯一的老師,既教語文,又教數學,后來也當了幾年校長,90年代末,學校才來了一幫年輕教師,爺爺才放下教學的擔子。爺爺一生一邊從教,一邊種地,幾乎村子里所有識字的人都是他的學生。除了傻柱外,其實傻柱也識字,這一點曾經出乎所有人預料。也有人說傻子認得的幾個字也是爺爺教的,但爺爺自己清楚:他能教干粗活的農民,但教不了一個傻子。
媽媽跟我說,他第一次見傻柱應該是1991年。那會她還是一個十七歲的姑娘,傻柱是空降到村子里來的,沒人知道他從哪里來。媽媽說,他見傻柱的第一眼,傻柱就坐在爺爺家的草垛上。他的頭上,身上都是稻草,臉上烏漆墨黑的,身上也臟兮兮的,一看就是個流浪漢,而且是一個傻兮兮的流浪漢,不管是誰來了,都傻乎乎地笑,草垛最高有三米多高,村里人都怕他摔下來跌傷,只有我爺爺爬上草垛,把他給牽下來。
爺爺是一個熱心人,他把傻柱帶回家的時候,奶奶沖他也吼幾句。他默不作聲,并打來涼水給傻柱先洗了一把臉。傻柱還是傻笑,對于湊到他臉上的濕毛巾,還有些抗拒,爺爺把傻柱擦干凈一看,發現這小伙子除了傻,長得還算眉清目秀,濃眉大眼,就算留了一點胡子,也不顯老,看起來二十歲上下。如果不是傻子,倒像是城里來的大學生模樣。
3
爺爺追著傻柱直問,小伙子叫什么名字,從何而來,要去哪里,家里有什么人。但問了半天都是白問,傻柱除了傻笑,沒有任何反應。這可急壞了我的奶奶,奶奶轉頭對爺爺說,就你事多,別人都不動,只有你把他帶回家。
爺爺說,我是老師,也是黨員。看這孩子也挺可憐的。
奶奶說,村支書不也是黨員,他怎么不管?
爺爺說,他不是在鎮上開會嗎?
奶奶說,那你把他領過去。
爺爺用說教的語氣對奶奶說,做事要從一而終,送佛送到西嘛。
眼瞅著打聽不到任何結果,爺爺只好盛了一碗飯,給這流浪漢送上來,傻子倒也不是太傻,看到米飯甭管有沒有菜,就用手抓起來,爺爺遞給他筷子,他竟當沒有看見,奶奶看著直搖頭。
往后幾天,爺爺用盡一切辦法來打聽流浪漢的來處和去處,甚至去了村支書家商量,村支書讓爺爺擬個“尋人啟事”,貼在村委會。爺爺就用過年貼春聯的紅紙和毛筆寫了兩則尋人啟事貼在村委會大門的兩側,并注明人就在爺爺家里。結果好幾天都沒人來認領,倒是來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其中也包括我的媽媽,大家看著傻子就像是一個外星生物一樣,充滿好奇和未知。
4
對了,我還沒介紹我的媽媽,我的媽媽是村支書的女兒,小名叫丫丫,媽媽說她曾是村子里公認的村花,不光長得好看,也穿得好看,村子里一半的男生都暗戀她。但最后獲勝的是我爸爸。我的爸爸叫馬陽,那會也才十八歲,也是個帥小伙,當然那會兒還沒有我,我是五年后,才來到了這個世界。
奶奶雖然嘴硬,但也是一個老好人,他讓爺爺給傻子洗了個澡,再換上我爸爸的衣服,又給他剪掉了又長又臟的頭發,然后再看傻子,已然是俊俏小伙。奶奶總覺得爸爸長得尖嘴猴腮的,繼承了我的爺爺,而不太像她,眼前忽然出現這樣一個大男孩,奶奶流露出的同情心立馬翻了一倍。
我的爸爸倒也“寬容大量”,雖然一開始有一點點抗拒,但還是在爺爺奶奶的堅持下,跟傻子睡在一個床上。傻子倒也識趣,有飯吃又有住,也逐漸學會用筷子,穿得也不算太邋遢,也沒惹什么大麻煩。奶奶心想傻子來到了自己家,多半也是緣分,就給傻子起了個名字,叫柱子,因為人傻,所以大家都叫他傻柱。
那會媽媽經常去我家,借著學習的名義跟爸爸約會,傻柱就當電燈泡,在一旁傻傻地盯著媽媽看,有時甚至流出口水來,媽媽見他傻乎乎的樣子,心里直笑,尋思著傻子也愛看美人。傻柱每天和爸爸一起送媽媽回家,為此那時的爸爸沒少私下里來揍傻柱,對他是又恨又嫌。
據說,某日傻柱和爸爸一起到了媽媽家,媽媽還在房間里洗澡,而四下無人,爸爸就趴在門縫里頭看,叫傻柱在門外把風。傻柱哪會把風,就傻兮兮地靠在墻上,發呆。
可能是用力過猛,媽媽的房門上不免有些動靜,乃至于媽媽注意到門外有雙眼睛,遠處媽媽的家人也正好往回趕。爸爸稍有察覺,比老鼠還靈敏地找個洞溜了,媽媽披著浴巾沖出來,見傻柱傻兮兮地站在門口,而外公外婆也正好回到家中,眼看這一幕,都認為偷看的是傻柱,傻柱第一次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外公上去就是一陣打,外婆拉住,媽媽嚇得哭起來。但也許只有我媽媽心里清楚,偷看的絕不是傻柱,傻柱只是背個了鍋。
5
外公氣不打一處來,領著媽媽也來找爺爺理論,爺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心想他是個傻子,他知道個啥,傻子壓根做不出這事來。但心里清楚,偷看我媽洗澡的,多半是自己的兒子。不管是誰,先賠了不是,又叫來我的爸爸馬陽,叫馬陽來解釋,爸爸支支吾吾,就算自己不是主謀,也有個疏于看管的責任,奈何外公沒有當場捉住,沒有直接證據,也橫不起來,倒是我爸爸隨口一出:大不了我娶了丫丫好了。
外公隨口一出,呸,臭小子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媽媽在一旁既羞又樂。但不得不承認,傻柱倒間接地撮合了我的爸爸媽媽,嚴格來說,也算是一個媒,于我們老馬家算功德一件。
而這時,爺爺和外公都覺得傻柱留在村里也不過事,他做的這個“齪事”不說。也許傻柱的父母還在大江南北地找他,于是跟爺爺商量了一下,到了鎮上的照相館給傻柱拍了一張照片,還抽空去了縣城自費登了個報,把村委會的尋人啟事一字不改地搬到了報紙上。但報紙發行后,還是沒見個人來。
爸爸既讓傻柱背了黑鍋,也多少抱有僥幸的心理,心想家里也不愁吃穿,無非是多一雙筷子,關鍵時刻,還能頂上用場,也漸漸地接受了傻柱。但因偷看洗澡這事,跟媽媽有段時間保持一定距離,類似現在他們自己常用的“冷戰”。終于有一天,爸爸叫傻柱帶著一封信和爸爸特地買的牛奶味餅干去找媽媽,傻柱依舊傻兮兮地往前沖,好像上次在外公家被打這事沒發生過一樣,不管是刀山火海都往里面闖。
媽媽看到傻柱,也生他的氣,但還是接過了信,還把餅干分了他兩塊。爸爸看著傻柱高興回來,心想上次那事總算翻了篇。

方啟華,1986年出生于安徽無為,現居合肥。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抵達》詩刊副主編,曾任鳳凰網安徽頻道等多個網絡媒體特約評論員、專欄作者,部分詩歌作品散見于《星星》《揚子江》《詩歌月刊》《江南詩》等詩歌刊物,曾參加第三屆長三角青年詩人改稿會,曾獲首屆安徽詩人新銳詩人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