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3-07 來源:安徽作家網 作者:安徽作家網
《王朝的余暉》再現近代中國各階層奮力求生的大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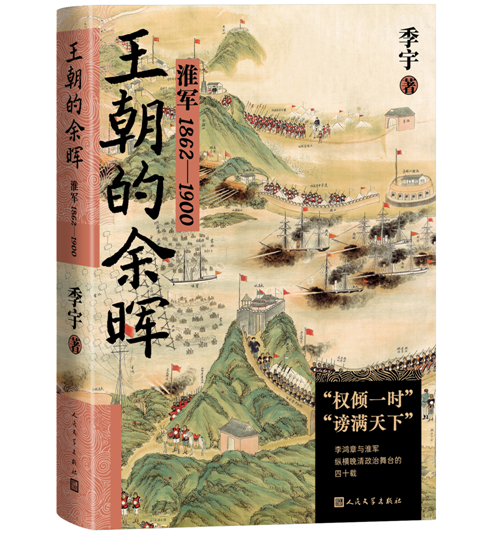
季宇新作《王朝的余暉:淮軍1862-1900》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本書從1860年前后晚清政壇動蕩寫起,到1900年庚子國變后結束,書寫了清末重臣李鴻章創建、發展淮軍的始末以及淮系集團不斷演變、壯大直到最終覆滅的歷程。在接受新安晚報、安徽網、大皖新聞記者專訪時,季宇直言,退休后寫作的功利色彩淡了不少,寫作成了一種愛好,也是一種生活常態。“安徽文化資源是一個富礦,我一直情有獨鐘,寫起來也得天獨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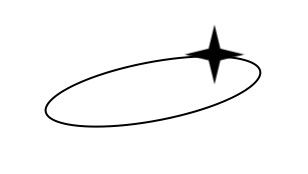
以淮軍興衰,觀察晚清四十年
新安:晚清歷史十分豐富,您對這段歷史十分熟悉并深耕多年,那創作這部《王朝的余暉》的動因是什么?
季宇:晚清歷史和人物作品,我寫過一些。如徽商題材的《新安家族》《徽商》等;如辛亥革命題材的《共和,1911》《江淮雄風》等;如反映晚清歷史的《清朝大崩潰》等;還有清末民初的《段祺瑞傳》《權力的十字架》等。淮軍這個題材,早在2009年,安徽電視臺拍攝十集大型紀錄片《淮軍》時,我受邀擔任撰稿,從那時起,我就開始關注這個題材了。
淮軍最早是從安徽走出去的,后來逐步壯大,成為晚清王朝最大的政治、軍事集團,前后貫穿了晚清四十年的歷史。關于晚清的書有很多,但《王朝的余暉》從淮軍興衰這個角度來觀察晚清四十年的歷史,這就與其它寫晚清的書有了區別。此外,淮軍是從安徽走出去的,地域色彩濃郁,這也讓我很感興趣。安徽文化資源是一個富礦,我一直情有獨鐘,寫起來也得天獨厚。
新安:能不能說,淮軍史就是一部晚清史,也是晚清軍事史。
季宇:淮軍的歷史從同治初年開始,到庚子事變結束,貫穿了整個晚清歷史。可以說,一部淮軍史就是一部晚清史。晚清內外交困,風雨飄搖,為了改變積弱,中國社會各階層都在艱苦探索,尋找出路。從這個角度說,淮軍的興衰史也是一部社會各階層艱難探索,奮力求生的大歷史。這些都是我極力想表現的。
在寫這本書時,我有兩點感觸較深。一是晚清時,西方列強為了瓜分中國,多次挑起侵略戰爭。淮軍作為國家武裝力量的中堅,成為抗擊外敵入侵的主力。他們中涌現出了許多愛國將領,像吳長慶、潘鼎新、劉秉璋、劉銘傳、左寶貴、鄧世昌、聶士成等。雖然晚清對外戰爭(除中法戰爭外),大多以慘敗告終,但在這些過程中,一些淮軍將領所表現出的英勇無畏的犧牲精神卻令人感動,像左寶貴、丁世昌、聶士成等都死得非常悲壯。他們不愧是民族英雄,永遠值得緬懷。
二是當時的淮軍集中了許多那個時代最優秀的人才,其中有一批最早“睜眼看世界”的人,非常可貴。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英國工業革命開始轟轟烈烈地興起。隨著“蒸汽時代”的到來,西方列強迅速崛起。然而,經歷過康乾盛世的清王朝依然沉浸在昔日的輝煌中。對于世界大勢,當時大多數國人都渾渾噩噩,一無所知。但淮軍中有一批人最早接觸到西方的先進文明。有句話叫“中堂勛業洋槍始”,就是說,淮軍進入上海后,是最早接觸到洋槍洋炮的。當時中國還是冷兵器時代,淮軍接觸到洋槍洋炮,便開始換裝。這是中國軍事近代化的開始,也是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開始。后來,淮軍中很多人物都投入了洋務運動。他們主張師夷之長技,在中國辦新式教育,興辦各種新型企業,如機器制造局、江南造船廠、開平礦務局、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漠河金礦等等。1870年,李鴻章在直隸總督任上啟動了第一批留美幼童計劃,更是堪稱中國教育史上一大創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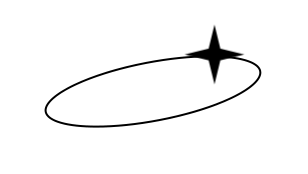
以真實客觀思想性,耙梳“還原”歷史
新安:晚清是風云變幻的大時代,書里眾多的線索和視角,作為一個創作者,最大的難點在哪里?
季宇:這本書的歷史跨度大,人物眾多。從1862年至1900年,這是清王朝走向衰落的幾十年,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所以說風云變幻,一點也不為過。淮軍鼎盛時,有十一個軍系,二百多營。淮系的重要人物,省部級文職高官(如總督、巡撫、尚書、侍郎)有三十八人之多;至于武職,像提督和總兵數量更是驚人,約有一千三百人之多,其中有七百多人為土生土長的安徽人。晚清的歷史又極為復雜,各個派系之間、朝廷與地方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矛盾更是錯綜復雜,如何在四十萬字的作品中把這些都有機地表現出來,在結構和寫作上有一定難度,需要動點腦筋。
再者就是如何寫出每個人不同的性格,性格要靠細節來支撐。我這本書是非虛構,不能瞎編,每個細節,每個場景,包括對話,都要有出處,有根據。出版社也是這樣要求的,責編王蔚先生與我溝通時就多次強調。為此,我花費不少精力去查閱史料,包括筆記、回憶、文檔、通信等,從中一點點耙梳、尋找,的確費了不少勁。
新安:書中雖然引用了大量的史料,但讀起來卻非常生動,也非常好讀。您好像在寫人上花了不少工夫?
季宇:是的,我是作家,我和歷史學者的關注點有很大不同。歷史學者高屋建瓴,比較注重宏觀的歷史以及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作為作家,我比較關注故事,關注個體活動,特別是注重怎么寫好人物。寫好人物,關鍵是要寫性格。比如,曾國藩與李鴻章都是“中興名臣”,李鴻章還是曾國藩的學生,但他們的行事風格有很大差異。曾國藩為人師表,追求完美,但李鴻章是實用主義者,他做事注重結果,不在乎手段。曾國藩用人講究出身和品行,可李鴻章不管這一套,只要有能力,能夠為己所用,不論雞鳴狗盜之徒,一律來者不拒。他還善于籠絡收買人心,凡跟著他干的人,他給官給錢,從不吝嗇。他有一句名言:“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不助人,誰肯助我?”
左宗棠的性格也極有特點。他為人強勢,做事霸蠻,就連曾國藩也不放在眼里。他是舉人出身,由于沒考上進士,所以對進士很不待見,提拔干部也多用舉人不用進士。這些在正史中也許無關緊要,但在文學作品中卻多多益善。
還有人有多面性,不是非白即黑。如丁寶楨也是清代名臣,此人為官清廉,一聲正氣。慈禧手下的大太監安德海南下采辦,作威作福,怨聲載道,但人們敢怒不敢言,就連直隸總督曾國藩也不敢動他。可他到了山東地界,卻被時任山東巡撫的丁寶楨一舉拿下,斬首示眾,這事轟動朝野。可就是這樣的一位清官,卻堅決反對為楊乃武與小白菜平反,為此他還大鬧刑部,咆哮公堂,指著刑部尚書鼻子,罵他老邁糊涂。但事后證明,楊乃武與小白菜確系冤獄。人無完人。我認為,表現人物性格最好的辦法就是寫出他的多面性,這也是我多年寫作的一點體會。
新安:“還原復雜歷史的本來樣貌”是很多創作者希望能做到的,那在您眼里,歷史的本來樣貌應該是什么樣的,如何才能無限接近這個目標?
季宇:紀實文學,或者說非虛構作品,顧名思義就是以非虛構方式真實地反映生活,但對于歷史,真正“還原”很難做到,我們能做的只能盡可能地接近歷史。我寫過不少這類作品,比如《共和,1911》《江淮雄風》等,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江淮雄風》可以說是第一本全景式的寫安徽辛亥革命歷史的書,這也算是我的一點小小貢獻吧。我個人感到,要寫好這類作品,需要做到真實性、客觀性、思想性。
真實性,就是要提倡學者精神,把敘事建立在史料的基礎上,力避杜撰,最大限度地呈現或還原歷史本來的樣貌;客觀性,就是不拔高,不貶低,力求真實;當然,最重要的一點則是思想性。一部好的非虛構作品必須注意發掘時代精神,用現代觀點反映歷史、解讀歷史。在《王朝的余暉》中,我對淮軍由盛走向衰落也進行了反思。它們向西方學習,卻不改變封建制度,還有腐敗嚴重,這些痼疾都導致了它們無法擺脫舊式軍隊的宿命,最后跌落神壇。這與晚清王朝走向滅亡是一個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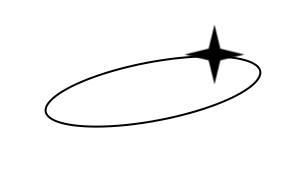
退休后的寫作,功利色彩淡了
新安:退休之后,您手里這支筆是一直沒閑著,而且動輒出來的就是大部頭。這種寫作其實對創作者的智力包括體力都是一種考驗,您應該也是70出頭了,是如何保持這種激情和狀態的?
季宇:退休后我寫作的功利色彩淡了不少,寫作成了一種愛好,也是一種生活常態。我喜歡靜,不大喜歡湊熱鬧,年紀大了更是如此。王維有詩:“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待在家里,喝喝茶,看看書,寫點東西,這種悠然自得的狀態是我喜歡的。寫長篇的確比較累,但我現在寫什么都不趕,慢悠悠地來,張弛有度。我把這稱之為“慢寫作”,能寫一點就寫一點,也不強求。每有收獲,則沾沾自喜。廉頗老矣,尚能飯,這就夠了。我希望這種狀態一直保持下去。
新安:接下來手里還有什么樣的寫作計劃?
季宇:今年底、明年初我有兩本書要出。年底要出的是小說集《月光如水》,收了我近兩年創作的中短篇小說共八篇。這些小說都在全國各地的雜志上發表,其中一些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長江文藝·好小說》《中篇小說選刊》《思南文學選刊》等有影響的選刊所選載;明年初要出的是一部長篇,是寫劉銘傳在臺灣的故事。兩本書均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
另外,有個題材我一直在醞釀,就是想以合肥為背景,通過幾個家庭,寫改革開放以來幾十年的變遷。我一歲時就隨父母來到合肥,小時候我家住在六安路一帶(當時也是老城區的中心),那里有一個土崗。每到傍晚,我和小伙伴們爬上土崗玩,只見成群的蝙蝠在暮色中飛翔。那時的合肥還很荒涼,稻香樓、黑池壩一帶都是農田。可幾十年的變化,合肥已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我是見證者之一,所以很有一些感受。
(新安晚報安徽網大皖新聞記者蔣楠楠,專訪刊發于《新安晚報》2023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