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3-04-07 來源:中國作家網 作者:安徽作家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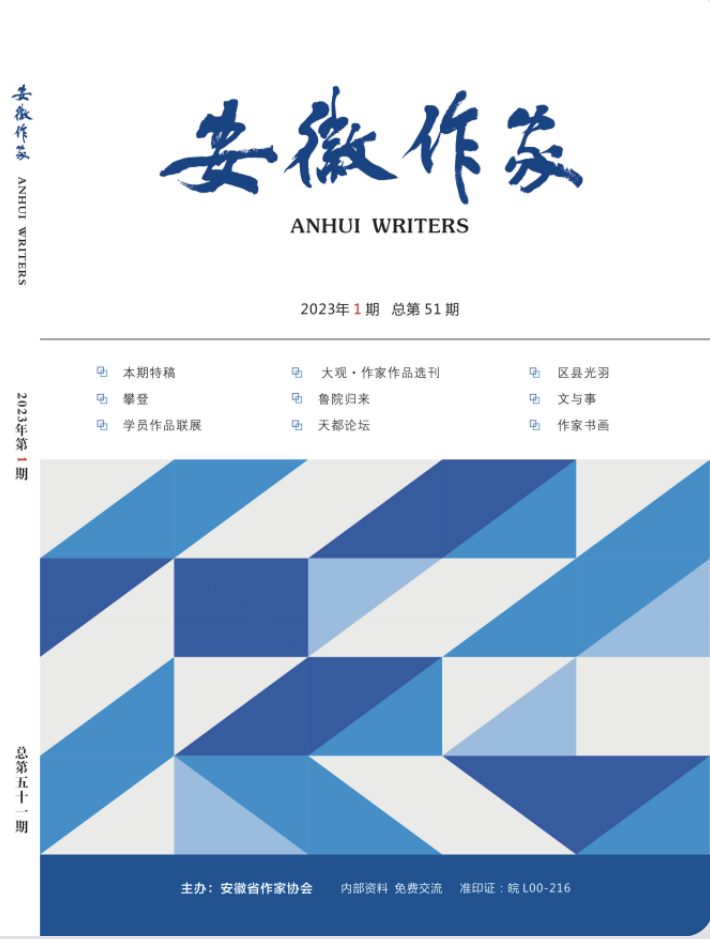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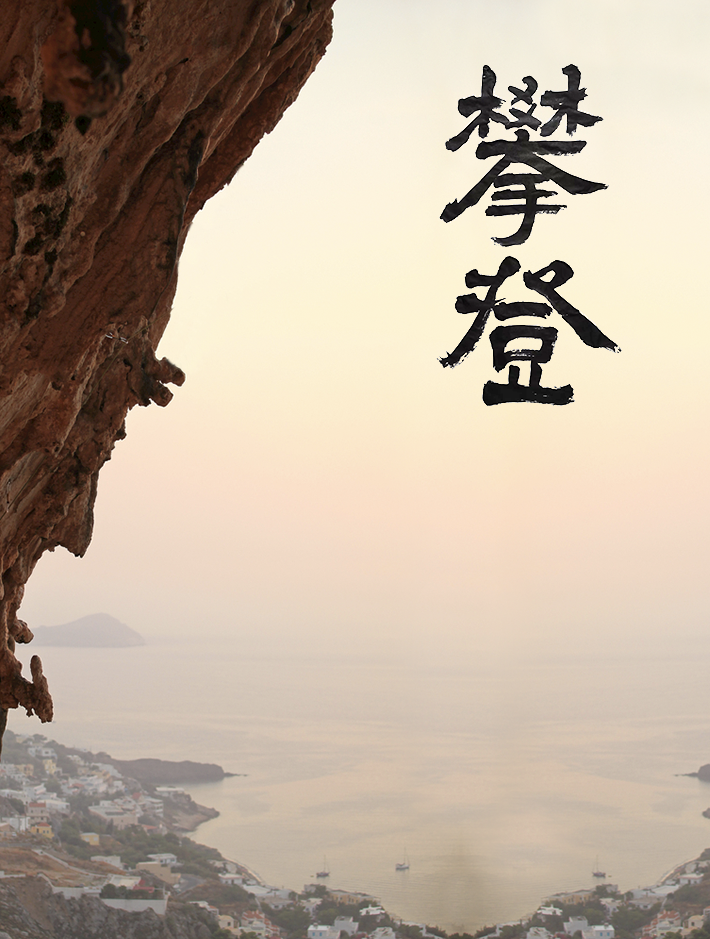
編者按:中國作協推出“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以來,省文聯指導部署,省作協積極組織,協調引導,搭建平臺,賦能皖軍文學精品生產,推動安徽文學高質量發(fā)展。洪放、時國金等一批作家,是我省“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的攀登者,同時又是領跑者、助跑者。從本期起,《安徽作家》推出“攀登”欄目,陸續(xù)刊發(fā)他們的作品。
作品欣賞
把人間唱遍(之三)
洪 放
大街和小巷
博爾赫斯用一生的文字建構了他的帶著無數分岔小徑的花園。那是哲學的,歷史的,人性的,神秘而高遠,猶如形而上的宮殿。很多人因此迷路,試圖在這花園中,尋找到一條適合于自己的小徑,并從而在小徑上追尋意義與并不存在的未來。當然,這是荒謬的。一如在這城市之中,追尋那些大街和小巷的意義,或者追尋它們的所來與所去。它們都只是歧途!包括這偌大的城市,對于一個生活中的心靈來說,它要么是往昔生活的折射,要么就是此生注定的一次劫難。
此刻,這個人的腳步正從大街進入小巷。
他的腳步有些拖沓,仿佛從前的泥沙還沾在鞋底上。那些泥沙雖然已經不太明顯,甚至有的已經鍥入了鞋子的深處,但是,它們的重量仍然存在。那是他已經過完的日子的重量,是從鄉(xiāng)間走到城市所耗費的重量,是從另一個城市進入這個城市所提拎著的重量。這重量就像古時候行旅者的包袱,里面雜物紛呈。不僅僅有白銀,也有皂片;不僅僅有書卷,也有烙餅;不僅僅有青衫,也有玉佛。如今,這些重量都附著在鞋底的泥沙上了。沒有人看見,也不會有人看見;甚至,也不曾有人愿意看見。他,或者無數個他,從大街轉入小巷。秋天的桂花將開,桂花的香氣若有若無。他停下步子,翕動著鼻子。桂花的香氣卻繞開他的鼻子,跑進巷子旁的老宅子了。
許多年的追尋,其實無非就是獲得與不斷的放棄。城市一天天膨脹,但是,對于每一個在城市中行走和生存著的人來說,城市依舊是城市。城市也就只是一只籃子,讓行走者取得食物、水與空蕩蕩的名聲,以及那些不堪一擊的愛情。那是愛情嗎?或許就像剛才的桂花香。只是一瞬。然后便消匿了。除了巨大的汽車聲,人聲,鋼筋、水泥擠壓聲,腰椎折斷聲,老人蒼茫的哭聲,墻角最后的那一叢青草枯死聲、老井邊上繩子的坼裂聲……這個從老街進入小巷的人,他茫然而獨立地停在那里。秋風將他的頭發(fā)吹硬,將他的目光吹硬,將他掌心里那僅存的一縷桂花的香氣吹硬。
大街和小巷對于一個鞋底沾滿泥沙的人來說,沒有多少選擇的權利。在大街上,他熱切而顫抖。他想將自己飄揚成一面旗幟,插進市政大樓、銀行、保險公司、房地產公司、電力大樓、沃爾瑪、特斯拉、華為、名車匯、蘋果手機,和那些光鮮的下午茶、西裝、晚餐會。他曾經讀過博爾赫斯的《小徑分岔的花園》。他曾認真地思考著哪一條小徑會是自己的終極小徑。是那些他夢寐以求想插進旗幟的地方嗎?它們都在大街上,冠冕堂皇,高大美麗。他站在它們的腳下,或者蹲在它們的墻跟下。有時,他也勇敢地伸出手,想去握一握它們。結果,他發(fā)現:那些手永遠在高處。城市的偉大就在于:永遠沒有正面的拒絕,卻永遠都已被抽走通向高處的梯子,或者步道。
一個奮斗的人。他卻走進了小巷。
而小巷更深。小巷老派而堅定。小巷其實是城市最后的骨頭,即使有桂花香,有井水清冽,有幽深的院墻與蘗荔。他重新起身,慢慢往小巷深處走。他的愿望微乎其微——他只想得到一杯熱茶,一片花瓣,一把椅子,一個故事里可有可無的角色。
“時光中虛設的門,你的街道朝向那更輕柔的過往。”
梧桐樹葉,舊書店
上午九點。梧桐樹寬大的葉子開始卷曲。當然,它還在枝頭上。這些有著粗大且執(zhí)拗的樹干的梧桐樹,是這個城市已經很難見到的風景。每個城市在過分高速的成長中,或許都會有意無意地留下一兩處帶有往昔痕跡的風景。梧桐樹便是。它們幾乎同這條有些偏僻的道路一樣長久。春天的時候,梧桐發(fā)芽,長出新葉。那是何等的動人啊!新葉的清香彌漫在道路上,也彌漫進書店。這片狹小的僅僅只有十幾平方米的舊書店,被梧桐新葉的清香擁抱著。那是一年中最生動與最美好的時光。從前,舊書店的主人,一個微微佝僂著腰身的中年男人,會走出書店,站在門邊,望著梧桐樹,自言自語。他到底說些什么呢?沒有人認真地聽過。直到他離開之后,有一天,一個老的讀書人過來購書。老先生隨意地說道:“我每次來,他都站在門邊上看樹。他是在對樹說話吧?”
沒有人能回答老先生了。
梧桐的葉子開始卷曲,然后,下午的陽光下,這片葉片像命定的一樣,飄落下來。它先是在枝頭一點點地悸動,似乎在與這棵與它相依相伴了一年的樹告別。那是無聲的,卻沉浸著巨大的力量。終于,它聳動著身子,離開枝頭,它往下飄,它的方向明白而堅定——它飄向了梧桐樹的根部。它停在根部,仿佛最后一次親吻這厚實而寬廣的母體。然后,秋風來了。它旋轉,飄落;再旋轉,再飄落……
女人從舊書店的書架上抬起頭,早晨,她已經將一批剛剛收進來的舊書上架。從前,這份工作都是男人做的。女人也很少到舊書店來。這個被很多人稱為城市文明的最后的擺渡者的書店,半死不活,如同男人的病。女人只是偶爾過來看看梧桐,她甚至很少正眼看那些古怪地進店挑選舊書的顧客。男人卻同他們有說有笑,一同在舊書堆里翻找。男人的身上,不僅有了病的藥味,更多的則是舊書的古味和舊歲月、舊時代的黃昏味。她不喜歡。她只喜歡梧桐的新葉。到了秋天,她每到舊書店,總要將梧桐的落葉掃光。男人說:留著吧,也是個念頭!
念頭有意義嗎?她問。
男人不答。如同她現在無法回答老先生們的提問。舊書店在男人走后關了一陣,有一天,她突然懷念起舊書店里的氣味和門前的梧桐了。她打開舊書店的門,而就在她打開門的那一刻,她發(fā)現已經有人站在舊書店門前了。沒有客套,挑書,付款,留下要找的書名,臨走時微微一笑……她從來沒有發(fā)現:自己這一套流程下來,竟然是行云流水一般。她攏攏頭發(fā)望向門外。梧桐的粗干上,有一只巨大的眼睛。而那從枝頭落下的樹葉,正從那眼睛前飄過。
女人心一顫。她本來是準備關了舊書店的。但這一刻,她決定留下來了。
很快便會是又一個春天的,便會有梧桐樹新鮮的葉子和清香。女人回到舊書店,她慢慢地整理著書架上的書。一只金黃的蟑螂從書架上跑出來,它像光芒一樣,迅速而準確地跑進另一排書架。她忽然覺得:那蟑螂是有靈魂的,而且,它身上所散發(fā)出來的氣息,如此親切、熟悉和讓她心疼。她喊了聲男人的名字,舊書架上竟然發(fā)出了微小卻執(zhí)著的回聲。
包河的荷花與鳥
包河是一條屬于荷花的河流。一年四季,荷花未開,它在等待荷花;到了八月,荷花開了,它便消失。滿河滿河的就只有荷花了。粉紅的荷花,墨綠的荷花,青紅的荷花,墨色的荷花……那一河浩大的荷花啊!河流中所有的故事與所有的傳說,也都消失了。天地間只有荷花。甚至,連荷葉也消失了。荷花立在天地之間,雜亂無章卻又意味深長地書寫著。那些在清晨第一縷霞光中走過來的人,會看見露珠正從荷花微含的眉頭上慢慢走下來,它的晶亮之中,渲染著一抹不易察覺的微紅。而到了中午,秋陽高照,荷花令箭一般,直刺向陽光。一瞬間,荷花的光與陽光交織在一起,多彩而迷幻。而到了黃昏,河邊的人影漸重,離去的,到來的,沉默的,吟唱的……人影竟然都一一地對照進荷花的脈絡之中。因之,這一河的荷花,也就成了一河的人影,月影,花影,與不絕如縷的往昔之影。
而在包河逶迤的兩岸,城市正在近乎野蠻地生長。沒有人能說清這城市在一夜之間長高了幾尺,也沒有人能解釋那些消失的綠地,和被擠壓與夯實的寫字樓間的嘆息與曖昧。城市正在無限地廣大,然而,那里只收留皮囊、生計、流水線。其余的,城市或許將它們交給了包河,交給了荷花。包河是城市尚未工業(yè)化的血管,而荷花,則是城市后院里那一片貼滿星星的天空。
……一只鳥。
一只懂得包河流水的鳥。
一只立在荷花上作為知音的鳥。
一個失去了“知音”這個詞的年代!一只鳥,從夜的深處,到星光的深處,到陽光的深處,到晚霞的深處,到默守的深處,到喧嘩的深處,到靜立的深處,到微顫的深處,一只鳥,比這河流更為久遠的期待著。它的期待,在春天是河水映照里的荷的潛藏的根系;接著,是荷的往上怯生的嫩頭;到了五月,荷從河水里探出頭來,鳥第一時間親吻了荷的新葉。那是多么純潔的處子之吻啊!人間已經久違。六月,荷葉長高,長圓,荷葉上的水珠愈加飽滿,鳥卻選擇了離荷葉不遠不近的河中的樹樁。它站在樹樁上,望著荷葉,看著水珠在荷葉上游戲,傾聽荷葉底下,那水的喋唼。七月既盡,八月的星光之下,最初的荷花開了。鳥正醒著,它注視著那正在打開的荷花,它聞到了荷花的處子之香,它顫抖著,甚至想歌唱。然而,它靜默了。這天地之間,從此便是荷花的了。它獨立在荷花之內,更孤絕于荷花之外。
流浪者早晨從河邊醒來,他告訴人們他就睡在荷花之上。荷花像夢一樣的托舉著他……
而詩人看見了鳥。詩人從高樓上看見了鳥。詩人從河岸邊看見了鳥。詩人從荷花的影子里看見了鳥。
詩人寫道:那些遼闊的未知,殘缺而充滿激情。
詩人又寫道:一和無數,人間世無解的矩陣。
詩人還寫道:一定有更偉大的創(chuàng)造者,讓它們彼此獨立而共存于未來!
云 游
凌晨的大街,燈光、星光與月光一道靜了下來。樹影收攏午夜前的囈語,那里有音樂聲,有人語聲,有打開啤酒瓶聲;有親吻聲,有耳光聲,有暗處的激情聲,有龍蝦被剝開時的爆裂聲;有兩雙手放開時的嘆息氣,有孤寂的人的鼾聲,有不遠處高樓上尖銳而飽滿的叫聲,有蝙蝠從鄉(xiāng)村飛進城市的失去方向之聲,有那些注定要消失卻依舊亢奮的道別聲……所有的聲音,在凌晨來臨之時,全部隱匿。空地如水銀。如收回唱針的黑膠唱片。
所有來者。這城市里的生靈——不僅僅人,還有鳥,蟲子,樹,掉落的果實。我記起這城市街道曾經有過的名字,它們叫藍田,叫海陽,叫陳大郢,叫七里井。那是它們的童年時期,童真清純,長滿稻子與青草。云游的布谷,與雨水,在土地上縱橫;它們是天真,是自由,是樸素。是星光下的相看,月光下的相守,和平常時光里的不離不棄。
當然沒有人再記起。滄海桑田。永恒的苦役無邊無際。甚至,我們很少再感到這座城市的脈動。該唱的唱了,該醉的醉了,該罵的罵了,該哭的哭了,但是,誰能聽出這歌唱之中的深情?誰又能感受到爛醉之中的執(zhí)著?或者,誰又能驚悚于罵聲的熱血?以及哭聲中的昂首?
一切都低了下去,除了正在成長的城市,一切都往下。凌晨,大街掩面而泣。大街如同一個丟失了硬幣的孩子,又像一個失去了鑰匙的少年;大街蒼黃,無助,仿佛一個在暗戀者的婚禮上無語的青年,又顯露出一個中年之人的過早的禿頭。大街的路燈,老年斑似的暗黑下去,天空巨大的青色影子,收回了它由于干涸而無法游動的鰭。
但是,先知依然聽見了街角的對話:
冷嗎?
不冷。
需要我嗎?
需要。
風來了?
來了。
過來吧?
好的。
這人世一下子回到了云游的幸福!如此微小,卻如此真實。大街的弦被拔動,樹都彎下了腰身。該抖落的都抖落了,該清凈的都清凈了。脂粉與面具,虛空中的名字與纏繞,都散去了。從前的流水浮動上來,從前的田地浮動上來,從前田地里的青蛙、蛇、魚和水鴨,都浮動上來,整個大街,到處是稻香,是青草香,是魚香,是蛇莓香,是水香,是種子香,是墓碑香,是骨殖香,是村莊香,是夕陽與簫鼓香……
城市中心的玉米
環(huán)衛(wèi)工是在清晨的第一縷光里發(fā)現它的。那時,城市還在最后的夢境之中。機器暫停,啤酒停止了泡沫,大街和小巷回到了建筑與泥土的原初面目。這是環(huán)衛(wèi)工喜歡的時刻。他穿著黃色的工作服,推著車子,沿著廣場四周,開始這一天的工作。他喜歡這樣的時刻,太陽還沒升起,露珠仍在廣場的花壇中停留,那些花啊草啊的,都天真得像個正熟睡的孩子,又可愛得如同一只收攏了翅膀的白鴿。而且,這一刻沒有喧鬧,沒有匆忙,沒有異樣的目光與尖刻的語言。這一刻,城市新鮮如處子,簡單如星辰。
環(huán)衛(wèi)工慢慢地清掃著。他掃清應該掃去的樹葉、瓶子、方便袋與混雜著酒氣、色氣、財氣的塵土,他掃得很認真,很慢。對于這日復一日的工作,他幾乎傾注了所有的情感。一個在城市微不足道的人!他只有看著黎明之前被他掃清亮的城市,他才有一絲絲的快樂與自信。甚至,他笑了下,一個快六十歲的男人,他的笑,只有在這凌晨的第一縷光里,才更加真實,而且還有一丁點兒的浪漫。
他進入了廣場的花壇。有些花還殘留著昨夜的氣息。他細心地清掃著臺階上的紙屑、花瓣。等他清掃完,他看了眼花壇中心那有著一座兩米高的雕塑。那是一個少女,正在看著頭頂的天空。他每次都想:她到底看見了什么?這偌大的人世間,她還沒看夠?
然后,他看見了城市中心的玉米。
他一眼就認出了那是玉米。雖然才一尺來高。綠色的玉米苗,緊貼著雕塑,嫻靜,不惹事。他再次確認了下,是玉米。真的是玉米。這城市中心的玉米!它如何走進了這城市?又生根,發(fā)芽,并且長成了現在這一尺高的樣子。它為何而來?又將在這城市中,如何演繹它有葉有果的一生?
環(huán)衛(wèi)工看著,伸手摸了摸玉米的葉子。清涼,像老家玉米地的玉米。他腦子里“嘩”地就響起了風吹玉米的浩大聲響。但隨即,他看出了這玉米與這城市以及雕塑、花壇還有即將開始的市聲的悖逆。一瞬間,環(huán)衛(wèi)工明白了這株玉米的未來——很快,它將被清除出這花壇,被作為垃圾,送入垃圾場,然后被粉碎、消失……
它也是有夢的啊!可是,在這城市里,有多少人的夢會真正地結出果子?
環(huán)衛(wèi)工沉默著離開了花壇,這時候,太陽正升起,清軟的陽光,正照在玉米上,玉米生動著,連同它身邊的少女雕塑,也一起生動著。
環(huán)衛(wèi)工想:我必須讓它活下來,讓它長大,成為新娘。然后,結出玉米,金黃金黃的玉米。
環(huán)衛(wèi)們想著,笑著。但是,他必須繼續(xù)他的工作。他離開廣場,開始將工作面向四周擴散。這一天,他將會清掃道路、寫字樓下的過道、居民區(qū)和被玻璃環(huán)繞的高大的觀光塔……他笑著,因為他有期待。
他想好了,要在自家的狹窄的陽臺上,給玉米安一個穩(wěn)定的家。
(選自《安徽作家》2023年第1期)
作者簡介

洪放,1968年生,安徽桐城人。中國作協會員,安徽省作協副主席,合肥市作協主席。曾出版長篇小說《秘書長》《撕裂》《百花井》《追風》等十余部,散文集《南塘》《先生的課堂》等。并發(fā)表大量中短篇小說。作品曾多次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新華文摘》等轉載并收入多種年選。曾獲安徽社科文藝出版獎,浩然文學獎,林語堂文學獎,《安徽文學》獎,《廣西文學》獎,《紅豆》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