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shí)間:2022-12-15 來(lái)源:安徽作家網(wǎng) 作者:安徽作家網(wǎng)
近日,我省作家王漢英散文集《一條大河波浪寬》由安徽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發(f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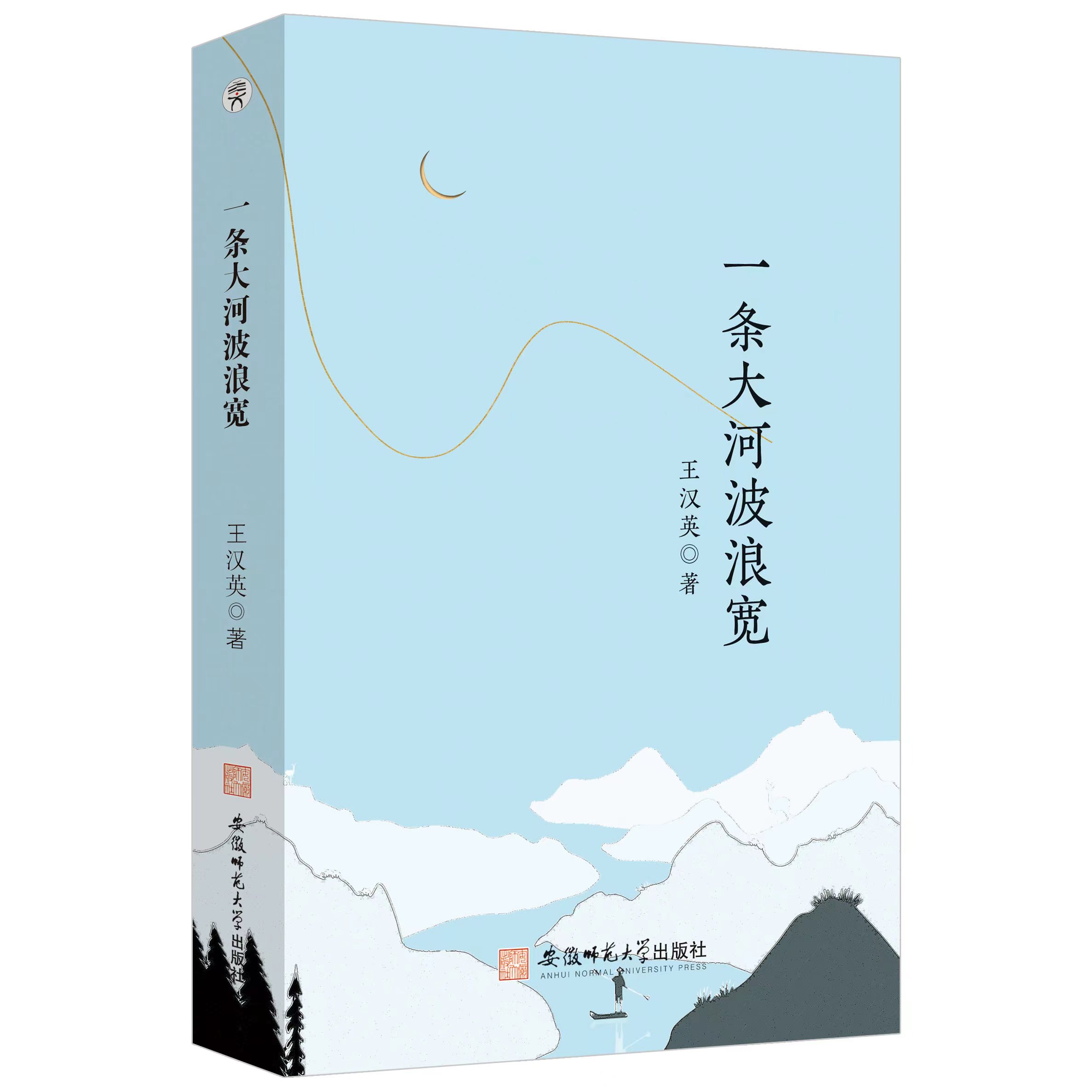
內(nèi)容簡(jiǎn)介
本書(shū)以飽滿(mǎn)優(yōu)美的筆觸,開(kāi)啟了一次對(duì)長(zhǎng)江文化和生態(tài)的抒寫(xiě)。記錄、闡釋有關(guān)長(zhǎng)江流域生態(tài)與人文環(huán)境、思想文化、歷史人物、文學(xué)藝術(shù)、民風(fēng)民俗和人文景觀。本書(shū)觸探方苞的文化江南、劉大櫆的江南審美和姚鼐的長(zhǎng)江文化意識(shí),評(píng)析朱光潛的《談美》,回望古詩(shī)中長(zhǎng)江的風(fēng)景;從漢劇中的“云夢(mèng)澤”一路行至十六鋪、新安江畔、小孤山、振風(fēng)塔、上碼頭,留念街頭“磨剪子、搶菜刀”的回聲……文中展示了長(zhǎng)江文化和生態(tài)的豐厚與魅力,生動(dòng)描繪了長(zhǎng)江中下游的人們,在時(shí)光的洪流里,一派熱氣騰騰的生活畫(huà)卷。
序:每一滴江水
許旸
收到《一條大河波浪寬》樣章,光是掃過(guò)目錄,耳邊就響起了鄉(xiāng)音——
吼一嗓子“磨剪子——熗菜刀”,“安徽的母語(yǔ)”山鳴谷應(yīng),從十六鋪、小孤山、上碼頭,一路回蕩至下樅陽(yáng)、古鎮(zhèn)湯溝、振風(fēng)塔……“君住長(zhǎng)江頭”,把每一滴江水鋪于眼前,待來(lái)年,“江南丘陵的春天里,丟下一粒籽,發(fā)了一顆芽”……
蓬勃的鄉(xiāng)情,順著長(zhǎng)江水,乘著空氣,洶涌而來(lái)。由此,許多有關(guān)故土的記憶,一點(diǎn)點(diǎn)蘇醒膨脹,拱出板結(jié)的記憶土壤,冒出毛茸茸的枝丫。恍惚回首——哎呀,原來(lái)我離故鄉(xiāng)已經(jīng)這么久這么遠(yuǎn),原來(lái)這里還有那么多我未曾熟悉或自以為熟悉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
所以,《一條大河波浪寬》的寶貴在于,這本集子無(wú)時(shí)無(wú)刻無(wú)休無(wú)止地在打撈、在縫補(bǔ)、在捕捉,無(wú)論是從史料堆里爬梳線索,從父親母親的記憶里拼出版圖,還是從田間地頭、浩渺江波采集鮮活片段,書(shū)中“全感官”式的地理人文書(shū)寫(xiě),化作寫(xiě)給故鄉(xiāng)的一封封綿長(zhǎng)情書(shū),讀者也隨著文字里江水的波動(dòng)、流淌、澎湃,體味一座江邊小城的煙火氣息。
方言、戲曲、美食、典故、建筑……簇?fù)碇紒?lái),人聲鼎沸中,故鄉(xiāng)的身影愈發(fā)真切。王漢英以她多年的堅(jiān)守、飽滿(mǎn)的深情、伶俐的筆力,寫(xiě)活了這方水土的生生不息,遞上了一份長(zhǎng)江生態(tài)融入日常的個(gè)性化報(bào)告。
有時(shí),回眸出生地,最初的出發(fā)點(diǎn),很容易因身心距離跌入“時(shí)光濾鏡”,或一味陷入懷舊,或流于瑣細(xì)考據(jù),而《一條大河波浪寬》始終以一簇簇溫暖而不熾烈的情感貫通,讓人順著字里行間的細(xì)浪,打量著歲月沖刷的痕跡。
近兩年疫情改變了很多人的行動(dòng)軌跡,向外走四方,諸多不便,于是,這個(gè)時(shí)候,向內(nèi)再回望,我們獲得了對(duì)故鄉(xiāng)更切身地感觸。
正如書(shū)中所說(shuō):“我們?cè)谛畔r(shí)代里打滾,漸漸蛻變,離精致的冷漠主義者越來(lái)越近。”而在江水氤氳中,作者并不諱言“我是喜歡大城市的,少年的第一個(gè)夢(mèng),就是逃離生長(zhǎng)油菜花的地方。”但這種沖動(dòng)與逃離,與“由衷愛(ài)上這山重水復(fù)的一堵堵白墻”并不矛盾。
在風(fēng)箏線般的拉拉扯扯中,每個(gè)從故鄉(xiāng)出發(fā)的人,獲得了遠(yuǎn)超出懊惱、后悔、快意、慶幸等單一情緒的復(fù)雜體驗(yàn),故鄉(xiāng)不語(yǔ),只靜待歷經(jīng)摔打后的回歸。
我是安徽人。我是“安徽”人。我是“安”“徽”人。我胸前有個(gè)通靈寶玉,這么多年,我怎么沒(méi)有發(fā)現(xiàn)呀。幸虧沒(méi)發(fā)現(xiàn)得早,否則我也摔。
——這段書(shū)中的神來(lái)之筆,令我一遍遍回味家鄉(xiāng)的各種懷抱。就像作者說(shuō)“江水奔流過(guò)的地方驗(yàn)證著流水的哲學(xué)”,有關(guān)故鄉(xiāng)的反復(fù)書(shū)寫(xiě)何嘗不在更新著“家”的哲學(xué)——我愿意接納你的一次次沖動(dòng)。
“后記”代創(chuàng)作談
王漢英
一本書(shū)的容量是承載不了浩蕩長(zhǎng)江的無(wú)窮個(gè)億萬(wàn)分之一。只是說(shuō),我想借一本書(shū)的容量來(lái)描述一滴水的重量和溫度。為什么非得要寫(xiě)一本這樣的書(shū)?起先我以為是為了計(jì)劃好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后來(lái)我否定了……并沒(méi)有。就是非常想寫(xiě)。非常。
這幾乎是一個(gè)心理暗示,必須要有一次告白,對(duì)故鄉(xiāng)的。對(duì)自己的。
故鄉(xiāng)的形象,在我的記憶版圖上,就是一條浩浩蕩蕩的長(zhǎng)江。故鄉(xiāng)并不遙遠(yuǎn),它一直在我的身后奔流。然而,我卻很少與人談起它。是的,很少。那些牙牙學(xué)語(yǔ)的聲調(diào),那些蒹葭蒼蒼的往事,那些聲蕭鼓樂(lè)的鄉(xiāng)村情節(jié),那些酸辛和熱辣的生活,以及正在經(jīng)歷的變化……我并不愛(ài)陷入回憶之中,回憶并不比事實(shí)更靠得住。
童年時(shí),一滴掛在棉桃上晶瑩欲滴的露珠,也許要比走五里地去上學(xué)的路程,更讓我印象深刻。
回憶要么讓人牽腸掛肚,要么就是耿耿于懷,或許基于這些經(jīng)驗(yàn),我覺(jué)得自己特別像一條魚(yú),記憶也只有幾秒。
可真是這樣嗎?即使是一條小得不能再小的小魚(yú),她也許會(huì)在某天游過(guò)長(zhǎng)江大橋時(shí),面對(duì)水天一色,江流千古的浩渺煙波,突然想喊出一嗓子——你在哪里啊?媽媽。
基因里攜帶著江水的因子,無(wú)論走多遠(yuǎn),無(wú)論我如何地想繞過(guò)回憶,這些因子總會(huì)固執(zhí)的在一個(gè)深夜,幻化成故鄉(xiāng)一個(gè)個(gè)久遠(yuǎn)而模糊的人物,站到我的夢(mèng)里,頑強(qiáng)地告訴我,我是長(zhǎng)江的女兒,我的第一聲“姆媽”,是永遠(yuǎn)的母語(yǔ)。
《一條大河波浪寬》這本書(shū)的緣起,應(yīng)該就是這樣的吧。雖然收錄了以前的少許文稿,主要內(nèi)容前后花了好幾個(gè)月才寫(xiě)完。那幾個(gè)月里,我?guī)缀跻挂拐碇L(zhǎng)江入眠,一篇一篇累積而成。
完成文本的整理時(shí),這本書(shū)的線索突然亮了——原來(lái)我執(zhí)于寫(xiě)這本書(shū)的念頭,得到自我解釋。我仿佛看到一條小魚(yú)緩緩游出江灣,順流,逆流——逆流,順流……是的,除了《一條大河波浪寬》——這是我母親最?lèi)?ài)唱的一首歌,沒(méi)有更適合的書(shū)名了。先前我擬了不下七八個(gè)書(shū)名,經(jīng)過(guò)出版社三四輪地淘洗,只有這個(gè)備選的“一條大河波浪寬”一錘定音。這是命定的書(shū)名,我欣然領(lǐng)命。
巜一條大河波浪寬》是我潛在地告白——小魚(yú)和長(zhǎng)江的關(guān)系,就是我和母親的關(guān)系。對(duì)我而言,故鄉(xiāng)就是母親,母親就是故鄉(xiāng)。
只有書(shū)寫(xiě),母親才不會(huì)真的隨著時(shí)間而消失于無(wú)形。只有書(shū)寫(xiě),母語(yǔ)才不會(huì)隨地理變化而改變音韻。
我出版的第一本書(shū)叫《人海》,這本叫《一條大河波浪寬》,奇怪得很,這兩個(gè)名字莫名有點(diǎn)關(guān)聯(lián),都有茫茫水字旁,并不是故意設(shè)計(jì)的。在《人海》里,我是粒微不足道的沙礫,在《一條大河波浪寬》里,我是條微不足道的小魚(yú)。
也許有人翻開(kāi)它們,會(huì)看到一條小魚(yú)兒,攜帶一滴長(zhǎng)江水,正奮力游蕩在人海。如此奮力,其實(shí)只是想讓生命更加結(jié)實(shí)起來(lái),這一點(diǎn)精神世界的感悟,是母親河的饋贈(zèng)和滋養(yǎng),謝謝打開(kāi)書(shū)頁(yè)的你們。
作者簡(jiǎn)介

王漢英,女,安徽省作協(xié)會(huì)員,從事文學(xué)編輯工作,已出版?zhèn)€人詩(shī)集《人海》。有文學(xué)作品見(jiàn)于報(bào)刊,部分作品轉(zhuǎn)載于光明網(wǎng),中國(guó)作家網(wǎng)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