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shí)間:2021-11-05 來(lái)源:安徽作家網(wǎng) 作者:安徽作家網(wǎng)
日前,我省作家馬洪鳴長(zhǎng)篇小說(shuō)《霜刀》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發(f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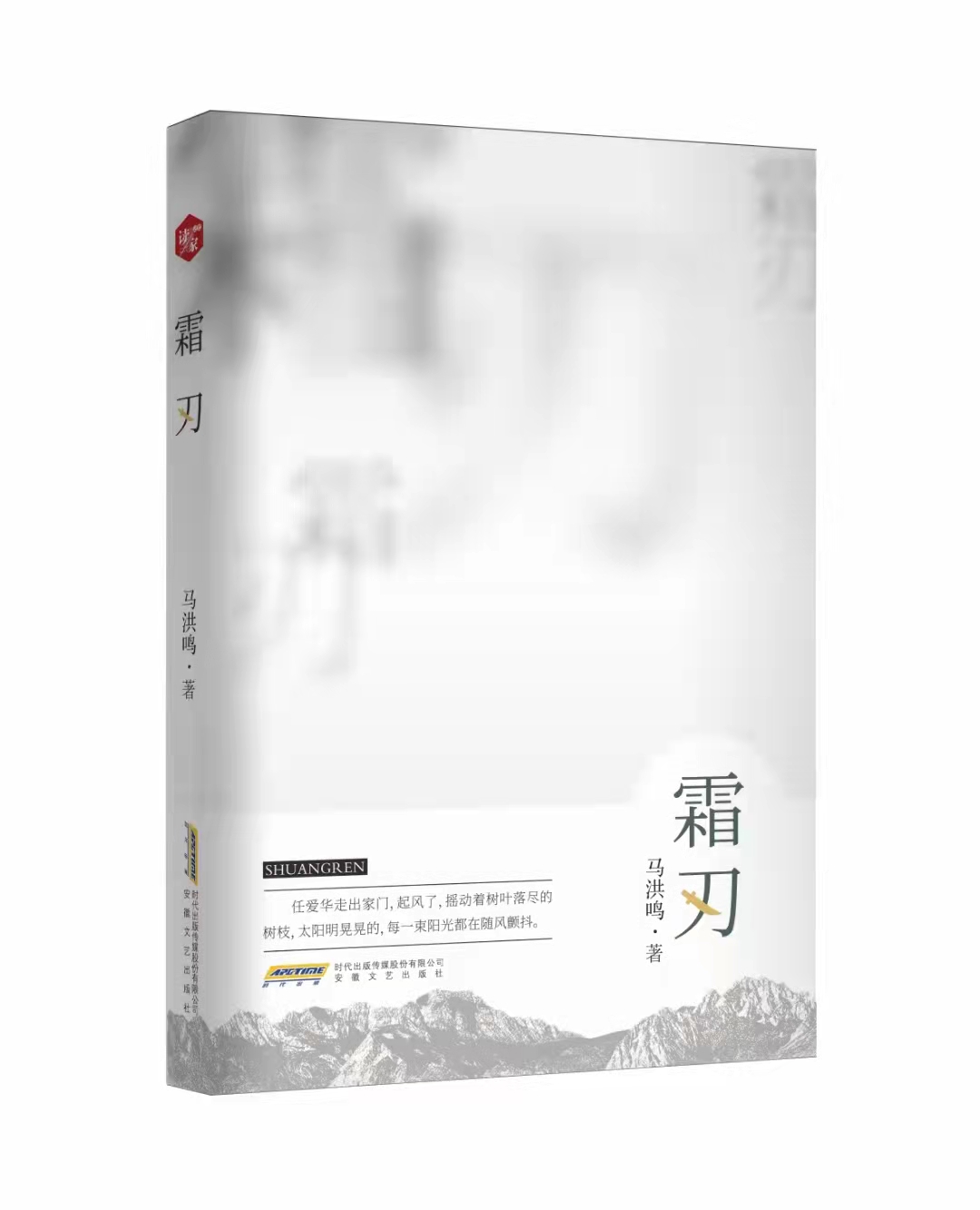
作品簡(jiǎn)介:
《霜刃》將千年的打鐵技藝巧妙地融入到文學(xué)的記敘之中,詩(shī)意的語(yǔ)言伴隨著流暢的打鐵程序緩緩敘述,節(jié)奏張弛有度,于不動(dòng)聲色之中記錄了古老的匠藝,以及民間匠人堅(jiān)忍、執(zhí)著之心。小說(shuō)圍繞一把傳說(shuō)中的利刃展開(kāi)故事情節(jié),一家三代人對(duì)利刃的不同態(tài)度,在失與得之間,將人性置于刀鋒之下拷問(wèn)。寒光熠熠的鋒芒間,有紛亂的世相亦有人性的裂變之痛以及人心善良的光茫、小人物的人格色彩。小說(shuō)的內(nèi)在精神有赤裸的人性卻不乏悲憫。小說(shuō)注重心里世界的刻畫(huà),在結(jié)構(gòu)上也進(jìn)行了大膽的嘗試,分為兩種章節(jié)呈現(xiàn),卻并非傳統(tǒng)的主線和副線鋪陳,小說(shuō)以打鐵程序銜接卻并無(wú)中斷之感,讀來(lái)令人耳目一新,同時(shí)也多方位地呈現(xiàn)了民間匠人在時(shí)代的巨變中的生命狀態(tài)及情感,也彰顯了匠人之心的價(jià)值,以及對(duì)傳統(tǒng)匠藝的繼承與重建的思考。
作品節(jié)選:
霜刃(節(jié)選)
馬洪鳴
第一章 蒼老的恐懼
1
任愛(ài)華心生恐懼,但他人并不清楚。
是她熟悉的恐懼,存在過(guò),存在著,已經(jīng)蒼老了······整整35年,她曾經(jīng)把這恐懼掩藏在更幽深、更隱秘的地方,混淆在內(nèi)心深處。恐懼,卻在接到陌生電話的那一瞬間而迸發(fā),沒(méi)有尺寸、沒(méi)有形狀、而悄無(wú)聲息的恐懼······
眼前是鐵餅街的街道,有些房門(mén)敞開(kāi)著,有些房門(mén)關(guān)閉著,從東南方的大良山竄出的寒風(fēng),掠過(guò)文水河,裹挾著枯樹(shù)的焦燥和河水的躁動(dòng),一種不受任何阻擋的暴烈情緒,徑自在街道上喧囂。路邊丟棄的廢紙、廢塑料袋借著風(fēng)力一次次沖向半空,而寒氣像一條蜿蜒的繩索,從腳底攀沿,一道道纏裹著任愛(ài)華。
陌生號(hào)碼通話內(nèi)容很短,短到只有耳朵能夠抓住,他說(shuō),我忍不住打了這個(gè)電話。 任愛(ài)華的手指僵冷,仍抓緊話筒中的余音追問(wèn),你是誰(shuí)?你說(shuō)你是誰(shuí)?
我仍然相信你不是個(gè)撒謊的孩子,你不用知道我是誰(shuí)。沒(méi)有點(diǎn)明意圖,沒(méi)有說(shuō)明突然來(lái)電是出于善意、歹意、還是悔意。仍然稱她是個(gè)孩子!仍然是那句霸道、罪惡的原話,低沉的、沙啞的、穿透力的腔調(diào),沒(méi)有消匿、沒(méi)有萎靡,有著頑強(qiáng)的生命力和35年前留給她的困窘一同,成了一枚生命中的烙印,而由此衍生的屈辱與恐懼同樣存在著。
一枚沒(méi)有年輕過(guò)也沒(méi)有蒼老過(guò),可以活著也可以死去的烙印!
對(duì)方掛斷電話,通話時(shí)長(zhǎng)16秒。一種無(wú)法平息的情緒卻并未戛然而止,任愛(ài)華手指顫抖著,循著號(hào)碼撥回去,她想要抓住他,回?fù)羲岳邪愕匿h利、瞬間的冰冷與火熱的交鋒干凈利落地?cái)財(cái)嗨?/span>
電話接聽(tīng)了,但換了一副腔調(diào),拖沓而平和,輕飄飄的:找誰(shuí)啊,這里是公用電話啊。剛才打電話的是誰(shuí)?抓住他!別讓他走!任愛(ài)華顫聲喊道。神經(jīng)病啊,“啪”地一聲,電話掛斷了。寒風(fēng)打著旋,饒過(guò)任愛(ài)華,將街面上的一張廢紙帶到半空中。任愛(ài)華站在空蕩蕩的鐵餅街上,雙手摟緊了雙肩慢慢蹲下,身體顫抖著越縮越緊,仿佛抵御和躲避著危險(xiǎn)和不可預(yù)測(cè)的未來(lái)。
任記鐵匠鋪,在50米開(kāi)外,隔著一段有歷史的青石路面,石板之間的淤泥布滿了不屈的青苔。鐵匠鋪的門(mén)外是個(gè)簡(jiǎn)易的柜臺(tái),兩張條凳肩負(fù)一張邊角凹凸不平的木板,木板上擺滿打制的鐵制成品,菜刀、剪刀、石釬······還有一些流動(dòng)的歲月。
鋪?zhàn)永铮芜B鋼正在砂輪機(jī)邊打磨,一件成品刀具通身已呈現(xiàn)出人們常見(jiàn)的鋒芒,砂輪機(jī)正開(kāi)在最小的檔速,以便挫敗細(xì)微的鈍痕。任愛(ài)華跨進(jìn)門(mén)檻時(shí),身影遮擋住門(mén)外的光線。何連鋼關(guān)閉砂輪機(jī),端詳了一番手中的刀具,然后,抬眼望向站在門(mén)邊的任愛(ài)華,見(jiàn)她臉色蒼白,身體微微打顫,手上拎著的保溫飯盒直晃蕩。你怎么了?太冷了吧?何連鋼撂下打磨的刀具,接過(guò)飯盒,手掌掠過(guò)任愛(ài)華指尖驚人的涼,手怎么這么涼?快到爐邊來(lái),爐膛里還有熱火。他拽起任愛(ài)華的手貼在嘴上呵了一口熱氣。
背靠爐壁,坐在小板凳上,任愛(ài)華雙手收緊了雙肩,仍然抖抖的。你怎么了?何連鋼又問(wèn)。沒(méi)什么,就是冷!任愛(ài)華垂著眼瞼,牙齒打著顫,擠出幾個(gè)字。下次你不要給我送飯了。何連鋼說(shuō)著摘下掛在鐵釘掛鉤上的外套,披在任愛(ài)華身上。煙熏累累的墻壁上,其余的掛鉤上掛滿整齊的工具,鐵鉗子、鐵錘······由小到大,像是一排隨時(shí)應(yīng)征的士兵。
我不送飯,你盡糊弄自己。任愛(ài)華說(shuō)著拎起掛鉤上的一把小鐵錘,走到鐵砧旁,對(duì)著鐵砧用力一擊,鐵砧發(fā)出一道有沖擊力的脆響,帶有余音。接著,任愛(ài)華像是鼓足了勁和一種隱秘而冷酷的對(duì)手較量,鐵錘愈來(lái)愈密集地落在鐵砧上,鐵與鐵的擊打聲,擁有硬碰硬的從容,鐵錘落在鐵砧上彈起的瞬間,有些挫敗明顯被擊落了。漸漸的,任愛(ài)華的臉上有了紅暈。你這是干嘛?像和誰(shuí)較勁似的。何連鋼的話音被起伏的擊打聲湮沒(méi)了。
洗凈了手,何連鋼打開(kāi)保溫飯盒,飯盒里的香氣和熱氣不畏寒冷似的裊裊升起。何連鋼在擺滿“鐵畫(huà)”的案臺(tái)上開(kāi)辟了一塊空地,鋪開(kāi)一塊軟玻,將紅燒肉、香菇青菜、雞蛋羹、白米飯一一放在上面。案臺(tái)上幾幅“鐵畫(huà)”相互倚靠,畫(huà)面內(nèi)容有的是山水、有的是人物、花鳥(niǎo)還有一些是無(wú)法辨清的圖案,在薄薄的鐵板上呈現(xiàn)出凹凸有致的個(gè)性。這些獨(dú)特的作品屬于任愛(ài)華,沒(méi)有被外人品讀,沒(méi)有人傾聽(tīng)她解讀,這些“鐵畫(huà)”是她生活內(nèi)容的一部分,像是她對(duì)鐵的一種剖析。她在這里把她挑選出的鐵,經(jīng)過(guò)紅爐中冶煉,有時(shí)鍛、有時(shí)鉆、有時(shí)焊、有時(shí)銼,而堅(jiān)硬的鐵的柔韌和延展經(jīng)過(guò)她的手?jǐn)U展開(kāi)來(lái),成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現(xiàn)在,她以鐵錘敲打鐵砧,不發(fā)一語(yǔ),圓圓的下巴繃的緊緊的,她不是鐵的信徒,但她傾心傾聽(tīng)鐵與鐵的碎語(yǔ)。
靠近任愛(ài)華待過(guò)的位置,有爐火的余溫和任愛(ài)華遺留的體溫。何連鋼看了一眼任愛(ài)華,今天的伙食太浪費(fèi)了,又有肉又有雞蛋,下次午飯弄簡(jiǎn)單點(diǎn)!他大聲說(shuō),現(xiàn)在沒(méi)活,我不出力氣,不用吃的這么好。身體是自己的,不是力氣的!任愛(ài)華搶白他,手下用力一錘。他們的對(duì)話夾雜著擊打聲,幾種聲音交加并不令人感到呱噪和困窘,而是充滿了帶有彈性的活力。
吃過(guò)午飯,何連鋼靠在爐壁邊閉眼打盹,像是要將任愛(ài)華制造出的敲擊聲鎖在睡眠之外,任愛(ài)華注意到這一點(diǎn),便停止了敲打。手臂松懈了,鐵錘便順勢(shì)滑落,而那些有力的敲擊聲并沒(méi)有留下印跡,鐵匠鋪?lái)暱涕g落于寂靜之中。在何連鋼視線之外,任愛(ài)華慢慢抬起雙臂,再次收縮了雙肩。她輕輕抬腳,繞過(guò)鐵錘、繞過(guò)地面上凌亂的鐵塊、繞過(guò)何連鋼的鼾聲,悄悄走到鐵匠鋪的后門(mén),拔開(kāi)鐵銷,閃身躲過(guò)穿堂而過(guò)的一陣?yán)滹L(fēng)。
鐵匠鋪后門(mén),通向他們留在此處的家。
壹 撿料
坐北朝南的三間瓦房,是在土胚墻的宅基上翻建而成,曾添加仿古的青磚 。門(mén)前院內(nèi)并沒(méi)有樹(shù),卻飄滿了落葉,榆樹(shù)葉、楝樹(shù)葉,任愛(ài)華熟悉這些樹(shù)葉。她出生之前,這兩棵樹(shù)落地院門(mén)之外,堅(jiān)守至今。現(xiàn)在,院落中每間房間門(mén)窗緊閉,空置于此,有些存在過(guò)的仍然存在,有些存在過(guò)的已經(jīng)消失了,而一切并沒(méi)有應(yīng)該存在或并不應(yīng)該存在的界定。
任愛(ài)華推開(kāi)每扇房門(mén),祖父與祖母的、父親與母親的、她和弟弟任建華的,每間房間的每扇門(mén)都能搜尋到過(guò)往的痕跡,每扇門(mén)板依然和門(mén)框相依相偎,并未荒廢!灶房在鐵匠鋪通向住房的走廊盡頭。土灶倚墻而立,灶臺(tái)上貼了白瓷磚,煤氣灶像是它的附屬,立在一旁。曾聚集在此的灶火燃燒的聲音、鐵鏟掠過(guò)鍋底的聲音、粗糙的食物、精細(xì)的食物被烹煮的聲音,現(xiàn)在,都已消匿,都過(guò)去了,而新的等待存在著。
院落沒(méi)有大宅院的陣仗規(guī)矩,卻有屬于此地的獨(dú)一無(wú)二的次序。父親的房間類似堂屋,擺放著條幾和八仙桌。墻角的挑擔(dān)還在,因被淘汰而產(chǎn)生了保留價(jià)值。窗下曾擺放單人床的位置空蕩蕩的。單人床連同床上的鋪蓋、幾件褪色的衣物都已化成了灰燼。任愛(ài)華想起,半個(gè)月前,焚燒父親遺物那天,瘋狂而殘酷的火焰,身子不由地一陣發(fā)寒。
鍍鋅鐵皮焊制的院門(mén)緊閉著,焊制的鐵銷上掛著一把中號(hào)的明鎖,鐵銷上有鐵銹的斑點(diǎn),和時(shí)光息息相關(guān)的斑點(diǎn)!門(mén)外榆樹(shù)和楝樹(shù)的樹(shù)枝躍上了院墻。院外文水河隨風(fēng)拍岸的水聲,穿透了泥土夯實(shí)的院墻,水聲悶悶的。
在這里,房間、院落以及在房間里沉默的陳舊的家具,任愛(ài)華能看見(jiàn)她的生活,不被拉長(zhǎng),也不被縮短。
任愛(ài)華出生時(shí),她母親葉佳宜陷入自身身體的疼痛和煩躁之中,母親的疼痛卻是由來(lái)到人世的女兒攜帶而至,母親承受著痛苦,而她這個(gè)女兒漫不經(jīng)心地經(jīng)過(guò)生命之門(mén),來(lái)到了人間。任愛(ài)華出生前,一些無(wú)關(guān)痛癢的煩躁早已在母親葉佳宜的腦海中堆積著,她總是嚷嚷大腦嗡嗡作響,抱怨一些游蕩的靈魂途經(jīng)于此,而擾亂她腦海中的清凈的生靈,有時(shí)被認(rèn)定那生靈是從耳朵飛入的蚊子,有時(shí)又加罪于無(wú)辜的金龜子。任愛(ài)華出生后,母親葉佳宜沒(méi)有精力看她一眼。任愛(ài)華發(fā)出對(duì)人世間的第一聲啼哭之后,仍然緊閉雙眼,她的皮膚呈現(xiàn)淺淺的粉紅色,很薄,可以看見(jiàn)紅色的血管,全身布滿了白色的皮脂,是在羊水中浸泡留下的。而她母親的臉上布滿了晶瑩的水珠,是在疼痛掙扎時(shí)流下的汗水,母親的疼痛只有母親的汗水能夠領(lǐng)會(huì)。
4歲時(shí),祖母對(duì)任愛(ài)華說(shuō)起這些,有關(guān)她和這個(gè)世界和母親的關(guān)聯(lián),她并沒(méi)有完全通曉。祖母說(shuō)母親葉佳宜是典型的瓜子臉,上部略圓、下部略尖,一種美麗的臉型,任愛(ài)華并沒(méi)有得到遺傳,她的長(zhǎng)相酷似父親,長(zhǎng)圓臉型,一種被認(rèn)為很和諧的臉型,而她的皮膚白凈、細(xì)膩,祖母認(rèn)定,這一點(diǎn)遺傳于她。但任愛(ài)華留有很深的關(guān)于母親長(zhǎng)相的記憶,有關(guān)于母親的美的記憶,屬于小心翼翼收藏的記憶,有透明的薄膜,輕易不能觸碰。當(dāng)年,祖母坐在房間的角落里,晦暗中的薄弱光線使祖母的臉部有柔和的線條,任愛(ài)華靠近祖母,有些線條落在她的身上,并不張揚(yáng)。床上的麻布蚊帳耷拉著,只有她稚嫩的目光能看得見(jiàn),搗亂的瞌睡蟲(chóng)在其中鉆來(lái)鉆去,屋外的陽(yáng)光跨過(guò)門(mén)檻,撥灑在窗前,房門(mén)前的光亮和房間角落處的暗影,形成了鮮明的對(duì)照。任愛(ài)華和陽(yáng)光同樣無(wú)法理解祖母對(duì)明亮的回避。祖母習(xí)慣隱坐于房間的暗處,在老架子床一側(cè),坐出順從的姿勢(shì),而麻布蚊帳垂掛著,并未動(dòng)情,即使它經(jīng)歷過(guò)搓麻紗、紡紗、織布······這些古老的歷程。
作者簡(jiǎn)介:

馬洪鳴,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2015年開(kāi)始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作品刊于《清明》《天津文學(xué)》《安徽文學(xué)》《啄木鳥(niǎo)》等期刊雜志。著有長(zhǎng)篇小說(shuō)《揉藍(lán)秘境》《翡翠賭石》《鐵活》。《揉藍(lán)秘境》入選安徽作協(xié)第三屆精品扶持項(xiàng)目,入圍參評(píng)第十屆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作品曾獲奔流文學(xué)獎(jiǎng)。